《重生成了反派的掌中嬌》 第141章 鳥不拉屎的肅州
衡公主扔了一顆驚天悶雷,炸的溫婉和謝淵渟頭昏腦漲,無力思考。
時值深夜,衡公主早已經被謝淵渟趕走,
元宵燈會的喧囂早已經結束,溫婉終是起了,走到謝淵渟后,
拍拍他的肩膀,道:“走吧,該回家了。”
一夜之間,謝淵渟從靖北候和長公主的幺兒了楚妃和靖國公珠胎暗結的產,
別說謝淵渟這個當事人,溫婉也只覺得這個世界瘋魔了。
所有勸的話在腦海里轉了一圈又一圈,最終,還是選擇什麼都不說,
如果謝淵渟愿意傾訴的話,倒是很樂意做個忠實的傾聽者。
意料之外的,謝淵渟的緒比想的要好很多,
見溫婉呆坐半夜,第一句話竟是要他回家,
謝淵渟忍不住主道:“你就沒什麼要問的嗎?”
皇室辛,他的世,忽然知道了這麼多的,難道一點都不覺得好奇?
溫婉腳步未停,微微側頭,淡淡道:“你想為他們報仇嗎?”
無論是為一群后妃所害的楚琳瑯,
還是因為和楚琳瑯有所牽連就被污蔑謀逆,滿門抄斬的靖國公,
他們其實都很無辜,而害死他們的人卻坐榮華富貴,
溫婉想,如果是的話,就算拼盡全力也要將這些人全部拽地獄。
只是謝淵渟卻比這個旁觀者冷靜多了,
他說,“我不會因為衡公主的一面之詞去冒險,
但如果,最終事實真如所說的那般,我會讓所有傷害過他們的人都付出代價。”
他說著話時緒沒有太多的起伏,就好像在向人陳述一個很普通的決定似的。
溫婉心中不解,怎會有人聽到自己的世,會如此冷靜?
想到之前謝淵渟的話,忍不住問道:“你早就知道自己不是長公主和靖北候的親子了?”
Advertisement
“是。”
謝淵渟點頭,“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母親和楚琳瑯是手帕,就像你和白萱茹一樣,
們在戰場上不打不相識,而后惺惺相惜。
只是后來在京都遇見,兩人份不同,便不在人前表現出來。
楚琳瑯產期臨近時宮中異頻出,早就料到會有危險,便求了母親幫,
但母親當時在宮外,鞭長莫及,收到消息時為時已晚,
只勉強保住了我的命,楚琳瑯卻是難產而亡了。”
沒有人能在提及自己亡故的生母時無于衷,
即便謝淵渟從始至終都沒有過楚琳瑯一聲母妃,
溫婉卻分明聽到,他的聲音越來越干。
“那靖國公呢?”
不想讓謝淵渟沉浸在過去的悲傷中,溫婉不停的提問題。
謝淵渟也的確被轉移了注意力,反應有些遲緩的搖頭,
“楚琳瑯和親天玄,楚琳瑯生我時也已經是進宮后的第九個月,
父親和母親一直以為我就是先皇之子,
在今日之前,我從未想過我的親生父親會有第二個人選。”
哪怕他一點都看不上先皇,也從未想過親生父親另有其人。
溫婉微微頷首表示理解,“那麼,我們明日的計劃還照常進行嗎?”
話鋒陡轉,謝淵渟下意識道:“當然照常進行,肅州那邊不能再等下去了。”
說完才愣住,有些哭笑不得的道:“我們方才談論的是這件事嗎?”
“你不是還要去查證嗎?”
溫婉理所當然道:“是真的,咱們就為他們報仇,
若是假的,也不耽擱正事啊,你說呢?”
謝淵渟認真一思索,覺得說的還真有些道理,讓人無法反駁。
于是這樣一件令人頭禿的事就被暫時擱置,如溫婉所言,抓時間忙正事。
肅州與靖州相距四百余里,溫婉和謝淵渟早晨從靖州出發,
策馬疾馳整整一日,傍晚才抵達肅州。
目的全是一幢幢的干打壘,遠遠看見幾間二層的土樓,屋頂無飄著酒旗。
呼嘯的寒風像是要把人都吹走,路過的行人卻像是早已經習慣了這惡劣的條件,
兀自說笑或者行路,耳朵里順風飄來幾句吆喝,是有人在行酒令。
“這,便是肅州城嗎?”
溫璇看著眼前的一切有些懷疑人生,京都附近的一切小村莊怕是都要比這里強太多吧?
“沒錯,這就是肅州城。”
溫婉淡定道:“后悔了,我可以讓人送你回去。”
臨出發的時候溫璇非鬧著要跟來,其名曰要助溫婉一臂之力,
溫婉被纏的沒辦法,想著以肅州城的況,就算來了也待不住,便答應了。
如果小丫頭畏難,想要回去,倒是正遂了的愿。
沒想到溫璇明明一臉菜,卻還是堅定的搖頭,“不,我不回去。”
對上溫婉詫異的眼神,小板兒的筆直,“我說了要幫你,就一定會幫,
不就是條件差了點兒麼,咱們就是因為這里條件差才來這兒的,
我不走,你也別想趕我走!”
小丫頭機靈著呢,知道溫婉不想讓留下來,干脆先發制人。
溫婉無奈,“行,只要你能堅持住,想留便留下來吧。”
“恭迎公子回城!”
一陣整齊的聲音將正在斗智斗勇的姐妹倆嚇了一跳,
聞聲去,便見幾個穿著鎧甲的將士站在謝淵渟面前,想來是來迎接謝淵渟的,
一群人上帶著難掩的煞氣,街道上的百姓們仿佛見了洪水猛似的,四散開來,
溫婉還聽到了“砰砰”關閉門窗的聲音。
無暇多想,便見謝淵渟在沖招手,
溫婉理了理心神走過去,便聽謝淵渟道:“溫婉,之前你們在遼東打仗的所有軍需都出自手。”
說完,攬著溫婉的肩膀向前幾步,指著一人道:
“這是肅州守備軍副將韓啟江,他自己就是肅州人,
此番打下肅州,也是他打的前鋒,關于肅州的一切,你都可以向他了解。”
那是個三十來歲的男人,高大獷,很符合溫婉對靖北人的固有印象。
謝淵渟特地向自己介紹他,說明此人地位非同一般。
溫婉便客氣頷首,“韓將軍,日后請多多指教。”
韓啟江咧出一口大白牙,“指教不敢當,溫大小姐有何要求,盡管吩咐便是,
別的不敢說,您若是想了解肅州城的況,找末將是找對人了!”
聽慣了邊眾人客客氣氣的寒暄,韓啟江這靖北大漢都有的大嗓門兒一張,
溫婉總覺得有人在自己耳邊扯著嗓子吼。
努力出一個看起來不那麼勉強的笑容,溫婉客氣道:“如此,溫婉就先在這里謝過韓將軍了,還韓將軍莫要嫌我叨擾才是。”
韓啟江大大咧咧的擺手,“不會,公子說了,溫大小姐您是來教咱們弟兄們賺錢的,
早就聽說溫大小姐手下的華姝在短短兩年之躋天玄最負盛名的商行,
連皇商蘇家都自愧不如,您肯來我們這鳥不拉屎的地方幫忙,
弟兄們激不盡,能幫之,絕不推辭!”
溫婉訝然,既沒想到這看似狂的大漢竟然也對華姝頗為了解,
更驚訝他對自己的接程度竟然如此之高。
側首去看謝淵渟,后者沖粲然一笑,并不說什麼。
溫婉還在狐疑,集的馬蹄聲響起,揚起的塵土嗆的人眼淚之類。
一群人策馬疾馳,里喊著溫婉聽不懂的怪,吆喝著沖過來。
道路兩旁的攤檔被他們撞翻了也不管,一路走過來,便有好幾個行人丟了背囊,
還有婦人被走了發簪等金銀頭飾,
溫婉和溫璇也正好在路邊,那為首之人策馬過來,順手就要去搶溫璇背上的包裹,
溫婉眼神一冷,抓住馬背上人的腳腕用力一拉,人就被拖了下來。
馬兒驚,不顧主人還在原地,撒跑遠了。
“大哥!”
那人的幾個弟兄紛紛趕來,策馬馬圍著謝淵渟幾人兜著圈子嚇唬人。
被溫婉拽下馬的是個其貌不揚的中年男子,一瘸一拐的站起來,
惡聲惡氣道:“臭娘們兒,敢對老子手,你也不去打聽打聽老子是誰,
敢在太歲頭上土,老子娘的弄死你!”
那人說著舉起拳頭就朝溫婉打過來,卻被一道猥瑣的聲音阻止,
“大哥別呀,這小娘子長的多水靈啊,瞧瞧這穿打扮,肯定是城里的大小姐,
弟兄們還沒嘗過……”
嗷的一聲痛呼,卻是那人的兩顆門牙落了地。
畫屏甩了甩打疼了的手,恨聲道:“姐妹們,教訓這一群不長眼的,
好他們知道,咱們大小姐不是他們那狗眼可以覬覦的!”
一聲和,畫屏和輕羅、錦蘭錦玉齊上陣,銀燭和流螢形筆的站在溫婉面前,
大有誰敢冒犯溫婉,便與之同歸于盡的氣勢。
一群人迅速在鬧事中央打了起來,東見狀,也想出手幫忙,卻被謝淵渟抬手阻止。
只見幾個丫頭的拳腳麻麻如雨點一般落在那幾個人上,
期間有個瘦猴兒似的男人想逃,被輕羅一把拽回來,對著下三路就飛起一腳。
在場的男人們下意識的夾了雙,
謝淵渟更是想起了當初溫婉那和輕羅如出一轍的靈魂已腳,忍不住懷疑輕羅這招是不是跟溫婉學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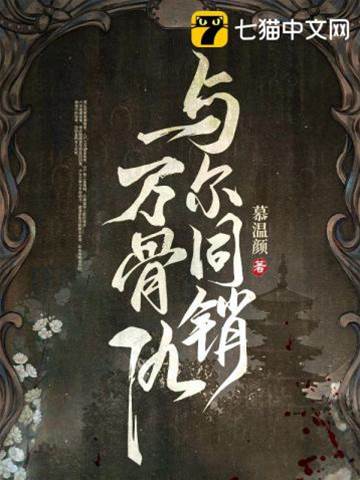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