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朕還傻》 第97章 番外:論重新搏得娘子的歡心有多難
蕭容洲近日來,心里有點堵。
他挑了一個最完的時間,最好看的姿態,最合適的時機,與人相認,結果人將他榨干了抹凈了,跑掉了。
蕭容洲心力猝的同時,外人都在傳他失寵一事。
“福德全。”
“在在在。”
福德全被重新安排在了蕭容洲邊伺候,五年不見,坐在面前前主子似乎威嚴更勝從前。
“阿煙去哪了?”
福德全一頓,將口中的話醞釀了半晌,方才開了口,“這個……今日科舉殿試結束,君在花園,設宴款待這批才子。老奴聽聞,今年的新科狀元是史大人獨子,年紀輕輕,儀表不凡,君在殿上很是賞識。”
明紫的袍在眼前拂,蕭容洲站起,揚了揚眉,“才子?儀表不凡?比我如何?”
福公公將頭低的更甚,“與您自是無法相提并論。”
“帶路。”
“啊?您去哪?”
“砸場子。”
就看誰敢撼他的位置!
今年新科狀元史大人獨子吳澤,二十五歲年華,氣宇軒昂。憑借一篇史論散文,一舉拿下今年狀元一席,得了君另眼相看。
花園設下的這場宴會,到場的皆是疆國年輕一輩的翹楚,公子和各家名門。
宴會開場之時,狀元吳澤與君席同坐,邊還跟著太子蕭安。怎麼看都像是一幅一家三口的絕畫面。
臺下眾人議論紛紛,對手者,都在支持吳澤與君今早婚,那樣吳澤的仕途就沒戲了,他們這群人就可以上位。看戲者,都在反對君與吳澤在一起,他們君要找君后,怎麼也得找個穩重,大度者。
走在一旁的太子蕭安,在計算自家老爹的勝算。
如果實在不行,不聲的將人‘除掉’的幾率到底有多大?
Advertisement
宴席開宴以后,吳澤親自走上前去給江明煙敬了一杯酒。
在燈的映照下,那坐在高坐上的君,如天上皎皎月,十分麗人。
現任君的事跡,近些年一直被說書人拿來當話本子傳頌,什麼一人可抵千軍,孤敵營,巾幗不讓須眉等等。如此英勇之人,神圣不可冒犯,但近距離與君相下來,吳澤倒是覺得君十分親切。
而江明煙現在腦子里想著的,卻是如果把蕭安掰過來。與一群大老爺們呆的時間太多,尤其是見了齊帝那個不靠譜的以及跟了蘇白風這麼多年,好好的一個太子,都學了什麼七八糟的。
他想著是不是能讓蕭安與文人多呆一呆,好熏陶熏陶自己的政治覺悟。
今年新科狀元吳澤本當不起親自設宴款待,但想著若是吳澤能給太子當個太傅幫他抬一抬價也未嘗不可。
手中舉著的酒杯就跟吳澤了,剛坐下,連翹急匆匆的從一旁跑了過來,低了聲音附在耳邊低語,
“君,聽皇帝宮的小太監來報,陛下不見了。”
江明煙皺了眉宇,“福德全不是跟在他邊?”
“福公公跟著一起出去的。”
江明煙心里一,害怕人出事,就站起來。
但一想到這邊正事,就同吳澤一笑道:“本君有些急事,先失陪片刻,吳公子別忘了與本君的約定。”
吳澤想到下午代他要照顧小太子當太傅一事,就一笑,“君放心,臣一定竭盡所能。太子就給臣,您放心去忙吧。”
兩個人的耳語落在眾人的眼中就又變了一個意味。
“吳澤與君如此親近莫非真的要當君后了?”
“三天前,君不是從大街上拐了一個男人回來,聽說很是寵幸。”
“一個男寵罷了,怎麼能跟正兒八經的世家公子比,能我們疆國君后之人那必是要文武雙全。”
一番爭論,除了男寵兩個字蕭容洲不敢茍同以外,其余倒是十分贊同。能與比肩之人,自是應該文武雙全。
蕭容洲走進來的時候,江明煙剛剛離開,看著上座吳澤與兒子坐在一起的模樣,蕭容洲瞇了瞇眼睛。
卻又因江明煙不在此而長舒了一口氣。
他拉過一旁婢問了一句,“君去哪了?”
那婢是近些年方才進宮之人,本就不認識蕭容洲,但猛地見到如此俊之人倒是一愣之后趕忙低下頭,“君有事,剛剛離開。”
蕭容洲余之間瞧見了隨后跟來的福德全,轉就走。
哪知蕭容洲此人氣場太過強大,再加上那張難以令人忘懷的容,一時間引了在場的世家公子紛紛回頭來看。
高座之上本是坐的有些不耐煩的蕭安因為自家老爹而來坐直了,他剛想出聲,就被一旁坐著的吳澤按住了手。
“太子莫怕。”
他既然擔了一個留守控場之責那此時萬不能退,到時候君就會覺得他能力不足對他印象大大降低,因此在同太子蕭安回過話之后,就站起,低喝出聲,“什麼人?竟然敢善闖宴會。”
本是走的腳步因為他的話倏然頓住,他偏過頭去看了高臺之上坐著的吳澤一眼,如桃花一般好看的勾起。
五年不在,現在的小子倒是越發的猖狂。
蕭容洲調轉腳步走了宴會里當中,璀璨的燈照耀在他明紫的決之上。沒了任何偽裝的蕭容洲,黝黑深邃的瞳仁中多了一抹玩味,他不不慢的走進來的姿態優雅從容,像極了坐于高位之上王者。
他走到場中央,眼眸微垂,“擅闖又如何?”
單是論氣度,吳澤就不能與蕭容洲相提并論,尤其是在他看過來之后,更是被質問而得啞口無言。
幸得一旁的婢機靈,俯在這位狀元爺耳邊道:“這位就是君帶回來的男寵。”
聲音本是不大,但在蕭容洲進來以后,場面一度雀無聲,此時更是被在場的人聽得一清二楚。
有人當即笑出聲來,“我當是誰,原來你就是君幾天前帶回來的男寵。”
“不,他是爹爹。”
太子蕭安想給自家老爹洗白,可卻被人趕忙止住,“太子殿下,飯可以吃但話不能說,一個男寵而已,還當不上殿下的父君。”
臺下之人議論更多,吳澤皺了皺眉,抬手制止,“這件事就當什麼都沒看見,這位公子您還是請回吧。”
“本座這輩子留在別人口中的名號頗多,男寵這個詞倒是頗為新鮮,只不過,從你們口中說出來倒是十分刺耳。”他抬手掏了掏耳朵,說出來的話,禍及了在場的每個人。
“誰給你的膽子如此猖狂,口氣倒是不小。你知不知道這場宴會乃是君親自舉辦,搞砸了宴會,君定然會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蕭容洲一拂袖,將在場的每個人看了一圈,“還真別說,本座仗著的就是君的寵。”
蘇叔叔曾經告訴過他,他的爹爹是一個十分沒有臉皮之人,他起初還不相信,但今日當著這麼多人的面,還能面不紅心不跳,沉穩優雅的說出來這麼不要臉的一句話,他爹爹真的是頭一個。他總算是看出來了,他的毒舌不是后期學的,乃是天。
正所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正是這麼個道理。
他抬手扶了扶額頭,努力思索著怎麼把這件事給解決掉,就在這時,外面響起了一陣,接著,眾人就瞧見君去而復返。
“臣等參見君。”
眾人心里都給蕭容洲點了一個蠟,祈禱這人一會還活著。
然而就在眾人心中肺腑的時候,余里就瞧見君急匆匆趕來,走到那人邊,怒道:“你怎麼跑這里來了?你知不知道讓本君一通好找,本君還以為你……”
完了,這人怕是要涼了。
蕭容洲挑了挑眉,打斷了的話,“你兩天未回皇帝宮,他們都說本座失寵了。”
“本君沒有回去是因為……”
因為腰快斷了好嗎!!!!!
江明煙掃了在場的人一圈,怒道:“這話誰說的?”
眾人大驚,這男寵的手段這麼高的嗎?三言兩語兩君哄這樣?
蕭容洲默了默又道:“他們還說我要是搞砸了宴會,你會讓我吃不了兜著走。”
眾人:“!!”
“蕭安。”
被娘親點了名字,蕭安從高座上走下來,“母君。”
“你為太子,怎麼不護著點你的父君,”
父君的樣子像是了委屈嗎?明明是占了大便宜好嗎??
蕭安沖著兩個人拱手一一一拜,“父君母君說的對,兒臣謹記。”
蕭安說完直起腰,看著四周面面相覷的眾人,擲地有聲的開口道:“你們都搞錯了,他不是母君的男寵,他是本太子的父君,是親生的父君。”
太子殿下的親生父君的話,這人豈不就是那傳言中已經去世多年的先帝……
“還是男寵好。”
眾人:“!!!”
江明煙也疑的嗯了一聲,蕭容洲將人打橫抱起,垂眸淺笑,“男寵男寵就要獨寵一人,如此甚好。”
后來,江明煙又懷了孕,打算將一干政事推給蕭容洲,那時蕭容洲正在一旁正在教兒子親親抱抱舉高高。
行吧,忍了。
再后來,三年抱倆的江明煙忍無可忍,撂挑子不干了。那時候蕭容洲說了什麼來著?
“阿煙,不干了好,正巧前幾天安兒說想要個妹妹,不如我們……”
別,我干,我干還不?
再后來的后來,疆國永安八年,帝后同治于朝堂,史稱‘永安盛世’。
全文完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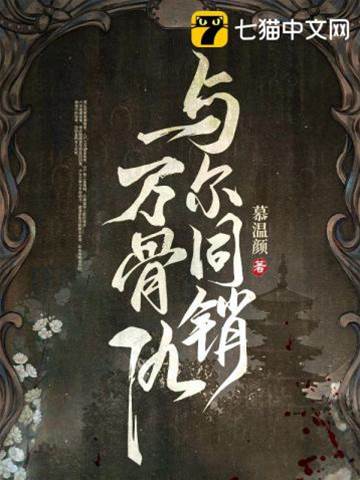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