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派他過分美麗》 第70章
“清靜君”側了劍刃,竭力朝下劈斬,霜藍的劍花一路落至徐行之劍柄,眼看劍刃距他握劍的右手手指不過咫尺,徐行之當機立斷,令“閒筆”重化摺扇,與那灼燙劍鋒鏗然錯開,自己也趁勢撤開形。
誰想他腳還沒站穩,劍鋒又已至前,徐行之只靠本能,刷的展開扇面,只見下一瞬,“緣君”劍尖便直撞上了他護於心口前的扇面,濺起一空碧碎屑。
徐行之來不及錯愕,立即將摺扇猛合,用扇面暫時吞住劍尖,押住劍勢,往左側下一推,一,飛騰起,子淩空一旋,那“閒筆”便已化了千點寒芒星針,朝來人面門擲去!
徐行之此招雖然損,換了旁人是萬萬避不開的,但就他對清靜君的瞭解,避開這些個針芒絕非難事,他也好靠這一手短暫地拖延住清靜君的攻速,再思量反攻之法。
沒想到,他剛一落地,便覺右肩一痛,他及時單腳往地面一點,避開了“緣君”主鋒,但肩膀還是被劍挑落出一道碧。
……“清靜君”對他甩出的寒針暗竟是避也不避,能用劍鋒開的便開,躲不開的,居然就任那寒芒紮皮之中!
徐行之抵死也想不到師父會採取此等以傷換傷的淩厲攻勢,也要向他進攻!
……這樣的打法,倒像是同自己有什麼深仇大恨,非要取自己命不可……
擂臺之下的溫雪塵猝然那元嬰期靈衝擊,不覺低一聲,曲彎下腰,死死捉住前裳,虧得曲馳反應及時,掌心凝,以靈制了一面護心鏡,遮擋在溫雪塵心口,好歹是護住了他的心脈。
周弦下這一波衝擊,馬上俯去查看溫雪塵的狀況。
Advertisement
已盤起了婦人髮髻,但頸肩修頎,姿如柳,顧盼之間仍是的靈神韻:“塵哥,如何了?”
溫雪塵擺一擺手,示意自己無事。
周北南確認周弦與溫雪塵無恙,方才把目投向擂臺,瞥見徐行之肩上沁出的痕和破損的服,臉驟然變青:“清靜君這是怎麼了?”
滿空激的狂暴劍氣,讓本來認定清靜君所謂的比試不過是耍圈花槍走個過場的眾家弟子及君長們瞠目結舌。
短暫鋒後,元如晝早已急出一冷汗,也顧不得什麼禮節,焦灼地對廣府君道:“師父!這不是切磋嗎?清靜君為何要對師兄……”
接下來的話不敢再說。
但在場諸人心中都不免生出與相同的念頭:
……清靜君怎麼像是要對徐行之下殺手?
於風暴中心的徐行之,對這種莫名的殺意得最為明確,但他毫顧不得思考究竟為何會變這樣。
徐行之毫不懷疑,若是自己遲滯了一步,師父絕對會將他的頭顱橫劍削下!
他將“閒筆”化為重劍,握於左手,掛定風聲,將形化作萬千虛影,同樣運起元嬰靈氣,縱月白的劍橫貫斬下,數道影並起,誰也不知道本在何。
然而在合攻中心的“清靜君”卻毫不,他有條不紊地接下每一道攻擊,所謂虛實變幻,於他極致的劍速而言,不過是小小的伎倆而已。
劍勢過,掃六合,雪迸!
他角開一猙獰的笑容。
陡然間,數十道劍收攏起來,凝聚一道白綢緞淩空舞起,直奔他面門而來,“清靜君”輕揮劍鋒,便破開了那白綢。
他能夠料想到,在這白綢之後,八藏著一個提著劍蓄勢待發的徐行之。
此等掩人耳目的把戲,也敢拿出來丟人現眼?
……他甚至已經可以想見那姓徐的小子的腦袋在自己劍下西瓜似的綻開時紅紅白白的場景了。
誰想,他劈開了白綢後,迎面朝他而來的竟是一道澤渾濁的!
他饒是行如風,也無法在做好斬殺敵手的準備時移軀,猝然被潑了個正著。
那難聞的順著他的頭臉汩汩湧下,他抬手一抹,嗅到指間的氣味,便瞬間變了。
……鬆油?
他膽敢用這東西來辱自己?
不,他難道是要用火?
剛冒出這一念頭,他便本能地調集靈力,在掌中掐上了一道水訣,以備不時之需。
他抬頭一,發現徐行之果然在擂臺對角側凝神掐訣,但他跡斑駁的臉頰上出的那抹笑容,怎麼看怎麼莫名。
轉瞬間,他上的鬆油便了徐行之的念訣,起了些靜,但卻並未如他想像中燃燒起來,而是將他上被細雨及鬆油沾的地方,都凍結了寸厚的寒冰!
“清靜君”頭臉被鬆油潑了個正著,凝結的霜凍讓他的視線變得一片模糊,當他剛用靈力震碎那該死的冰塊時,便覺右肩一沉。
旋即,一道寒涼橫陳在了他的頸間。
徐行之蹲踞在了他的肩膀上,左手持拿匕首,抵住了他因為中計氣惱而鼓凸出來的頸脈。
他朗聲笑道:“師父,承讓。”
眼見徐行之轉瞬間扭轉了局勢,方才還提心吊膽的元如晝才有了些許歡,周北南他們也勉強鬆了一口氣。
溫雪塵低聲道:“似乎有些奇怪。”
周北南也表示贊同:“清靜君……”
他才說出這三個字來,便聽擂臺上傳來一聲尖銳的帛撕裂之聲。
清靜君竟在已明確落敗的境況下,出其不意地再度驅了元嬰靈!
徐行之未曾防備,被得倒飛而出,落於擂臺上,又倒退數步,以曲跪之姿方才止住退勢。
然而他的上生生在靈迫之下四散炸裂開來,出了寬窄適宜、遒勁漂亮的上。
眼見此景,底下的弟子轟然一聲炸開了鍋。
徐行之只知自己背上有陳年的銀環蛇印傷口,以往他從不示人,這回突然曝在眾目睽睽之下,徐行之心知會引起不小的波瀾,但卻沒想到眾弟子竟像是見了鬼似的,對著他指指點點。
他茫然回轉過,將目對準了周北南他們。
……出什麼事兒了?
他未曾想到,周北南、曲馳與溫雪塵三人竟是一樣,面煞白地盯著他,彷彿……看到了什麼了不得的怪。
“清靜君”抖去一狼狽又骯髒的碎冰,回過半張臉,在徐行之看不見的地方,勾出一個人膝頭發的邪笑。
從剛才起就對師兄的種種反常舉心生不安的廣府君,在瞧清徐行之上的痕跡後,立時明白,師兄今日為何要對徐行之痛下殺手了!
他一聲斷喝:“徐行之,跪下!!”
徐行之莫名其妙,但師門之命他向來不會違拗,便在擂臺之上單膝下拜:“師叔,方才弟子也是非得已,不是故意折辱師父……”
廣府君咬著牙齒,字字飽含怒意:“徐行之,我問你,你背上的是什麼?!”
徐行之看不見自己的後背此時是怎樣一番景。
——在他的後背靠脊柱中央,原本烙下銀環蛇印的傷已經不見,而在原先的傷,竟無端生出一塊半拳大小的青綠流駁紋!
清涼谷弟子隊伍之中的陸九瞧見那悉的駁紋,猛地住了自己大附近的袍,眸中流出難以置信之。
是……是鬼族的刻印?
徐師兄……是,是鬼族?也是鳴國後裔?
他再定睛去看,卻發現那紋路有些古怪,其流倒逆,與他大側的鬼族刻印的順向流全然不同。
……假的?刻印是假的!
作者有話要說: 但是,在場之人既非鳴國人,不瞭解這刻印的奧,又離得遠,看不分明,本察覺不到這細小的差異。
徐行之毫不知自己後背被人做了什麼手腳,但他自覺銀環蛇印也不是什麼難以辨認之,便垂下頭,不多加辯解。
廣府君見徐行之不答,便當他是心虛,冷笑數聲,道:“徐行之,我且問你,你為何從不當眾解?是不是……有什麼不能為人言說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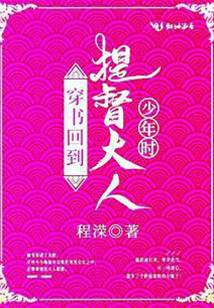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543 -
完結333 章

日日索吻!隻怪我太美,他太黏!
(穿書 重生,高甜,嬌軟,病嬌,娛樂圈)許知歲穿成了惡毒女配,想抱大腿卻在新婚夜死在了反派大佬床上。從小說世界回到現實,竟帶回了小說中的反派大佬。許知歲:這個大腿得繼續抱!不近女色的沈四爺忽然被人抱住叫老公。就在大家以為沈四爺會將人一腳踹飛時,沈遂之看著懷中的姑娘低聲溫柔,“要跟我回家嗎?”眾人:“……”從此沈四爺的心尖有了寶,她眼圈一紅他就頭痛。夜深人靜時,他壓抑著兩輩子的瘋狂低聲誘哄,“寶貝別哭了,再哭,命都沒了。”
61.4萬字7.92 16125 -
連載378 章

八零嬌女一撒嬌,高冷軍少領證了
【位高權重軍中禁欲團長vs農村嬌美溫軟大學生,穿書,雙潔】坐火車回家的霍梟寒懷里突然摔進一個嬌軟美人。 女子紅唇鮮嫩,呵氣如蘭。 霍梟寒一時心動,發現竟是仗著對他家有恩,朝秦暮楚、愛慕虛榮,被他厭惡拒絕的相親對象。 自那后,霍梟寒一想到,夜夜不能寐! 蘇婉穿成了年代文惡毒作精女配。 原主黑料多的洗不掉,她只好勤勤懇懇考大學,努力避開霍梟寒,卻被霍梟寒處處約束、管制、教育。 直到男人幫她開完家長會,拿著她告訴家里人處上對象的信。 禁欲高冷的老男人,緊繃著下頜線:“婉婉,畢業前不允許處對象,要處只能跟我處。”
64.6萬字8 121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