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落春夜》 第59章
同一個夜晚, 有人在相擁而眠,也有人在相互撕扯。
千里之外的某個別墅,郁家澤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廳里, 開了一瓶酒, 已經喝了大半。
但這點酒似乎對他沒什麼影響,他的臉依舊是蒼白的雪, 如同暗夜里的族,獨守空寂的城堡一隅。
自從烏蔓離開后,整棟房子變得毫沒有人間煙火氣。
流離臺邊似乎還有做飯的背影, 沙發的左邊是喜歡的位置,好像剛離座, 還在地毯上沒有聲息地走。
因此,當他聽到大門口傳來鎖匙的靜時, 整個人一驚,立即扭頭向門口去。
進來的人和他的小鳥有三分相似的臉孔,卻是一個假冒的劣質品。
他的視線潦草地在唐映雪臉上巡回了一圈,便轉回了頭。
唐映雪不太開心地說:“你怎麼搬回來了也不和我講一下?”
自顧自地開燈,驟然亮起的線讓郁家澤不由得瞇起眼睛。
他用命令的口吻:“關掉。”
“……”唐映雪微微一怔, 爾后撒道:“可是家澤哥哥,我怕黑。”
郁家澤揚起沒有溫度的笑意,拍了拍他旁邊的位置:“那就坐到我邊來。”
唐映雪微微一怔, 立刻雀躍地關掉燈, 依偎到他邊。
挨上郁家澤的肩頭, 他的手有一搭沒一搭地順著的發,這讓心跳加快,覺到一種過分的親呢。
郁家澤在黑暗中忽然冷不丁地問:“你為什麼想要和我結婚?”
“因為我你。”
唐映雪毫不猶豫地回答。
郁家澤輕笑了一聲:“哪怕我本不會你?”
倚在他肩頭的側臉微微僵,抬起頭看向郁家澤, 咬著牙問:“那你誰?別告訴我是烏蔓!”
Advertisement
郁家澤聞言悶悶地笑了起來。
“誰告訴你人一定要人?”他憐憫地了的頭,“迄今為止,我只過一只鳥。”
“……鳥?”唐映雪蹙著眉,恍然地想起了什麼,“是郁伯伯提到過的那只八哥吧?你要是喜歡,我再買一只送你。”
“不是每只鳥都能像它那麼有趣的。”
郁家澤反扣住吊腳杯,形狀宛如一座鳥籠。他點著空的杯壁外延,呢喃道:“就是因為太有趣了,如此昂貴的水晶杯也困不住它。”
唐映雪有點發地了自己的胳膊,總覺的他的語氣不像是在說什麼鳥,而是一個人。
不樂意地掰過郁家澤的臉,將他的視線從杯子移到自己的臉上。
要他只看著。
郁家澤冷冷地看了一眼的手,唐映雪猶豫了一下,還是收了回來,轉而挽住他的胳膊撒道。
“家澤哥哥,這幾天我好閑啊。郁伯伯說你不是要去國嗎,帶我一起去玩兒吧?然后婚后月我們再去個別的地方。”
“老頭子沒告訴你我是去出差理正事嗎?”郁家澤快速地轉著手中的尾戒,“你很閑是你的事,我沒著你退圈。”
“可我這是為了你啊……你難道希你的妻子,郁家未來的夫人在外面拋頭面被別人評頭論足嗎?”
郁家澤背靠在沙發上,淡淡瞥了一眼說:“我無所謂。”
唐映雪被這句話說得一愣。
但很快安自己,郁家澤和年齡差得很多,在眼里很重要的事,也許在他眼里并不值得一提。想要全心奉獻于他,可也許,他希自己也能有事業?
不愧是看中的男人,又有思想。
唐映雪展笑道:“但我還是更想陪在你邊。”
話音剛落,郁家澤神一凜,鷙的眼神猛地懾住。
“不要……讓我聽到第二遍。”他干脆地下了逐客令,“我累了,你回去吧。”
唐映雪也惱了:“為什麼你一直不愿意讓我留下來陪你過夜?”
“這是你爸的意思,要等結婚。”
“可是我們已經訂婚了啊。”唐映雪狐疑地左看右看,“你是不是又養了別的人?你上次就在騙我!”
郁家澤坦然地揚了揚下:“隨便你上樓找,你能找到就是你的本事。”
唐映雪盯著他的眼睛:“你如果騙我,我就去向郁伯伯告……”
這一回,話都來不及說完,便被郁家澤掐住了脖子,將剩下的話卡了下去。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對你,我已經用了很大的耐心。”郁家澤緩聲細語,“如果你認為一直搬出老頭子有用,那你就去。”
郁家澤的手離開了,唐映雪卻還驚魂未定。
那一刻,仿佛他真的就是一只吸鬼,而自己的脈會折于他的手中。
他眼中的狠戾更是過,投向了話語背后的那個人。
夜半四點,烏蔓的老病又犯了,依舊在這個點驚醒。
后的追野睡得很沉,抱還抱得很。不想吵醒他,于是被迫讓自己再度閉上眼睛,催眠自己再睡著。
但是這難的,如果沒有吃藥,自然睡著再醒的話,很難再次睡。
于是眼地維持著同一個姿勢尸半天,最終實在覺得難,想起來去臺煙。
非常小心翼翼地,用升格鏡頭的速度將自己從追野的懷抱中出來。卻在這個緩慢的過程中意外扭到了小的筋。
……天。
烏蔓當即不小心痛出聲,又反應過來立刻咬住。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真的年紀上來了,筋絡和骨頭都覺得有些脆弱,扭到也不是一次兩次了。這麼想著烏蔓突然覺得有點搞笑的悲傷。
在這半夜突如其來涌上來的傷和依舊還在的痛苦中來回反跳,卻不期然聽見后那個睡得死沉的人模糊地說:“怎麼了阿姐?”
烏蔓忍不住懊惱自己還是吵醒了他,回過一看,這人眼睛還閉著……
“沒事,你睡吧。”
輕聲哄他,他卻似乎應到了著他的地方在搐,一把從床上支楞起來,將的在自己暖和的小腹上,半閉著眼替。
這一系列作看上去就像是在夢游。
他勉強半睜開眼睛,迷迷瞪瞪地說:“是不是這個地方到了?”
烏蔓愣愣地看著他,小聲地嗯了一下。
想二十來歲的時候,好不容易拍攝完能出幾個鐘頭睡個覺,別說房子著火,就算世界末日了,也要閉著眼和床纏綿。
怎麼可能會因為邊人默默地了個筋就從睡夢里發現,沒清醒完全就靠著下意識爬起來替對方心甘愿地。
本抑制不住腔里那無法言說的容,猛地跟著直起抱住他的腰。
兩人像不倒翁似的,搖搖晃晃地倒到了床尾。追野在下,趴在他的口,抬起眼一眨不眨地盯著他。
追野終于被這麼大陣仗弄得清醒了,抬手摟住的腰,沙啞著說:“我現在在做夢嗎?”
“嗯?”
他笑得恍恍惚惚:“阿姐在主抱我。”
烏蔓板起臉,認真切嚴肅地了聲他的名字:“追野。”
“啊?”
他的頓時繃起來,不知道自己哪里惹了。
“我是不是到現在為止,都還沒主地跟你說過……”突然收聲,好半天才出三個字,卻擲地有聲,“我你。”
追野微張著,心臟仿佛在里蹦了個極。重重地沉了一下,又迅速飛躍到嗓子眼。接著又往回,來回跳得那麼劇烈,久久不能平息。
阿姐的就像是一顆封閉千年的蚌類化石,總是那麼固執又堅。從不輕易袒里頭的。
他也不急著打開,就打算和死磕,從邊緣撬起,一點一點地掉外頭風化凝固的沙子。
只是這顆小化石,就這麼猝不及防地對著他投降了。
因為從頭到尾,小化石就是紙糊的脆弱堡壘。只需要鼻酸時會將向膛的懷抱,還有筋時慌張過來的雙手,就會潰不軍。
要的,就是這麼一點點心無旁騖的溫暖。
追野深深地吸了口氣,在烏蔓來不及反應的瞬間翻過,將在下,位置顛倒。
他的眼睛在黑暗的房間里明亮得如一顆恒星。
“阿姐,我也你。”他沒有任何一遲疑,“這一生不會再有第二個人了。”
烏蔓在聽到的當下這個瞬間,毫無疑問是的。
但是理智卻告訴,不要太過當真。
三十歲說的我你,和二十歲說的我你,是完全兩種不同的分量。
年人總是喜歡在第一時間將自己充沛的外泄,想要天長,想要地久,想要這一刻為永恒。
可是世界上哪里存在什麼永恒呢?
曾經有一次,有家采訪,其中一個問題如此問道:這世界上你最討厭的一個詞語是什麼?
回答的是:永恒。
“一生沒有你想象得那麼短。”烏蔓手著他的側臉,“擁有眼下就夠了,不用給我什麼承諾。”
“你不相信嗎?”
他有些孩子氣地發問。
烏蔓沒有回答,只是笑著仰起頭,親了親他藏著不甘心的眼睛。
“阿姐,對我而言,我覺得人的一生真的很短。”他反手將抱住,攏進自己的懷里,下抵著的頭呢喃,“我媽在我八歲那年去世了,走之前還那麼年輕有活力,如果拿起撣子收拾我可以追著我繞屋里跑十圈那種。”
“走之后我和我爸相依為命,我就是那時候學會的煮飯。因為我爸被我媽慣得太好了,什麼都不會。所以一走,他連怎麼活都不會了。”
“我十二歲那年放學回來,他倒在桌子邊,面前一瓶空啤酒罐,還有一瓶空了的百草枯。他為了我生生又堅持了四年,很了不起。”
“然后我就被接去和我爺一起生活。在我十五歲那年腦溢走的,走后不到半年,爺爺也跟著走了。從此,我就是一個人。一直到現在。”
凌晨四點天空還一片漆黑的昏暗房間,日出還沒有來,他抱著的雙臂不由自主地:“你看,人的一生是不是很短?甚至一把癮都過不了就得死。”
那些塵封的艱難往事被他三言兩語輕描淡寫地講出來,烏蔓了眼角,發現自己無意識地流出了眼淚。
太苦了,饒是的年那麼艱難,也無法想象他的苦難。
從來沒得到過,總比得到過又失去來得好。
更何況是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如同一場曠日持久的地震,伴隨著經年的余震,冷不丁地將他的摯從他的人生里走。
就像一個人被打開了心臟,又挖去。
“在青泠,他們都傳我是掃把星。”追野滿不在乎地說,“那就掃把星好了,反正我的人生也沒什麼可以失去的了。”他的語氣一頓,突然低下去,出了潛藏在滿不在乎底下的脆弱,“……但阿姐,其實我心里很怕。尤其在抱著你的這個時候。”
烏蔓知道他想說什麼,快一步地手,捂住了他的。
“你不用害怕。”吸著鼻子,在他的頸窩輕蹭,故作輕松道,“我可是不被待見來到這個人間的,命得要死,正好和你天生一對。”
追野許久沒說話。
良久,他的聲音很輕,又很堅定地說:“如果哪天你真的離開了,那我會跟著你離開。”
烏蔓的靈魂被劇烈地敲打了一下。
有些來氣道:“我比你年長那麼多,比你早離開是很正常的。你別那麼任!”
他帶著濃濃的鼻音,笑了一下。
“我不管,我已經被他們丟下了,不要再被你丟下了。”他吻了吻的頭頂,“我你,所以不要丟下我一個人,好好活著,和我一起。”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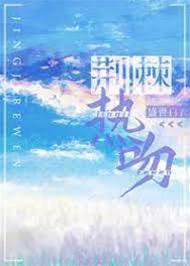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