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進酒》 第88章 帝師
清風徐來, 涼夜生寒。
蕭馳野適才的殺意都讓這一聲“二郎”驅散了八分, 他沉默半晌,在涼爽里平復了心緒。
沈澤川再看回葛青青, 面上沒有半分慌張, 說:“想要運轉這麼多的白銀, 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夠做到的事。他辦得再干凈,也不能瞞天過海。今夜就召集人手出城, 先去琴州, 沿途細細打聽,把近兩年厥西往東北的大貨買賣都記錄起來, 讓人敷陳給我。”
葛青青收到消息后一直憂心忡忡, 但見沈澤川談笑自若, 不心下稍松,也穩住了緒。
“晨,”蕭馳野肩頭掛著袍子,示意道, “先帶他們去闃都會同館, 懸掛中等馬匹的牌子, 配給緝拿江洋大盜的公文,就說大盜流竄厥西,軍不便出都追拿,便委托給了錦衛。明早我親自去趟兵部和刑部,做個呈報。”
城門已閉,不能隨意出都, 錦衛又涉及緝查逮捕的重任,平時出都外勤都要先稟報刑部和都察院,然后等候批復。蕭馳野這是給了葛青青帶人出都的理由,免了刑部的后續責問。
葛青青得令立刻就走,晨披帶路,兩個人先行出了宅子。
沈澤川穿得單薄,蕭馳野把人牽回來,帶進門時看他還在沉思,便說:“先生的事和薛修卓也不開關系,但他既然肯把人轉移走,就說明先生對他而言還有用,他就不會貿然對先生痛下殺手。薛府里藏的事太多,我得想個理由,從皇上那里討一份搜捕特令。”
“想要出軍,必須得是證據確鑿的大案,現如今的試探還是要靠錦衛。”沈澤川沒有坐回原位,他見天不早,便知道今夜又難休息,于是倒了杯釅茶,卻只含了一口,剩余的都給了蕭馳野。
Advertisement
蕭馳野喝完了,說:“薛修卓事事謹慎,平常外歸都孝敬的冰敬,他也一概不收。他任職都給事中期間,在都察院言眼里最干凈,甚人彈劾,所以就算是錦衛,恐怕也難以找到理由去查他。”
“大張旗鼓地查,就會打草驚蛇。”沈澤川把玩著茶杯,在苦味里思量著,“他在明,我們在暗,薛修易這步棋只要藏好了,我們就仍舊是進攻的那一方。宮外事皆好說,但是宮事,卻要更加留心。他既然已經對皇上起了殺心,又有慕如風泉姐弟倆相助,對皇上的一舉一了如指掌,讓人不得不防。”
蕭馳野想了一會兒,說:“風泉不是才了司禮監掌印太監麼?憑他的資歷,必定會外朝一起責難。福滿頂在他下邊拳掌,海良宜又厭惡宦,風泉如今擔任的掌印,可比不了潘如貴時期的權勢。讓他外困,自顧不暇,他就沒有余力再替薛修卓辦事。”
“穩住皇上也是關鍵,”沈澤川說,“皇嗣一事,不能傳出風聲。”
李建恒登基以來,多言的苛責,又接二連三地出事遇險。他沒有漂亮的政績,在民間的名聲也不如先帝,如果皇嗣一事走了風聲,必定會人心浮,從哪方面講,都不利于維持穩局。
“不論薛修卓手里握的是真龍還是假龍,”蕭馳野抵著骨扳指,盯著琉璃燈,“大周的皇帝都只能是李建恒。即便日后要立儲君,那也得立李建恒的兒子。”
蕭家如今略勝花家,又保持著勢頭。蕭馳野走得穩,在離北的蕭既明也守得穩,他們跟世家在中博、啟東暗地里博弈,大家打得不激烈,就是因為有直臣海良宜一派居中調解,勉強穩住了二虎斗的趨勢。然而海良宜最大的屏障就是李建恒,李建恒肯信他、敬他,知道他的不二心,所以在拉鋸戰中沒有立刻倒向太后,并且朝中的大小事,李建恒都肯拿出來與海良宜商議,這就是海良宜新朝后穩坐閣元輔的本原因。
李建恒這個人不重要,但他登基以后,“李建恒”就變得至關重要。他在明槍暗箭里居于中心,他就是三方共同制約對方的牢籠,他也是三方共同攻擊對方的匕首。
薛修卓已經浮現出來了,沈澤川在尋找突破點的空隙里,也要忍不住去想,薛修卓的背后還有沒有人。
* * *
幾日后小雨,薛修卓休沐。
他著著天青實地綢袍,拜會了小樓里的齊惠連。齊惠連大嚼著飯菜,連看也不看他一眼。
薛修卓沒有上桌,行的也是弟子禮。他見紀綱坐在窗前磨石頭,便對左右說:“紀老傷勢未愈,忌口辛辣,去讓端州的廚子重新做一桌菜肴。”
“不必勞駕,”紀綱吹著灰屑,沉聲說,“我不吃。”
薛修卓沒有開口,那伺候的人便已經退下去囑咐廚子。薛氏是晉城大家,吃不慣中博風味,這端州的廚子,是他專門為紀綱聘來的。
樓外小雨淅淅瀝瀝,四月有杏,院里的白都被雨打了泥。齊惠連吃飽喝足,拭了,起看那院里的凄涼,說:“甭費那功夫,他紀綱犟得很,不吃就是不吃,你人備點饅頭咸菜讓他充就行了。”
薛修卓含笑:“二位前輩來我家中做客,我不能輕慢了去。”
“那你打開門,”紀綱給石頭雕著鼻子眼睛,“我們自個兒能回去。”
薛修卓神不變,說:“近來春寒,我看沈同知自己都尚無定居之,又如何能安頓得好二位前輩?”
“你在咱們跟前拿腔拿調,囚|就說囚|。”齊惠連走幾步,腳踝上的鐵鏈跟著發出聲音,他說,“我這輩子讓人囚來囚去,也快到頭了。我老,他殘,你把我們兩個老弱病殘拿在手中,是想干什麼?”
薛修卓親自俯,為齊惠連拾起他撥在地上的筷子,拿著帕子拭,說:“先生過去是彪炳春秋的人,本有后太廟供奉的尊榮,可惜跟錯了人,在那昭罪寺里裝瘋賣傻二十年。如今,我想請先生再做帝師,一來可以彌補先生當年沒有看見太子登基大典的憾,二來可以洗清先生的冤屈,讓先生重整冠,堂堂正正地回到萬眾眼前。這兩個理由不夠充足嗎?我是尊敬仰慕先生的人。”
“再做帝師,”齊惠連拖著鐵鏈倒退一步,中發出笑聲,“你想要我再做帝師?你好大的口氣!如今四海升平,當今皇上名正言順,有那海仁時看顧輔佐,還要我齊惠連干什麼?我又瘋又傻,本當不了大用!”
薛修卓擱下筷子,說:“先生人污蔑,才會落得如此下場。太后在永宜年間把持朝政,導致大周朝綱顛倒,貪橫行。咸德年間更是如此,花、潘狼狽為,在闃都,在八城,在整個大周興風作浪,各地百姓苦不堪言。而后中博兵敗,六州哀鴻遍野,殍載道。先生在昭罪寺里空度二十年,如今出來了,卻已經失去了當年揮斥方遒的豪邁英氣,連與海良宜一爭高下的心也沒有了嗎?”
齊惠連轉,扶著窗,看那雨水敲打著杏花,沉默須臾,說:“二十五年前,我是想要與海良宜爭個高下。我們同赴科考,他那般不起眼,我卻連中三元。我年得意,不懂場迂回,人構陷,被貶斥出都,自覺無見渝州父老,便沉郁了幾年。后來海良宜提拔擢升,太子卻沒有拜他,而是把我從渝州迎回闃都,從此我便做了東宮太傅,兼任吏部尚書。海良宜這一生都敗在齊惠連名下,可他是個君子,太子自刎時人人喊打,唯獨他還存有挽回之心,就沖這一點,我不如他!我們之間沒有高低,只有相惜。可嘆蒼天無眼,我們是即便道路相同,也仍然不能共事的人。我困二十五年,你說得不錯,我如今已經沒有再與他一爭高下的心了。”
薛修卓也沉默下去,房間里只有雨聲和紀綱雕琢的刮磨聲。雨下大了,杏花掉得更紛,在泥水間鋪就一片殘。
“我這輩子只教了兩個人,都是傾盡畢生所學。我自負才高,不肯將就,正是這樣的恃才狂傲,才害苦了第一個學生。”齊惠連著那殘瓣臟水,猶如著自己潦倒的半生。他說:“我齊惠連到底不是神仙,有兩個學生足夠了,別的人,我教不起。”
紀綱劇烈咳嗽起來,用帕子掩了口,埋怨道:“關窗吧!”
齊惠連把那些景都關在外邊,回頭看著薛修卓,說:“我言已至此,你休要糾纏!走吧,別留在這里礙眼。”
薛修卓不,他和薛修易長得不像,他甚至不像是世家子弟。他沒有潘藺、費適的那種驕矜,庶子的份讓他在過去數十年里吃盡了苦頭,他已然被打磨了這樣不鋒芒的儒雅。
“我仰慕先生的才學,更仰慕先生的知世之道。我三顧小樓,求請先生出山,是因為我明白先生的抱負。先生,海良宜確實是個崖岸高峻的君子,可是君子向來不能與小人長存。如今的皇上不詩書教導,沒有禮賢下士的仁心,他只是這大周崩塌之勢下的一稻草,他本不了圣賢之君。海良宜還有多余力?把社稷安危寄于他一人之,本就是尊卑顛倒,誤了輕重。”
齊惠連說:“輔佐君主,本就是臣子天職。海良宜力挽頹勢,調和八方,他是在盡力而為。他是忠臣,難道你還想要他做個頂替李氏,改朝換代的臣賊子嗎?”
“世家與寒門的斗爭百年不休,想要剔除痼弊,就得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薛修卓起,說,“李建恒不行,還有別人。大周是李氏江山,只要李氏的脈猶存,那麼為渡難關,換個人也在理之中。”
齊惠連與他看法相左,只把他當作弄權謀私的世家子,不肯再與他談。
薛修卓默立須臾,說:“我與先生,也是同道中人。只可惜先生不信我,但我也要與先生說,沈澤川是含恨殘的余孽,他心無外,只為報仇而活。他行事狠辣,為人狹隘,與太子相差甚遠,先生以教帝王之心去教他,無異于為虎作倀。即便來日他有所作為,也不會是良主。”
紀綱猛地擱下刻刀,對薛修卓怒目而視,說:“你懂川兒多?你們口口聲聲喊他是余孽,可我看你們才個個都是食髓余孽!你住口,快走!”
薛修卓行禮,說:“先生若是反悔,我隨時恭候。”
他退出去,下簾走了。
薛修易在院子外邊閑逛,遠遠地見薛修卓往回走。他兜著傘,往廊下鉆,卻正好撞著散學的學生。
這些出青樓的學生對他行禮,薛修易把傘扔給后的丫鬟,他把人挨個看了,丫鬟說:“這是你們能走的路嗎?沖撞大爺,不知禮數!”
學生們垂頭避退,后面立著一個十七八的孩兒。薛修易看姿不凡,便輕佻地拉了的袖,說:“你也是延清買回來的雛兒?什麼?”
這孩兒瞧薛修易一眼,沒答話。那頭的薛修卓正好走近,擋了薛修易,笑說:“大哥才回來麼?歸院吧,雨大,別淋著了。”
薛修易拍開他的手,不耐道:“知道了!”
薛修易走了幾步,聽著后邊的學生們一齊行禮,喊薛修卓“先生”。他回頭又看一眼,卻看見適才的那個孩兒,正偏頭看著他。
那目不畏懼,也不惶恐,在被薛修易發現后,也沒有立刻閃開,反倒看得薛修易忍不住先轉過了頭。
風雨撲面,薛修易打了個哆嗦,抱著手臂快步離開了。
猜你喜歡
-
完結72 章
他懷了他家主子的崽
霸道帝王攻x傲嬌死忠受 成功幫主子解決一次情毒後,戚七事了拂衣去,隱去姓與名,繼續做自在逍遙的暗衛。 然而,主子情毒未清,還要捂住馬甲去給主子解毒,一不小心還給主子扣留下來。 沒辦法,自己的主子,不僅得負責到底,還不能暴露真實身份。 戚七:不怕,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個馬甲。 用馬甲幾次接近主子解情毒,成功從主子身邊跑了幾次後,戚七又被抓回去了,他發現主子怒了。 戚七:“我現在認錯可以嗎?” 戚珩泰扣著死士的脖子,輕輕摩挲,“看來不給你個深刻教訓,你還能繼續跑。”長夜漫漫,他會讓死士知錯的。 後來,戚七穿上喜服嫁給當朝帝王,還想著怎麽跑路+捂住馬甲+捂住肚子。 直到肚子大起來,再也捂不住,馬甲也掉了一地。
26.5萬字8 9567 -
完結237 章
和冥主成婚之后
鬼王x驱鬼师,灵异小甜饼 路迎酒自幼体质特殊,厄运缠身,在一位老前辈的指点下,与鬼怪成婚。 原话是:“看我给你找个香艳女鬼。” 没想到老前辈是个骗子,成亲的对象是孤魂野鬼,连名号都不知道。 仪式走完,阴风阵阵,老前辈噗通一声跪下了,吓得直哆嗦,不肯多说半句话。 但自那之后,路迎酒再没有遇见厄运,也渐渐忘了成婚这事。 直到他离开了驱鬼师联盟,白手起家,身边又开始出现怪事。 比如说,家里东西坏了,第二天在门口能找到一个全新的。 比如说,来他店里闹事的客人总会噩梦缠身。 比如说,一大早打开门,陷害过他的人对着他砰砰砰磕头,高呼:“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 路迎酒:“……?” 后来门口的电灯泡时好时坏,是鬼怪的手笔。 灯泡有阴气,不能留,路迎酒天天过来弄坏灯泡,就是没逮住鬼。 他挑了个晚上蹲守,逼的鬼怪现出原型—— 英俊的男人手里拿着一个阴间电灯泡。 两人对视。 男人开口说:“我想帮你修电灯泡,每次都是刚修好就被人拆坏了。现在阳间人的素质真差。” 路迎酒:“……” 路迎酒又说:“你为什么要帮我修?” 男人语气有些羞涩:“我们、我们不是夫妻么。” 路迎酒:??? 说好的香艳女鬼呢?!
51.2萬字8 14039 -
完結480 章

重生之別來無恙
傅昭覺得自己修道修成了眼瞎心盲,一心敬重維護的師兄為了個小白臉對他奪寶殺人,平日里無所交集的仙門楷模卻在危難關頭為他挺身。雖然最後依舊身隕,但虧他聰明機智用一盤蛤蜊賄賂了除了死魂外啥也沒見識過的窮酸黃泉境擺渡人,調轉船頭回了八年前的開春…… 十六歲的霍晗璋(冰山臉):“師兄,我要傅昭。” 師兄無奈搖頭:“晗璋,人活在世上就要遵守規則,除非你是製定規則的人。” 霍晗璋(握劍):“我明白了。” 師兄:……不是,你明白什麼了? 關鍵字:強強,溫馨,雙潔,1v1
118萬字8 7202 -
完結2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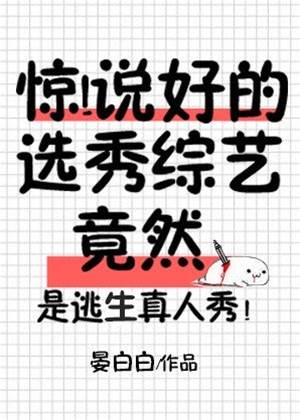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某娛樂公司練習生巫瑾,長了一張絕世美人臉,就算坐著不動都能C位出道。 在報名某選秀綜藝後,閃亮的星途正在向他招手—— 巫瑾:等等,這節目怎麼跟說好的不一樣?不是蹦蹦跳跳唱唱歌嗎?為什麼要送我去荒郊野外…… 節目PD:百年難得一遇的顏值型選手啊,節目組的收視率就靠你拯救了! 巫瑾:……我好像走錯節目了。等等,這不是偶像選秀,這是搏殺逃生真人秀啊啊啊! 十個月後,被扔進節目組的小可愛—— 變成了人間兇器。 副本升級流,輕微娛樂圈,秒天秒地攻 X 小可愛進化秒天秒地受,主受。
89.5萬字8 8616 -
完結528 章

醋壇王爺的神醫俏皮小王妃
【雙潔+甜寵+團寵+空間+男強女強】現代古武世家的中西醫全能圣手,一次意外,靈魂帶著武功和空間戒指穿越到東郡王朝的花癡丑女身上,醒來時就在花轎里,被皇上和她那便宜爹爹聯合當做棋子嫁給雙腿殘疾的寧王爺為正妃。幸好她空間里存了大量現代物資,她為了避免麻煩,選擇抱緊寧王大腿,逐漸展露鋒芒,立誓要成為東郡的第一富婆。她忙著治病救人賺銀子,某王爺卻老是喜歡纏著她,特麼的,是誰說這個臭男人不近女色的?
94.4萬字8 1116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