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系暖婚》 第一卷 011:請叫我乖狗!
何況,謝一直很不滿意姜九笙當年棄了大提琴,拿了把弦樂里最‘三教九流’的木吉他去趟了娛樂圈這蹚渾水。
自打那之后,謝公主就總是眼睛不是眼睛,眉不是眉了,脾氣很大,誰哄都沒有用,姜九笙才不哄。
興許是醫院開的藥見效了,晚上生理痛好了許多,吃了藥,姜九笙很快便睡了。
晚十一點,深秋夜微涼,滿天星辰,
景銀灣的保安室里,安保人員正打著盹,腦袋一搖一晃,忽然猛地一砸,磕在了桌面上,他疼得齜了齜牙,腦門,了眼繼續瞇眼打盹。
“誒,醒醒。”
另外一名安保人員從室外跑進來,搖了搖瞌睡的同伴:“醒醒!”
同伴睡眼惺忪,眼睛,還迷糊著:“怎麼了?”
“監控出問題了,七棟七樓走廊的畫面出不來。”
剛剛還打瞌睡的保安大哥這下徹底清醒了,調了電腦畫面,果然監控顯示碼了:“可能短路了,我去看看。”
七棟七樓住了藝人,得格外小心才是。
一人去排查監控故障,留了一人在保安室里值班,小區里的路燈亮著,折了人影在窗前,來回移著。
保安小黎看了看手表的時間,起探向窗外,遠的雪松樹下,站著一個人,形很高,低著頭,像在尋什麼,他轉過來,月下,迷離的燈纏著,映照出那人長玉立、神飄灑。
Advertisement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小黎會的詩不多,這一首,還是前幾天聽小區九棟剛念高三的一個小姑娘說的。
一副模樣當真是俊啊。
小黎打開鋁合金的窗,向樹下的人打招呼:“時醫生,這麼晚了怎麼還沒睡?”
時醫生前幾天剛搬來,是個和善又溫的人,沒幾天保安室和小區里的人就都認得了他,他那張顛倒眾生的臉,想不記得都難。
九棟高三的小姑娘就是見了時醫生后,念了那首酸溜溜的詩。
時瑾抬頭,從樹影里走出來,路燈過樹的斑駁落在他黑襯上,他說,語速一貫的還:“我的狗走丟了,我來尋它,只是我剛搬來,還不太悉路。”
還是第一次見有人將深沉的黑穿得這麼端方,他一個七尺大男人居然看愣了,小黎不好意思地撓撓頭,熱地說:“我幫你找吧。”
“謝謝。”時瑾將袖子挽起,手臂上有細的薄汗,說,“是一只白的博。”
小黎怕他著急,拿了個手電筒趕去找狗了。
十分鐘后,白博找到了,在小區北邊的地下車庫里,當時小黎找到它的時候,博正抱著一塊狗餅干在吃得津津有味。
回了保安室,十分鐘后,小黎發現丟了一串七棟702住戶的備用電子鑰匙卡。
一刻鐘后。
時瑾給姜博倒了一盆進口狗糧:“乖,吃吧。”
姜博嗷嗷了兩句,鉆到狗盆里拱狗糧,進口的就是進口的,制作很細,狗糧的形狀都是一塊塊骨頭。
“好好看家,我去跟你媽媽說晚安。”時瑾晃了晃手里的鑰匙卡扣,勾笑了,轉出了門。
桌上的電腦屏幕里顯示的畫面是對面702的門口,黑白的。
姜博打了個哆嗦,抱了進口狗糧和自己。
這夜,夜幕籠垂,萬籟俱寂,深秋的風刮過,挲著窗,出輕響聲,淡淡星輝進來,鋪了一屋昏沉。
姜九笙做了個夢,怪陸離的,也不知道夢見了什麼,約有個好聽的聲音一直喊笙笙,看不清那人模樣,白的襯衫染滿了,不知疲倦一遍又一遍地喊的名字。
哦,那人也有一雙得驚心魄的手。
七點醒來,在跑步機上跑了四十分鐘,洗了個澡,的房子是復式的,裝修偏向現代簡約,客廳向,開了一整面的落地窗,天藍的紗窗,墜了雕花布藝的結扣,一側擺放了水滴狀的吊籃,另一側沿墻面嵌放了高低不平的CD。
一樓有三個房間,臥室、客廳,還有占據了近半面積的帽間,二樓裝修了的個人音樂室,用了特殊的吸音材料來隔音,有錄音棚、寫歌室,甚至弄了一個小型的演奏房。
二樓是姜九笙的區,除了樂隊員和莫冰,就是助手小喬也沒有上去過。
運完,選了一張民謠,落地窗外折進來的日打在復古的CD機上,悠揚緩慢的曲調流淌。
打開手機,有三個未接來電,是小區保安室,姜九笙回了個電話。
“姜小姐你好。”
是保安小黎,姜九笙對聲音素來很敏。
“抱歉,我昨晚睡得早,沒有接到電話,請問有什麼事嗎?”
小黎語氣很禮貌謹慎,詳細說了緣由:“您存放在保安室的備用鑰匙卡昨晚不見了,不過今早又找到了,抱歉,打擾到你了。”
才一個晚上時間,電子鑰匙不至于會被復刻吧,又不是變態。
保安室找到鑰匙后,只當是鬧了烏龍,所幸昨晚電話不通后沒有貿然去醒戶主。
姜九笙沒有追究:“無事。”
小黎這又想到了另一茬:“哦,還有一件事要和姜小姐您說一下,這兩天您那個樓層走廊的監控信號經常不穩定,小區業已經安排了人在排查,十分抱歉給您帶來了不便,若是有反常的地方您可以第一時間給保安室致電,我們已經安排了人員二十四小時班。”
姜小姐是藝人,正當紅,雖然這里是高檔小區,安保系統很完善,可盡管如此,以前還是有私生飯潛進來行不軌,得異常小心才是。
“好的,謝謝。”
道了謝后,姜九笙掛了電話,化了個淡妝出門,一打開門,面對七零三正巧也開了門,視線撞了個正著。
時瑾邊有淡淡的笑:“早。”
幾乎口而出:“時醫生早啊。”
若喊時瑾顯得過于親昵,時先生略微疏離,稱呼為時醫生剛剛好,姜九笙倒是喜歡這樣的稱謂,對醫生并沒有什麼特殊懷,只是覺得正好他是,恰好他適合。
問候完,他們一前一后走向電梯口,時瑾按了下樓按鈕,姜九笙避開目,盡量顯得不那麼刻意關注他的手。
“要嗎?”
漂亮的手,遞過來一瓶黃桃味的酸。時瑾低聲問,像舊識的朋友,問得自然又隨意。
姜九笙盯著那瓶酸,還有拿著酸盒的時瑾的手。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深情入骨:裴少撩妻套路深
要問蘇筱柔此生最大的幸運是什麼,她會說是結緣裴子靖。那個身份尊貴的青年才俊,把她寵得上天入地,就差豎把梯子讓她上天摘星星。可他偏偏就是不對蘇筱柔說“我愛你”三個字,起先,蘇筱柔以為他是內斂含蓄。直到無意間窺破裴子靖內心的秘密,她才知曉,那不…
112.5萬字8 16872 -
完結623 章

豪門危婚
臨近結婚,一場被算計的緋色交易,她惹上了商業巨子顧成勳,為夫家換來巨額注資。 三年無性婚姻,她耗盡最後的感情,離婚之際,再遭設計入了顧成勳的房,莫名成為出軌的女人。 一夜風情,他說:“離婚吧,跟我。” 她被寵上天,以為他就是她的良人。 她不知道,他的寵愛背後,是她無法忍受的真相。 不幸流產,鮮血刺目,她站在血泊裏微笑著看他:“分手吧,顧成勳。” 他赤紅著雙眼,抱住她,嘶吼:“你做夢!” 顧成勳的心再銅牆鐵壁,裏麵也隻住著一個許如歌,奈何她不知......
103.9萬字8 117371 -
完結1609 章

一胎三寶,爸比好厲害!
因失戀去酒吧的阮沐希睡了酒吧模特,隔日落荒而逃。兩年後,她回國,才發現酒吧模特搖身一變成為帝城隻手遮天、生殺予奪的權勢之王,更是她姑姑的繼子。她卻在國外生下這位大人物的三胞胎,如此大逆不道。傳聞帝城的權勢之王冷血冷情,對誰都不愛。直到某天打開辦公室的門
149.4萬字8 55852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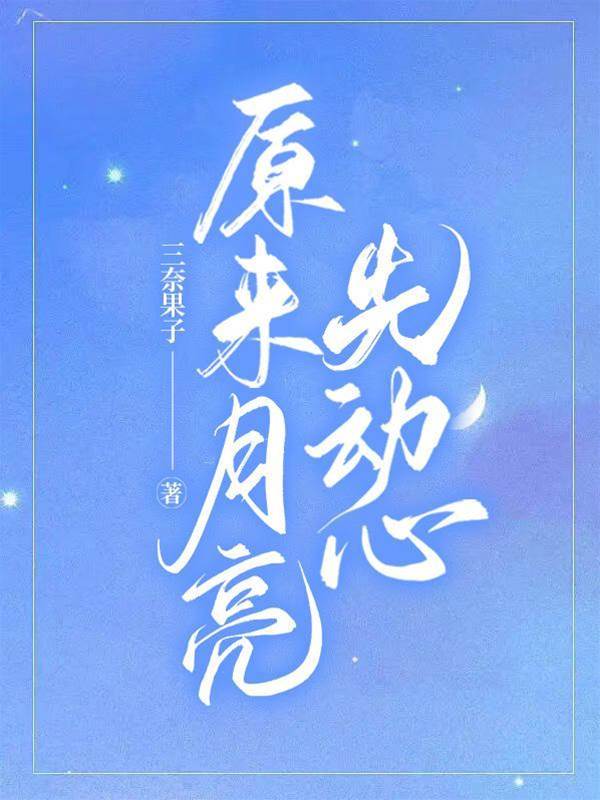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