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玉生香》 第513章 老匹夫
賀泉聽到這消息後卻隻是嗤笑了一聲,當夜裏便讓人將之前所擒大將的腦袋扔到了叛軍營地裏,然後接下來一日攻擊越發頻繁,讓得叛軍幾乎毫無停歇之時。
……
“這個老匹夫!!”
段闊聽著下方之人回稟之時,哪還有半分陣前冷靜姿態,看著擺在桌上的人頭,他神鷙怒聲道,“他竟敢這般挑釁殿下,真以為我們奈何不了他嗎?”
“殿下,我這就立刻率兵前往安昌,圍了賀泉的老巢,我倒是要看看,抄了他們的老底之後,他們還能不能如現在這般然我等。”
“不必。”宇文崢淡聲道。
“殿下!”
段闊臉上滿是怒,“難道咱們就這麽忍著?”
“賀泉那個老匹夫,短短幾日就已經接連傷我兩員大將,更是毀了咱們近兩萬大軍,囂張至極的將高昌東的人頭懸掛於他們營前桅桿之上。”
Advertisement
“若是不給他們一個教訓,世人還以為咱們怕了他們,被人打上門來還當了頭烏,屆時殿下威名損,還有誰肯投奔殿下就大業?”
“放肆!”
宇文崢聽著段闊的話後眸一冷。
段闊口而出之後,就已經察覺到失言,臉一變,“殿下,末將不是那個意思,末將隻是……”
宇文崢擺擺手:“我知道你的意思,也知道賀泉他們此舉讓人生厭。”
“可是你要明白,我們此次起兵為的是皇權正位,不是一時意氣之爭。”
宇文崢神冷淡,對著段闊道,“你以為賀泉當真隻懂這般險無恥,狡詐無賴的手段?那他怎能教導出那麽多的軍中猛將,被人稱為萬將之師?”
“賀泉他們之所以不敢與我們對陣戰,隻行這般人之,就是因為他們手中所握著的兵力遠不及我們,甚至正麵對抗毫無勝算,所以才想要借著此舉擾我們軍心,拖住我們京的腳步。”
“若你此時真的帶兵前往安昌,出了這一時之氣,反倒是正中他們下懷,如了賀泉等饒意。”
“你可知曉賀泉討伐書一出,下競相呼應,其他地方更已有兵力調,甚至已經朝著寧這邊而來,若是那些人趕來之時,我們再想攻京城便難於登,更有可能被賀泉與那些人前後夾擊,多年籌謀功虧預虧。”
“眼下與其去跟賀泉做一時意氣之爭,倒不如不理會他們,隻管朝著京中前行,隻要吩咐下去讓人守好主營之地,他們也奈何不了我們。”
段闊本就是軍中悍將,他原本也隻是被賀泉等人行徑惹怒一時失了分寸,此時被宇文崢勸之後,也是冷靜下來,仔細一想這段時間的發生的事,他頓時滿冷汗。
如若賀泉他們真的打著這般主意,那他若真帶兵前往安昌,豈不是中了他們算計。
分派兵力圍剿安昌,固然能出一時之氣,可若耽誤大事,那才得不償失。
眼下最要的就是京城,賀泉他們百般阻攔,甚至以這般手段激怒他們,就是想要拖延他們大軍開拔京的時間,如果他這個時候真了影響了方寸,那才是如了賀泉他們的意。
猜你喜歡
-
完結810 章
鳳謀天下:王爺為我造反了
「我雲傾挽發誓,有朝一日,定讓那些負我的,欺我的,辱我的,踐踏我的,淩虐我的人付出血的代價!」前世,她一身醫術生死人肉白骨,懸壺濟世安天下,可那些曾得她恩惠的,最後皆選擇了欺辱她,背叛她,淩虐她,殺害她!睜眼重回十七歲,前世神醫化身鐵血修羅,心狠手辣名滿天下。為報仇雪恨,她孤身潛回死亡之地,步步為謀扶植反派大boss。誰料,卻被反派強寵措手不及!雲傾挽:「我隻是隨手滅蟲殺害,王爺不必記在心上。」司徒霆:「那怎麼能行,本王乃性情中人,姑娘大恩無以為報,本王隻能以身相許!」
150.5萬字8 82602 -
完結1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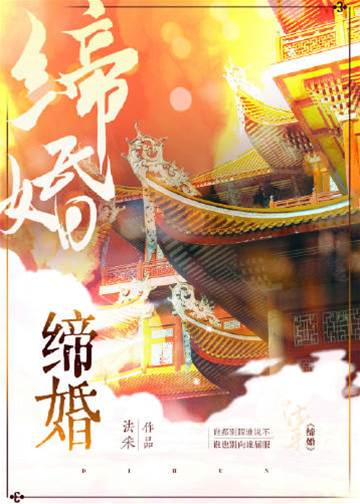
締婚
家敗落之後,項家老爹成了人人喊打的奸佞,項宜帶著幼年的弟妹無依無靠、度日艱難。 她尋來舊日與世家大族譚氏的宗子、譚廷的婚約,親自登了譚家的門。 此事一出,無人不嘲諷項家女為了算計、攀附譚家,連臉面都不要了。 連弟弟妹妹都勸她算了,就算嫁進了譚家,...
45萬字8.33 82137 -
完結136 章

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謝令窈與江時祁十年結發夫妻,從相敬如賓到相看兩厭只用了三年,剩下七年只剩下無盡的冷漠與無視。在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兒子的疏離、婆母的苛待、忠仆的死亡后,她心如死灰,任由一汪池水帶走了自己的性命。 不想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七歲還未來得及嫁給江時祁的那年,既然上天重新給了她一次機會,她定要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不去與江時祁做兩世的怨偶! 可重來一次,她發現有好些事與她記憶中的仿佛不一樣,她以為厭她怨她的男人似乎愛她入骨。 PS:前世不長嘴的兩人,今生渾身都是嘴。
27.1萬字8 26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