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中錄》 第139章月迷津渡(2)
輕微的聲音,流的氣息,忽然之間張極了。那種讓張臉紅的覺又出現在心口。
兩人走出那家店,夜深沉,兩人行走在人群散去而顯得寂寥的街道上時,黃梓瑕終于忍不住,說:“王爺……必定早已想到此事吧?”
他低低地“嗯”了一聲,那雙清幽深暗的眼睛在睫下微微一轉,看向了。
遲疑著,終于還是問:“為什麼……卻在現在告訴我呢?”
“因為,如今我們已經不一樣了。”他說。
微有迷惘,抬頭看他。
明月東出,天墨藍,他在月之前,夜空之下,深深凝著,他不發一言,卻已經讓清楚了他想要說的話。
是的,不一樣了。
記得自己抱住他滾燙的,在黑暗中將臉在他的脖頸上;記得自己曾割開他的服,按著他赤的幫他包扎;記得在他邊守了一夜之后,迷迷糊糊睜開眼,看見他一雙清澈無比的眼睛靜靜地在黎明天之中凝視著——
就像他現在凝視著一樣。
而他現在讓知道了這個,將又卷了一場他邊的謀。此后,哪怕是家的冤案洗雪,重獲清白,恐怕也只能與他并肩一直走下去,再也無法離他了。
因為,一切都已經不一樣了。
與他,不一樣了。
“夔……王兄!楊小弟!”
在他們走到客棧門口時,有個急促的聲音,驟然響起,打斷了此時兩人之前的沉默。
黃梓瑕轉頭看去,周子秦手中舉著一個小瓶子,向著他們快步奔來,臉上的表又是得意非凡,又是興高采烈,又是驚慌失措,混雜在一起,顯得格外怪異。
不由得問:“這麼快就檢驗出來了?”
Advertisement
“是啊,因為我萬萬沒想到……”他說到這里,眼睛一轉,看了看周圍,然后神兮兮地拉著他們往里面走,“這事可不對勁啊,趕的,我給你們看看!”
周子秦慣會吊人胃口,把門窗閉之后,還要仔細查看一下旁邊的隙,直到確定萬無一失,才將那個瓶子往桌上一放,低聲音問:“你們可知這是什麼?”
黃梓瑕接過看了看,里面是平平無奇的一瓶,無無味,和水似的。
“小心小心!這可是劇毒!”周子秦趕說。
黃梓瑕又問:“是什麼?哪里來的?”
“自然是從那綹頭發上來的。雖喝了毒藥就死了,但毒氣還是走到發梢了,我燒了那麼點頭發溶于水中,又過濾之后,就得了這麼一瓶劇毒。”周子秦得意洋洋地展示給他們看,“可要小心啊,我點了一筷子頭在水中,毒死了一缸魚呢。”
黃梓瑕不由得為他家的魚默哀了一下。
李舒白微微皺眉,將那個小瓶子拿過去,看了許久,才若有所思地問:“鴆毒?”
“是啊!就是鴆毒啊!”周子秦一抑不住的喜悅,偏又不能大聲說話,簡直是憋死他了,“鴆鳥羽劃一下酒,就能制鴆酒的那個鴆毒啊!”
“那是謠傳。”李舒白淡淡說道,“世上并沒有鴆鳥,只是因為被這種毒殺死之后,死者全發都會含劇毒,鳥被毒死之后,羽也會含毒。拿著死者的發或者羽,都能再度制劇毒,所以才會有此一說。”
周子秦吐吐舌頭,又說:“這樣的劇毒,幸好世人不知道配方是什麼,不然豈不是天下大了?”
李舒白點頭道:“這毒,宮中是有的,原是前朝所制。據說是以砒霜為主,烏頭、相思子、斷腸草、鉤吻、見封為輔煉制而。當初隋煬帝死后,宇文化及在揚州他的行宮中所獲,后來輾轉流到太宗皇帝手中。太宗因此毒太過狠絕,因此將配方付之一炬,藥也只留下了一小瓶,時至今日已經幾乎沒有了。”
“不能啊,既然它毒死一個人之后,那人的發都毒藥,那麼將那個人的頭發制藥不是又能得到一瓶麼?”
李舒白搖頭道:“鴆毒雖厲害,但也會在使用過程中逐漸流失。鴆毒在制好后第一次用的時候,沾起效,絕無生還之幸。而在提煉了被鴆毒殺死的死者的或者頭發得來的第二次鴆毒,發作就較慢了,服用之后可能一二個時辰才會發作,但一旦發作,片刻之間就會讓對方死去,甚至可能連呼救或者反應的機會都沒有。而再從這種死者上的來的毒藥,雖然依舊是劇毒,但是見效慢,死者痛苦掙扎可能要好幾個時辰,也已經無法再從死者上提煉毒,和普通的毒藥并無二致了。”
周子秦又問:“那麼,鴆毒的死法,是不是與砒霜很像?”
“自然是,畢竟它是主,其他為輔。但毒之劇烈不可同日而語。誤服微量砒霜往往無事,但鴆毒一滴卻足以殺死百人。”李舒白說著,又看著那瓶周子秦提煉出來的毒藥,說,“看來,傅辛阮與溫是死于第二次提煉的鴆毒之下。”
黃梓瑕則問:“如今我們的疑問是,一個遠在川蜀的樂籍子,與并未出仕的郎殉自殺,為何用的會只屬于皇宮大的鴆毒?”
“而且,按照夔王爺的說法,鴆毒現在連宮都是珍稀之了,他們究竟是從哪里得來的呢?。”周子秦的眼睛都亮了,明亮閃閃地著黃梓瑕,“崇古!說不定這回,我們又遇上了一樁驚天迷案!”
黃梓瑕默然點頭,說:“嗯,看起來……背后一定另有其他我們未能察覺到的真相。”
送走了被大案搞得興不已的周子秦,黃梓瑕也起向李舒白告辭。
就在走到門口的時候,看著眼前搖曳的蜀葵花,那月下艷麗的陡然迷了的眼睛,恍惚地站在花前許久,忽然想到一件事,心口一陣冰冷,臉驀然蒼白。
夏末,夜風漸涼意。李舒白站在的后,看見的軀忽然輕微地發起抖來。他低低問了一聲:“怎麼了?”
慢慢回頭看他,張了張,卻沒有說話。
李舒白見客棧院偶有人來往,便握住的手,將拉到屋,關了門,問:“你想到了什麼?”
“我父母,還有哥哥……祖母……”雙抖,幾不聲。
李舒白自然明白了,低聲在耳邊問:“你懷疑,你的父母也是死在鴆毒之下?”
狠狠咬著下,強迫自己清醒一點。的手抓著桌角,太過用力,連關節都泛白泛紫了:“是……我想,確認一下……”
“你先喝口水。”李舒白給倒了一杯茶,站在的面前,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視著問,“你真的,要確認一下?”
抬頭看著他,那雙眼睛在燈火之下,漸漸蒙上一層淚水,被燈一照,的眼睛茫然而恍惚,直如水晶般晶瑩。
死死咬著下,點一點頭,說:“是。”
他不再說什麼,抬起手在的肩上輕輕一按,便疾步走出客棧,奔到巷子口。
遠遠月之下,周子秦沒有騎馬,正牽著蹦蹦跳跳地往郡守府方向而去,那三步一蹦、五步一跳的樣子,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心中的喜悅。
他在后面喊道:“周子秦!”
夜深人靜,空無一人的路上,周子秦聽到聲音,趕拉著小瑕一路小跑著回來:“王兄!還有什麼事嗎?”
李舒白低聲說:“我們出去走一趟。”
周子秦頓時興了:“太好了,把崇古也來,我帶你們去吃蜀郡最好吃的魚!花椒一撒別提多香了……”
“不去。”李舒白說道。
周子秦“咦”了一聲,問:“那我們去……哪里?”
“掘墓。”
周子秦頓時又驚又喜:“這個我喜歡!我和崇古配合得很好的!我們絕對是挖墳掘尸兩大高手,配合得天無……”
“小聲點。”李舒白提醒他。
周子秦趕捂住自己的。
李舒白又說:“前幾日累了,今晚得休息一下。”
“這麼刺激的時刻,他居然選擇休息……真是太沒有為神探的守了。”周子秦撅著,然后又想起什麼,趕問,“王爺重傷初愈,這種事……不如就讓我獨自去做好了,保證做得一不茍,十全十!”
李舒白著沉沉夜,都府所有的道路都是青石鋪徹,年深日久,磨得潤了,月華籠罩在上面,反著一層微顯冰冷的芒。
他慢慢地說:“這可能是本案之中,第一個有利于的證據,我不能不去。”
周子秦有點詫異,問:“?哪個?”
李舒白不說話,只問:“你能出城嗎?”
“這個絕對沒問題,雖然我來的不久,但城門所有人都是我哥們了,我就說夜晚出去查案,保證替我們開門。”他說著,又悄悄湊近李舒白耳朵,輕聲問,“去哪兒挖?”
李舒白轉頭看向城外山上,目反映著月,又清冷,又寧靜。
他說:“黃使君一家的墓上。”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77 章

奪金枝(重生)
虞莞原本是人人稱羨的皇長子妃,身披鳳命,寵愛加身。 一次小產后,她卻眼睜睜看著夫君薛元清停妻再娶,將他那個惦記了六年的白月光抬進了門。 重活一次,本想安穩到老。卻在父母安排的皇子擇婦的宴會上,不期然撞進一雙清寒眼眸。 虞莞一愣。面前此人龍章鳳姿,通身氣度。卻是上輩子與薛元清奪嫡時的死敵——模樣清冷、脾氣孤拐的的薛晏清。 迎上他的雙目,她打了個哆嗦,卻意外聽到他的一句:“虞小姐……可是不愿嫁我?” - 陰差陽錯,她被指給了薛晏清,成了上輩子夫君弟弟的新娘。 虞莞跪于殿下,平靜接了賜婚的旨意。 云鬢鴉發,細腰窈窕。 而在她不知道的上輩子光景里—— 她是自己的長嫂,薛晏清只能在家宴時遠遠地看她一眼。 再走上前,壓抑住眼中情動,輕輕喚一句:“嫂嫂。” 【又冷又甜薄荷糖系女主x內心戲起飛寡言悶騷男主】 1V1,男女主SC 一些閱讀提示:前期節奏有些慢熱/女主上輩子非C,介意慎入 一句話簡介:假高冷他暗戀成真。 立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萬字8 39694 -
完結139 章
我以為我拿的救贖劇本
一朝穿越,虞闕成了修真文為女主換靈根的容器。好消息是現在靈根還在自己身上,壞消息是她正和女主爭一個大門派的入門資格,她的渣爹陰沉沉地看著她。虞闕為了活命,當機立斷茍進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門派。入門后她才發現,她以為的小宗門,連師姐養的狗都比她強…
62.6萬字8.33 1685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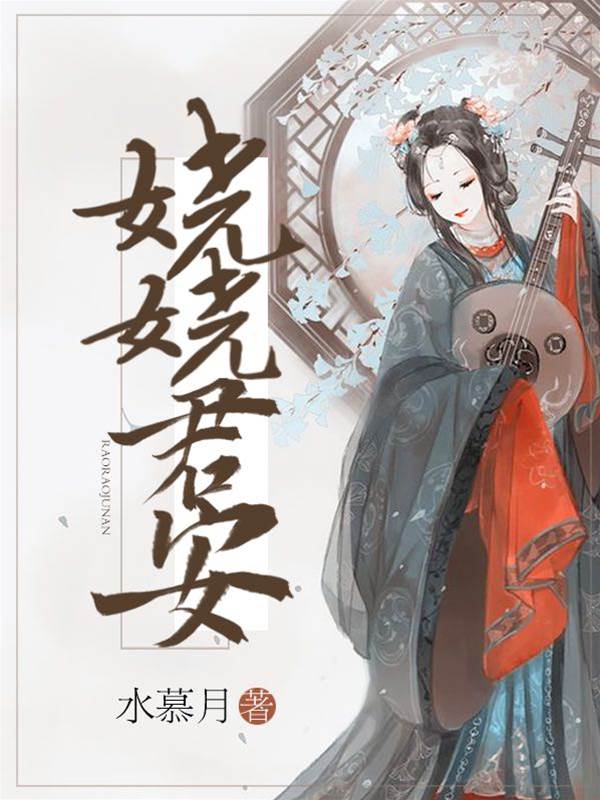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