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表叔畫新妝》 063
前麵就是皇宮了, 江氏很張。
阿漁握住母親的手,笑道“您連姑母都見過了,去東宮有何怕的?”
母親當了侯夫人之後, 曾隨父親去中宮拜見過姑母曹皇後。
江氏輕嘆道“能一樣嗎, 皇後孃娘頂多不喜歡我,側妃、太子妃平時就不把咱們娘倆放在眼裡,恐怕會蓄意刁難咱們。”
阿漁相信曹揮心敲瓷擔雖然曹良薜氖翹子, 但也需要孃家為撐腰, 今日曹琳娓腋們難堪, 得罪了孃家不說, 傳出去也會被東宮其他人笑話。
“可能隻想讓咱們羨慕羨慕吧。”阿漁笑著猜測。
提到曹畝親, 江氏慨道“側妃命好的,這胎若是兒子, 便是太子的長子了。”
阿漁沒再接話。
倘若嫁錯了人,生兒子生兒都不過是多帶個可憐人來世上罷了。
太子絕非曹牧既恕
進了宮,母倆直接被請到了東宮。
與太子人前表現出來的樸素剛正一致, 東宮上下陳設雅而不華, 還沒有鎮國公府、平侯府氣派。
來了東宮,肯定要先拜見東宮的主人。
到了廳堂,隻見側妃曹痢8子妃徐瓊都在, 徐瓊盛裝坐在主位,曹烈簧砑虻サ乃鼐懷と棺在下首, 眉目怯,並沒有寵妃孕後耀武揚威的樣子。再看徐瓊, 笑容親切地著阿漁,彷彿當初對阿漁的冷嘲熱諷全是旁人所為。
阿漁曾經做過人家的兒媳婦, 倒是能理解二的變化。
未出嫁的姑娘在自家拘束,想做什麼做什麼,可一旦嫁了人,就要努力藏出嫁前的種種小病,讓自己變得端莊大方或溫,免得被夫家之人挑剔嫌棄。
嫁進普通的夫家如此,嫁進東宮就更要謹言慎行了。
Advertisement
“夫人請坐。”徐瓊笑著對江氏道。
江氏輕聲道謝,坐到了一旁。
徐瓊與江氏沒什麼好說的,這會兒看向阿漁,驚訝地道“半年沒見,阿漁竟出落得如此貌了,平時我覺得側妃的容貌便是頂尖的了,瞧瞧你現在,簡直比側妃還要令人驚艷。”
曹廖叛裕微微扯了下角。
阿漁卻有點想笑,這纔是悉的那個徐瓊啊。
“我與姐姐再,到了您麵前,都是襯托紅花的綠葉罷了。”阿漁打趣地回道。
這話說得很漂亮了,江氏意外地看向兒,沒想到時與一般怯怯弱弱的兒進了皇宮竟能如此沉著,言行得。
徐瓊卻覺得阿漁在諷刺!
向來自恃貌,雖輸給阿漁一些,但絕不至於被曹簾認氯ィ可進宮這半年來,太子每月去曹聊潛叩拇問最多,就說明在太子眼中,曹簾人!
更可恨的是,曹輛尤幌人一步懷孕了!
說實話,曹梁萇偃ス公府做客,選秀之前,徐瓊幾乎想不起曹臉な裁茨q,進宮後相多了,徐瓊才漸漸發現這曹囊瘓僖歡簡直就是照著阿漁學來的,眉目怯細聲細語,不知道的還以為兩人是親姐妹!
麵對一個曹輛托娜了,現在同時要麵對阿漁甚至江氏,徐瓊客套片刻便地曹燎氚15婺概去的院子喝茶去了。
阿漁等人笑著告退。
東宮地方不大,大多數太子的人都得三四個在一個院子裡,曹寥叢繚緹頭值攪艘桓齠懶5男≡海而且,與徐瓊的住比,曹琳獗咼饗遠嗔思阜稚蓴之。
沒了徐瓊的眼線,曹林沼諢指嗽諍罡時的姿態,指著廳堂裡擺放的海棠盆景,微微自得地對阿漁道“我記得妹妹很喜歡海棠,這是昨日太子剛命人從花房搬過來的名品,妹妹若喜歡,走的時候帶兩盆回去吧。”
開在冬日的海棠,多珍貴多稀奇!
雖非金銀,卻更能現太子對的寵。
曹療詿地看向阿漁。
阿漁兩世為人,也算明白了一些道理,當一個人想要在你麵前炫耀什麼時,你越表現得羨慕嫉妒,對方就會越滿意。
阿漁無需奉承曹潦裁矗但如果不接這盆海棠,曹量贍芑峒絳顯擺其他東西。
因此,為了耳朵清凈,阿漁寵若驚地道“多謝姐姐!”
說完,還欣喜地盯著那盆海棠看了會兒。
曹良了,笑容裡出一輕視。
早就說過,就算阿漁當了嫡,曹琳昭會高阿漁一頭。
接下來,曹輛拖翊蚩了話匣子一般,開始不經意般泄出太子對的各種殊寵。
阿漁、江氏互視一眼,都羨慕地聽著。
兩盞茶過後,曹遼肀叩逆宙治律提醒曹潰骸澳該休息了。”
曹媛段難,對江氏母解釋道“哎,自打我懷了子,白日就容易犯困,今日母親與妹妹難得過來,我……”
江氏聽說話就膩味,忙道“您子重要,快去休息吧!”
曹廖弈蔚孛肚子,憾道“那我就不多留母親妹妹了。”
阿漁鬆了口氣,其實當個合格的陪客也很累啊,明明不想笑,卻又要維持笑容。
走出東宮,阿漁揶揄地朝母親眨眼睛“我猜對了吧?”
江氏苦笑。
阿漁正要隨母親離開,忽見曹皇後邊的陸公公笑著走了過來,遠遠地朝兩人道“夫人,四姑娘,娘娘得知二位今日進宮,特意我來請二位過去喝茶呢,瞧我,腳步慢得差點耽誤了娘孃的大事。”
曹皇後有請,娘倆笑著改了方向。
然而還沒到中宮,半路卻撞見了三皇子。
如今的三皇子已經十五歲了,年郎一紅錦袍,眉目倨傲,而他剛剛還在疾步往東宮的方向走,現在見到阿漁就早早停在原地,目不轉睛地盯著阿漁,倒好像他急著去東宮便是為了見阿漁。
江氏皺眉,這個年什麼意思?
及時擋在了兒麵前。
阿漁也咬了咬。
上輩子曾經深深地疑過,為何堂姐曹沛、表姐徐瑛喜歡,庶姐曹痢1斫閾燁砣囪岫袼?為何徐三徐四徐五甚至徐恪等表哥都照顧,三皇子就非要刁難呢?而且三皇子是主跑過來要欺負人,比徐瓊、曹沛更壞。
“您是平侯夫人?”見到江氏,三皇子愣了愣,還算客氣地問道。
江氏點頭,在後兒的小聲提醒下,朝三皇子行禮道“臣婦見過三殿下。”
江氏容貌溫又麗,還是個長輩,三皇子抿,看眼陸公公,道“夫人要去給母後請安吧,那您先行,我與阿漁表妹說說話。”
江氏第一次遇到這麼不講理還一副理所應當語氣的年,兒年後就十四了,憑什麼要冒著被人議論的風險單獨與三皇子說話?
沒等江氏開口,陸公公笑著乾涉道“殿下,娘娘已經等了許久了,咱們不好娘娘再等。”
三皇子的生母乃陳貴妃,後宮地位僅次於曹皇後的妃嬪,心深,三皇子並沒有太把曹皇後當回事。
“既如此,我也過去給母後請個安。”三皇子冷哼道,說完便往江氏後走,要與阿漁並肩而行。
阿漁再惱火,卻無法攆人,畢竟沒資格阻止三皇子去見姑母。
江氏一直都以為曹廷安夠蠻橫無理了,現在才發現三皇子比曹廷安更無禮!他這麼追著兒,旁人看見該怎麼想,徐老太君、徐五爺知道了該怎麼想?
兒的名聲要,江氏相信曹皇後能明白的無奈!
為了擺三皇子,江氏突然彎腰,麵痛苦。
阿漁真的被母親嚇到了,急著扶住母親“娘,你怎麼了?”
江氏做咬牙忍狀,緩了會兒才對陸公公道“我有腹痛的老病,今日怕是不能去給娘娘請安了,煩請公公代我們向娘娘賠罪。”
陸公公忍笑道“夫人要,快回府歇息吧。”
江氏便自然而然地靠著兒轉向宮門。
三皇子目瞪口呆,等他反應過來,阿漁娘倆已經走出一段距離了。
他剛要追上去,陸公公幽幽道“殿下適可而止,鬧大了貴妃那邊也會降罪於您。”
道理三皇子都明白,可是看著阿漁纖細的背影,想到相比去年越發嫵勾人的臉蛋,三皇子就管不住自己的腳。
他大步朝娘倆跑去。
聽到腳步聲,江氏眉頭鎖。
阿漁見了,心底倏地騰起一怨氣。
將母親給丫鬟,阿漁轉,冷視已經追到麵前的年“殿下究竟意何為?”
三皇子見慣了害怕躲避的怯懦樣,驟然對上小姑娘怒氣沖沖的杏眼,他竟看呆了。
他想做什麼?
他想欺負阿漁,想看淚眼汪汪的可憐樣,想聽驚慌卻好聽的哀求,特別是那一聲聲的三殿下,比黃鶯鳥的還悅耳。現在長大了,三皇子忽然還想想白的臉蛋,想咬一咬人的,想,想讓做他的人。
三皇子去年便有了通房。
夜晚的時候,三皇子常常走神,如果換阿漁會是什麼樣呢?
但,這些念頭他可以私底下對阿漁說,一邊欺負一邊說,卻不能當著江氏的麵說。
頭滾,三皇子目開始躲閃。
阿漁看不懂他的眼神,江氏看懂了。
“小已經定下婚事,殿下自重。”不再裝病,江氏擋在兒麵前,一臉嚴肅地道。
阿漁不從後麵攥住了母親的袖子,這就要公開了嗎?
江氏隻怒容瞪著三皇子。
三皇子宛如暴雨加,一下子滅了他心底的熾火。
“你要讓嫁誰?”三皇子沖地質問道。
江氏毫不退“這是我們的家事,與殿下無關。”
三皇子呼吸都重了,如果定了婚事,為何他一點訊息都沒聽說?
就在三皇子靈機一懷疑江氏是不是在騙他的時候,宮門突然傳來一陣馬蹄聲。
他抬頭看去,看到一隊神策營的侍衛,領頭之人一深紫袍,卻是徐潛,他那位比皇帝老子還喜歡管教人的五表叔。
巡城歸來的徐潛並未料到會在宮門附近撞見準嶽母與小未婚妻。
他迅速掃視三人,見江氏神、姿態都不對,徐潛命手下原地待命,他縱下馬,大步而來。
阿漁低下頭,穿服的徐潛,冷峻威嚴,莫名不敢直視。
三皇子攥了攥拳頭,卻沒有走開。
江氏看到準婿,宛如看到了主心骨,一委屈便不控製地漫上心頭,再化眼中的水。
自覺丟人,急忙偏頭掩飾。
徐潛捕捉到了,何事竟能氣哭準嶽母?
他直接看向三皇子“你在這裡做什麼?”
三皇子振振有詞,半帶諷刺地道“聽聞阿漁表妹已經定了婚事,我特來道喜。”
年郎盯著阿漁的眼神,讓徐潛想到了侄子徐恪。
反應過來,徐潛冷笑“是嗎,那用不用我提前送你一張喜帖?”
三皇子……
啥?
五表叔剛剛說了啥?
我為表叔畫新妝
猜你喜歡
-
完結367 章

前妻,敢嫁別人試試
三年前,她在眾人艷羨的目光里,成為他的太太。婚后三年,她是他身邊不受待見的下堂妻,人前光鮮亮麗,人后百般折磨。三年后,他出軌的消息,將她推上風口浪尖。盛婉婉從一開始就知道,路晟不會給她愛,可是當她打算離去的時候,他卻又一次抱住她,“別走,給…
95.4萬字8 74666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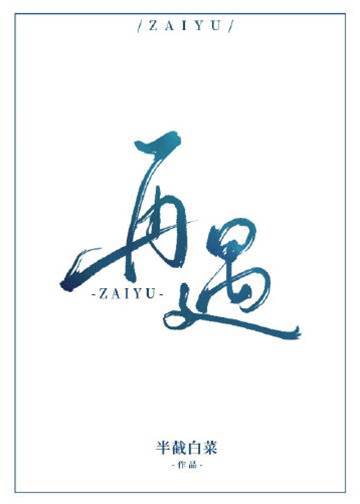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8890 -
完結641 章
重返七零之空間小辣妻
末世大佬唐霜穿到年代成了被壓榨的小可憐,看著自己帶過來的空間,她不由勾唇笑了,這極品家人不要也罷; 幫助母親與出軌父親離婚,帶著母親和妹妹離開吸血的極品一家人,自此開啟美好新生活。 母親刺繡,妹妹讀書,至于她……自然是將事業做的風生水起, 不過這高嶺之花的美少年怎麼總是圍著她轉, 還有那麼多優秀男人想要給她當爹,更有家世顯赫的老爺子找上門來,成了她的親外公; 且看唐霜在年代從無到有的精彩人生。
121.5萬字8 68733 -
完結2314 章

第一名媛:奈何嬌妻太會撩(盛莞莞凌霄)
“我愛的人一直都是白雪。”一句話,一場逃婚,讓海城第一名媛盛莞莞淪為笑話,六年的付出最終只換來一句“對不起”。盛莞莞淺笑,“我知道他一定會回來的,但是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父親車禍昏迷不醒,奸人為上位種種逼迫,為保住父親辛苦創立的公司,盛莞莞將自己嫁給了海城人人“談虎色變”的男人。世人都說他六親不認、冷血無情,誰料這猛虎不但粘人,還是個護犢子,鑒婊能力一流。“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麼?”“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說你不好,那個人依然把你當成心頭寶。”
426.6萬字8 397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