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嫁不晚:獵愛小鮮肉》 第四百六十四章 和解
王向中的父母常年在國外,除了老太爺他也沒有要見的人,打過招呼之後就直奔王向的房子去了。
敲門進去,王向不在。
等他轉出來的時候正好到王向和莫曉曉雙雙牽著手回來,他有些納悶的指指莫曉曉,那意思是說,不是說莫曉曉被抓了嗎?救出來了?
“進去說。”王向說著便開門回家。
“向中,好久不見。”莫曉曉跟他打招呼。
王向中走在後頭,故意拉了這個三嫂一把:“怎,怎麼回事?”
莫曉曉搖搖頭:“我也不知道,你問你哥去。”
“你不是被,被抓了嗎?”
“嗯,算是限製了我的人自由,不過我已經和臺裡請過假了,等向這邊的事了結了再回去。”
王向中是一頭霧水,到現在也不知道事往哪個方向發展了。
正要仔細問問,前頭王向已經在客廳坐下了:“我向老爺子鬆口了,不再管方家的事,這段時間留在老宅。”
王向中顯然不相信:“不,不至於吧?”
“不管方家的人是我,不是你,你繼續做你的事。還有,老爺子也沒把葉英給那個人,算是拿在手上的一個籌碼吧,他說了,如果這次方家過去了,葉英將來會作為證人給警方,如果方家沒過去,則作為禮送給那個人。”
王璽從來不打無準備的仗,也不會做吃虧的事。葉英拿在他的手上,算的上是一個雙贏的局麵。
王向中鼻子,算是瞭解了個大概。
“越南那邊的事理的怎麼樣了?”
“還,好好,正在進行中……引渡的事,有點,有點麻煩,H市當地政府已經跟,外部,談過了。”
“對了,”王向中有些侷促不安道:“家裡這是怎麼了?老爺子?生氣了?剛才,剛才我見他的時候,他,他好像臉不是很好。”
Advertisement
“那不就是生氣嗎。”王向一向喜怒不形於,這會兒反而勾發出一聲冷嗤。
王向中有些不安,自顧自的倒了杯水,從小到大這個家裡他誰也不怕,最怕的就是那位老爺子。
本來看他臉不好以為會被他訓斥幾句,沒想到聊了沒兩句就說:你是來找你三哥的吧?去吧,去吧。
他這才誠惶誠恐的告退,直接奔著他三哥這裡來了。
“爺爺……不,不同意你跟咱三嫂的婚事?”
莫曉曉坐在旁邊有些尷尬的笑了:“向說,我和他的事隻是小事。”
是不是小事他們自己也懂清楚,王家不過是不信任能安安穩穩的做王向的妻子吧。
對於這份不信任,也隻能說,時間會檢驗一切。
“那,那是因為什麼?”
“之前我們起過一些爭執,爺爺想放棄方家。”王向道:“有比方家更合適的‘合作夥伴’出現,他便不讓我再手方家的事,我沒同意。”
他一向黑白分明,哪怕那個人是自家爺爺。
王向中有些恍惚,半晌之後忽然問道:“就,就因為這個?所以把,把三嫂抓來,做,做人質?”
“差不多是這樣,不僅如此,還讓我卸任集團的管理工作。”
“不,不是吧……”王向中驚訝的張大了:“三,三哥,你可不能卸,卸任,你要走了,咱們這不是群龍無首了嗎!”
“向平會接我的班。”
“四哥?”王向中一口水沒嚥下去:“他,不行!”
王向沒有說話,連老八都知道他不行,爺爺不可能不知道。
把集團給職業經理人他又不放心,給自己的孫子,也就隻有王向平能趕著做點什麼了。
所以他現在樂的清閑,就在家裡跟他們耗著,看看這事最後是個什麼結果。
“A市那邊你給我盯著點,越南那邊也照應好,把人安排到安全的地方。”
王向中麵嚴峻的點點頭:“就,就這樣了?”
“就這樣。”
王向中又道:“爺爺那邊用不用,我,我再去說說,你這一天不在,票,票可就大跌啊……”
王向端起桌上的杯子喝水,鏡片後的眸微微一抬,掠向自己的八弟時略得幾分戲謔:“跌就跌,經此一事,A市大換,就當洗牌了。”
王向中隻想說一句,看到自己的心變這樣,他這個三哥也是心大。
“你回去吧,配合蘇楠的行。”
王向中稍稍一頓,點頭應了下來:“行,行吧,那我先走了,你要是跟三嫂想回去了,跟我,說,說一聲。我到時候來接你們,爺爺應該不會攔。”
“嗯。”
也沒在家裡停留,大冬天的回家一趟卻跑了一的汗,等他上車要走的時候,一堆傭人又圍了上來。
打趣著王八爺這麼快就要走了啊,還給八爺做了晚飯呢。
王向中有點hold不住,覺得這些人熱的他難以招架,還是在A市好,天高皇帝遠。
潘英傷好出院後的第二天蘇楠和徐子瑞就一刻也不想耽擱的要去提審他,蘇楠起了大早,這算是第一天正式上班了,天氣不錯。
已經快要忘記自己上次穿製服是什麼時候了,雖然到生產之前也一直在崗,但因為那時候肚子比較大,製服穿在上不倫不類的。
產假還沒結束的早就已經整裝完畢,乍然出現在辦公室引來無數人艷羨的目。
“蘇警生完孩子真的一點也沒變,這服穿在上還是不大不小正合。”
蘇楠回以一笑:“雖然我不想拉仇恨,但好像我還真有吃不胖質。”
“沒有吧?”同事打趣道:“還記得你才調過來那段時間,臉龐就圓圓的,被你老公養的不要太好!”
回想起那個時候,好像重確實有所增加,要麼跟方錦程出去吃,要麼就是他下廚。
而且那段時間剛調往市局,還在學習階段,很多事不用親力親為,也沒什麼好心的事。
哪像現在,雖然生產之後大力的補充營養,但因為心的事多,也一直在參與調查方家的事,怎麼也胖不起來,反而還有點往下瘦的覺。
“楠姐,資料準備好了。”小林將一份資料夾遞給蘇楠:“基本都是你給我的資訊我做了整理,還有就是徐隊那邊發過來的。”
“好,辛苦你了。”
小林一臉期待道:“要不要帶我去見識見識?我可以給你做筆錄。”
蘇楠哭笑不得:“那不就有點大材小用了嗎,你老老實實在辦公室待著吧,那邊有人做筆錄。”
小林有些失:“阿智去嗎?”
“應該也不去,用不了那麼多人,就我和徐隊過去。”
小林點頭:“行,那我在辦公室等著。”
跟徐子瑞帶上資料離開辦公室,在走下市局一層一層的臺階時,蘇楠突然有種慨。
人生就好像爬樓梯一樣,似乎所有屹立頂端的人都不可避免的會走下坡路。
一步錯,步步皆錯,潘英是從什麼時候走錯的?又是從什麼時候攀上了那麼一座大山的?
所有的一切都隻是他們的猜測,在沒得到潘英親口證實之前,不好斷言。
抬手微微擋了擋眼前刺目的,蘇楠扭頭問徐子瑞道:“你覺得潘英會老實代嗎?”
“可能隻會代一部分,你想知道的容他應該不會說。”
“我想知道什麼?”
“難道不是方錦程的事?”
蘇楠笑著搖頭:“我已經不想知道他的事了,我想知道的就是你想知道的。”
徐子瑞麵容冷峻的表示沉默,他沒有說,在他心中,他想知道的容跟蘇楠多還是有些出的。
開啟警車的車門,蘇楠坐了進去繫好安全帶。
車子出了大門就向看守所的方向去了,有了上次的前車之鑒,潘英已經移了看守所。
那邊的人也經過嚴格篩查,確保潘英在裡麵能夠安全,再鬧出一個‘自殺’事件,他可就不一定有命活下來了。
蘇楠翻了翻手上的資料,對正在開車的徐子瑞道:“以前我以為潘傑這個份是潘英自己在利用,潘傑名下的財產也都屬於潘英,沒想到觀瀾國際竟然不是潘英的,由此是不是也說明,以前所調查的那些屬於潘傑的產業也都不是潘英的?”
“不一定,”徐子瑞搖頭:“得在銀行那邊申請賬目明細進行調查,誰也說不準。”
“這個幕後黑手可真夠厲害的,一個是方錦程的姐姐,本市最出名的企業家,一個是本市玩轉黃賭毒,社會最底層的黑暗勢力,都被他盡收囊中。連國外的雇傭兵都玩的轉,我開始有點期待他浮出水麵的一天了。”
徐子瑞看一眼,繼而說道:“不管是你的父母,還是方家,都和你有所牽扯,你還是要時刻保持警惕,不要忘了他還曾經讓你命懸一刻。”
蘇楠咂咂:“既然讓我活下來了,我也就沒那麼容易死了。”
除了那次*事件,幾乎已經可以確定,自己幾次差點死於非命的原因也跟這位幕後黑手有關。
如果越南藥廠的勢力是屬於方靜秋的,而方靜秋又幕後黑手的驅使,那就是他想要置自己於死地。
當時,那個人眼看離父母失蹤真相越來越近的時候,除了讓死已經沒別的選擇了。
如果是方靜秋下的手,那完全沒必要在自己的包裡放上炸|彈來引起自己的注意,甚至希藉此來讓接警方調查,從而躲避一段時間,或者就此和警察這個職業說拜拜。
剩嫁不晚:獵小鮮
猜你喜歡
-
完結1497 章

天才雙寶:傲嬌前妻抱回家
一場意外,她懷了陌生人的孩子,生下天才雙胞胎。為了養娃,她和神秘總裁協議結婚,卻從沒見過對方。五年後,總裁通知她離婚,一見麵她發現,這個老公和自家寶寶驚人的相似。雙胞胎寶寶扯住總裁大人的衣袖:這位先生,我們懷疑你是我們爹地,麻煩你去做個親子鑒定?
267.8萬字8 65089 -
完結100 章
萌妻迷糊︰第一暖男老公
他陰沉著臉,眼里一片冰冷,但是聲音卻出其的興奮︰“小東西,既然你覺得我惡心,那我就惡心你一輩子。下個月,我們準時舉行婚禮,你不準逃!” “你等著吧!我死也不會嫁給你的。”她冷冷的看著他。 他愛她,想要她。為了得到她,他不惜一切。 兩年前,他吻了她。因為她年紀小,他給她兩年自由。 兩年後,他霸道回歸,強行娶她,霸道寵她。
8.9萬字8 26664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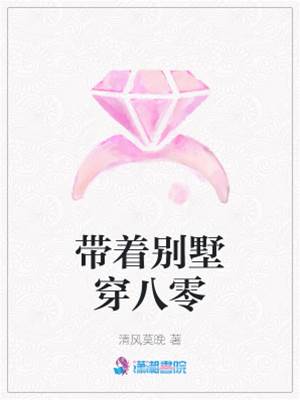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32 章

辣妻致富1990
身價千億的餐飲、地產巨亨顧語桐,訂婚當天被未婚夫刺殺! 再次醒來的她,發現自己竟然穿越到了生活在1990年的原主身上! 原主竟然跟一個傻子結了婚? 住進了貧民窟? 還在外面勾搭一個老流氓? 滿地雞毛讓她眉頭緊皺,但她顧語桐豈會就此沉淪! 一邊拳打老流氓,一邊發家致富。 但當她想要離開傻子的時候。 卻發現, 這個傻子好像不對勁。在
61.2萬字8 14929 -
完結921 章

一胎三寶:夫人又又又帥炸了
被設計陷害入獄,蘇溪若成為過街老鼠。監獄毀容產子,繼妹頂替她的身份成為豪門未婚妻。為了母親孩子一忍再忍,對方卻得寸進尺。蘇溪若忍無可忍,握拳發誓,再忍她就是個孫子!于是所有人都以為曾經這位跌落地獄的蘇小姐會更加墮落的時候,隔天卻發現各界大佬紛紛圍著她卑躬屈膝。而傳說中那位陸爺手舉鍋鏟將蘇溪若逼入廚房:“老婆,什麼時候跟我回家?”
229.5萬字8 73055 -
連載342 章

從摸魚開始成為學霸
【校園學霸+輕松日常+幽默搞笑】“你們看看陳驍昕,學習成績那麼優異,上課還如此的認真,那些成績不好又不認真聽課的,你們不覺得臉紅嗎?”臺上的老師一臉恨鐵不成鋼地
83.3萬字8.18 41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