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執天下》 第二十八章 虛實(八)
來自北方的炮聲,就像捅了馬蜂窩。
連著七八聲巨響從天際傳來,如同雷暴。
井井有條,甚至顯得過於平靜的天門寨,在炮聲後,陡然間沸騰了起來。
食堂里正在吃飯的兵紛紛擡起頭,還在外面排隊的指揮,幾百人的隊伍中有了些,隊伍中的軍紛紛出列彈。
王厚站在稍後的位置,跟他的隨行人員說話中間,擡頭看了看那邊的人羣。
秦琬從側面看見王厚臉上的表,臉就微微一沉,“唉……都是沉不住氣的混賬,讓太尉見笑了。”秦琬臉上帶著尷尬的笑,瞥了那些士兵一眼,心中計較,回頭往死裡練。
寨中的軍這是都已經聽到了炮聲,先後狂奔而來。
秦琬見王厚和他隨從還在說,走上前去。
跑得急了,軍們各個大氣,問秦琬,“都……監,出了何事?”
秦琬沒好氣,“誰知道?”
軍們相互一看,一齊搖頭。
“遼狗打起來了?”有人猜測。
“莫不是弄夜間演習?”又有人猜。
另一人冷笑,“夜戰演習還開炮?!”
秦琬就任後,在天門寨中練過兩次夜戰,但槍炮都沒敢用,怕出事。
以天門寨的訓練水平,都沒敢玩那麼大,天雄城的遼軍都沒怎麼演習過,誰會相信他們敢直接上夜間演習,還敢用火炮。
幾個人相互否定,誰都弄不明白,又向秦琬請示,“都監,怎麼辦?”
秦琬著聲音過來的方向,“晚飯照常吃,花三、樂文,你們已經吃過了,先上城去守著。炮壘那邊注意支援,值班的人數不夠搬火藥炮彈。”
兩名軍應諾,又是飛奔而去。
Advertisement
就在秦琬吩咐的時候,又是幾下炮聲傳來,約約的,還夾雜著輕微的砰砰聲。
連火槍都了,這是真打起來了。
秦琬點了自己的親衛,“去跟衛弘說,最快速度,把飛船升起來。”
一名親衛飛奔遠去,秦琬又對另一人道,“去放警號,所有請假離營者,即刻回營。”
“幾級戒備?”親衛問。
新的軍事訓練大綱中,數字化的程度很高。就連軍事戒備,也分爲一二三和日常四級。
秦琬學過了,背過了,但是還不習慣在日常上應用。幸好經過訓練後的親兵,知道該問上一句。
旁腳步響,王厚跟邊人說完話,走了過來,“要提升警戒等級了?”
“請太尉示下。”秦琬躬請示。
“你的兵,你的寨。”王厚沒有越俎代庖的打算。
秦琬應聲,回頭道:“二級戒備。”
算是不過不失的一個決定。
來自城衙鍋爐房的汽笛聲響起,短促的接連響了一長兩短的三聲,隔了十幾秒,又重複了一遍。前後五遍,方悠悠止歇。
還在家中的兵們,紛紛從小樓中跑出來,滿大街都是人,有一些連服都沒穿戴好,邊走便穿。
二級戒備下,衛馬隊開始在城中巡防,除了歸建的兵士,穿戴有異之人,全都被攔下查問。
安放在炮壘頂端的探照燈被點亮了,特製的燈罩將焦點火炬火,投到巨大的凹面鏡上,被凹面鏡反之後,筆直地照出去。幾道柱劃破夜空,開始在城外的市鎮、田宅和野地裡來回掃。
城門開了又關,進來的是從外面聽到警號,趕回來的士兵,出門的有幾個信使,帶著秦琬的文書、手令和令箭,趕往安肅城和其他幾座近寨堡。
但更重要的是派出去的斥候。幾隊探馬著黑,騎著黑馬從四門散出,分頭去往各個重要地點查探。有去邊境上的,也有要越過邊境。王厚在旁邊看著,聽到秦琬派人越境打探,也沒有阻止,默認了下來。
而最重要的,則是國境線上的車站。那裡集中了編組站和裝卸場,那裡有著千匹以上的挽馬,數百節車廂,以及上百萬貫的資。不過那裡本就有一個指揮的鐵路部隊駐紮,車站建築也是以寨堡的制式建造的,有槍有炮,食水不缺,守住一兩天不問題。秦琬也派人去聯絡了,讓他們保持最高戒備,到進攻或發現有人劫掠,立刻開火,天門寨會立刻趕去救援。
一切安排好,王厚、秦琬一同上了城樓。迎面北風來,遠那座用燈火鑲出金邊的黑影方向,傳來的槍聲如同炒豆一般,比之前更加清晰了許多。
王厚和秦琬在炮壘上一直在等著,時不時拿起千里鏡,但在鏡片中,連炮火和槍支的閃口看不見。似乎遼人方面的槍炮發,並不是發生在面向國境的這一邊。
半個時辰過去了,所有指揮都結束了晚上的用餐。炮兵指揮全數就位,所有步騎指揮,全都回營進行戰鬥準備。包括原本被派上城守衛的那個指揮,也被調了下來,返回營地等候命令。而派出去的斥候探馬,還沒有人回來。
這時北門方向,有人來報,說有鄉人想寨躲避。
在城牆上的最高,王厚和秦琬都看見了棄家出逃的百姓,有的打著燈,一條斷斷續續的流,帶著喧囂的人聲,一直延到天門寨這裡。
至上千人,不確定是否有細的況下,不能放進寨中來。
秦琬問來報信的軍校:“他們知道出了什麼事?”
“下這就去問。”
“等等,不用問了。讓他們沿著路往回走。過了葫蘆堤,有村子可以收留他們。”
“不問了?”待軍校走後,王厚問道。
“如果知道發生了什麼,直接就會說了。既然沒說,肯定是不知道。問了,反而會有人扯謊想混進來。派出去的探馬,比那些百姓更清楚什麼是軍。”
王厚點點頭,沒說話了。從一開始,他就看著秦琬安排佈置,最多問一問,就沒幹涉過。
秦琬則又了親兵過來,吩咐道,“等一下去城門,看能走的都走了,剩下不便走的,打開甕城外門,讓他們在甕城中休息。”
吩咐過後,他轉回來對王厚解釋,“能往後繼續走的,肯定是能走的。實在走不了的,也不能讓他們留在外面。我們吃兵糧,畢竟是爲了守境安民。”
秦琬想得也算周全,王厚又點了點頭,算是讚許。
半夜的時候,食堂那邊擡了大筐的麪餅和大桶的熱湯上了城頭和炮壘,給各送上了熱騰騰的夜宵。還在營中等候的各部指揮,也得到了他們的那一份。
王厚和秦琬,同樣就著熱湯,啃起了乾堅的麪餅。
王厚將麪餅撕小塊,一塊塊地丟進湯裡面泡開,“應該不是要寇了。”
派出去的探馬,已經回來了兩隊,都說沒有發現遼人寇,或準備寇的跡象。還沒回來的,是準備潛往國境對面的探查,需要更多的時間。
秦琬沒有泡麪餅,用力地啃了一口,嚼著,“那就是鬥。演習基本上不可能,現在就只能等了。朝廷不下令,看到機會也抓不到。太尉要不要回去休息。”
王厚搖頭,“再等等看。”
接下來,始終沒太多消息,北面的炮聲早停了,槍聲很快也停了下來,隔上很長時間纔會響上一聲,而且隨著風向轉變越來越弱,最後都微弱到分不清是不是錯覺了。
到了下半夜兩點多鐘的時候,見北方的確不會有敵軍來襲,秦琬終於下令,一半士兵繼續守候,剩下的回去休息。
快天明時,派出去的斥候探馬除了一隊之外,全都回來了。最後回來的一隊,有兩人了輕傷,但帶回了一遼兵的。
“遼狗似乎是有人叛,打了起來,戰場在天雄城東北面。”抓俘虜卻變收的斥候隊正回來稟報,“本來想抓個落單的問一問,沒想到靜太大,就只能先殺了。”
“怎麼把首給帶回來了?只帶個首級回來不行?”
“都監容稟,這事給遼人知道了不是不好嘛?”隊正是秦琬親兵出,沒有什麼不敢說的。
“會沒馬蹄印?”
隊正嘻嘻笑著,“那種事,都監一咬牙,什麼都不認,遼狗也沒轍。留下首證據就多了。”
“你這狗頭,就是。”秦琬笑罵了一句,一揮手,“辛苦了一夜了,先回去歇著吧。”
此時雄高唱,東方已白。遼國方向上,一片平靜,看不出半點的跡象。
秦琬看看王厚,王厚又回看過來,兩人都搖搖頭,折騰了這一夜,卻一頭霧水,實在讓人不痛快。
而還沒回來的一隊斥候,更讓秦琬揪心。天都亮了,人再也不回來,接下來一整天就沒機會了。
要是他們在遼境出了事,他責事小,給了遼人口實也沒什麼,折損了這些兵就虧大了。
就在秦琬憂心忡忡的時候,最後一隊斥候終於姍姍而歸,還領回一個年輕人來。
年輕人二十上下,整潔,上乾乾淨淨的。不是做工的,也不是務農的,沒有江湖中人的戾氣,謙恭有禮,像個店員。
他也的確是個商行裡做事的,跟軍隊看似不搭邊,但秦琬卻認識他。
“這是荀諒,在遼國那邊的商號裡做事,跟他東主一樣,都是末將派過去的人。”先跟王厚解釋了兩句,秦琬就問那年輕人,“荀諒,你怎麼跑回來了?是不是知道什麼?”
荀諒目不斜視,儘管王厚看起來明顯比秦琬地位高出許多,可他沒往王厚那邊窺視一眼,“回都監,是小東寨出事。由不知,小人只知道小東寨寨主領兵叛,一下就被剿滅了。”
“小東寨寨主領兵叛了!皮室軍的人也會叛?”秦琬幸災樂禍地嗤笑了一聲,又連聲追問,“爲什麼?有人跑出來沒有?從哪邊知道的。”
連問幾句,但那荀諒一概不知,最後一個問題纔回答說,是他躲在門後,聽到街上遼兵的對話。
秦琬無奈,“你家的東家派你來稟報的?”
“不是,是小人自作主張。”荀諒一抱拳,“東主三天前去涿州的,要過兩天才回來。”
又問了幾個問題,見沒有更多的消息,秦琬讓荀諒下去領賞、休息。
待荀諒離開,王厚問道,“他的東主是什麼人?”
“他的東主姓卓名順。”秦琬道,“幫末將打理些買賣上的事,是從順行裡出來的。”
猜你喜歡
-
完結4306 章
魔帝纏身:神醫九小姐
“夫人,為夫病了,相思病,病入膏肓,藥石無醫,求治!”“來人,你們帝尊犯病了,上銀針!”“銀針無用,唯有夫人可治,為夫躺好了。”“……”她是辣手神醫,一朝穿越成級廢材,咬牙下宏願︰“命里千缺萬缺,唯獨不能缺男色!”他是腹黑魔帝,面上淡然一笑置之,背地里心狠手辣,掐滅她桃花一朵又一朵,順帶寬衣解帶︰“正好,為夫一個頂十個,歡迎驗貨。
385.4萬字8 113543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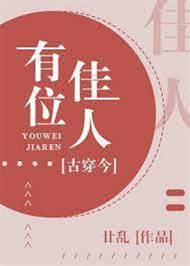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241 -
完結251 章

鳳馭天下:無情狂后
她是二十一世紀某組織的頭號殺手,因同伴背叛而中彈身亡,靈魂穿越到北越國,成為侯爺的女兒。而他則是深沉睿智的年輕帝王,運籌帷幄,步步為營,只想稱霸天下,當無情殺手遇上冷情帝王,當殺手與帝王共創霸業,結果會怎樣呢?…
70.2萬字8 17556 -
完結527 章

穿成五個反派的後孃
一朝穿越,竟然成了彆人的後孃,而且幾個孩子,個個都長成了大反派。究其原因,是因為這個後孃太壞太狠太不靠譜。喬連連汗顏,還好老天讓她穿過來,從此以後溫柔善良耐心矯正,幾個孩子從豆芽菜變成了胖多肉。可就在這時,孩子們的爹回來了。
91.5萬字8 302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