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邪》 第46章狐貍哄人的方式
鴻影被打得發矇,裡滿是鹹腥味,再回過神來,又是接連一陣耳。
「五公子,這到底是明輝閣的奴才,你就不怕我告訴老爺?」柳氏流著淚,「老爺說過,各院管各院的事兒,誰都不能越權,家規分明,眼下是你上宜院的人,欺人太甚,就算去了老爺哪兒,我也隻站得住理的!」
「你給我閉!」一聲怒喝,傅正柏站在門口,麵沉得能滴出墨來,「看看你養的好兒子,兔子還知道不吃窩邊草,這個孽畜竟然……」
說這話的時候,傅正柏瞧了一眼猶帶怒的靳月,冷聲長嘆。
家門不幸!
屋的傅雲傑正趴在門後聽靜,原本還聽得帶勁,驟聽得父親的聲音,嚇得連滾帶爬的躲回被窩裡「裝死」。
柳氏的臉乍紅乍白的,張了想申辯兩句,院子裡還站著不奴才,多雙眼睛看著,這個時候替兒子解釋,免不得會惹傅正柏生氣。
眼淚「吧嗒」落下,柳氏低訴,綿綿的跪在地上,「是妾管束不嚴,妾有愧於老爺!」
「自己的兒子是什麼德行,還需要旁人來提醒你?靳月才嫁傅家幾天,就敢鬧到這兒來打人?用你的豬腦子好好想清楚。」傅正柏恨鐵不鋼,氣得渾發抖,就差將手指在柳氏的腦門上了。
柳氏隻知道跪在地上哭,哭得讓靳月心煩。
「你們先回去!」傅正柏道。
傅九卿拾階而上,牽起靳月的手沖著傅正柏行了禮,轉往外走,臨走前,留下一句話,「記得把手留下!」
Advertisement
鴻影伏在地上,滿都是,聽得傅九卿這話,隻得的著柳氏。
「老爺!」柳氏啜泣,「即便傑兒有錯,鴻影護主又有何錯?五公子要鴻影一隻手,不是讓府裡的人,都來看妾的笑話嗎?」
「一個奴才,敢去攔九卿的新夫人?你腦袋是不是被驢踢了?」傅正柏咬著牙,狠狠著柳氏的腦門,「幹了什麼,你以為九卿沒看到?仗著你的份而肆意妄為,早晚害死你!虧你還這樣心肝的護著,真是蠢得可以!」
柳氏的淚還掛在臉上,卻是半句話都吐不出來。
「馬上就要離開衡州了,讓裡頭的人安分點,再敢招惹靳月,做出那些見不得人的事,就算九卿不找他算賬,我也要打斷他的,記住了嗎?」傅正柏低聲厲喝。
柳氏連連點頭,晃得髮髻上的簪都鬆了。
傅正柏抬手,將簪子扶正,「以後眼睛放亮點,若是連是非黑白都分不清,就不用再留著這對眼珠子了!」
原本,傅正柏拂袖而去。
臨走前,還是那句話,「照五公子的吩咐去做!」
鴻影倒伏在地,幾近歇斯底裡,「主子……主子,救救奴婢,主子……」
柳氏提溜著擺,心驚膽戰的瞧了一眼倒地的鴻影,快速離開了院子,傅正柏都這麼說了,這個妾室還能說什麼?若是惹怒了家主,自己定會扶正無。
還指著以後抬為平妻,兩個兒子就不再是庶出。
嫡庶分明,庶子和嫡子,總歸是不一樣的。
傅九卿牽著靳月進了上宜院,剛剛房門,便甩開了傅九卿的手,大步流星的往房走。待傅九卿進來,已經在收拾行囊,打理包袱了。
鼻間發出極為不屑的一聲輕嗬,傅九卿目冷冽的剜了一眼,拂袖落在了窗前坐著。
真是個沒心肝!
「傅九卿,你這個大騙子!」靳月手腳麻利,反正也沒什麼嫁妝,收拾起來很是方便,一個小包袱裝上幾套乾淨的裳,塞點小碎銀子就能走。
「來不及了。」傅九卿單手抵著太,角揚起一抹淡淡的笑,眸幽幽的瞧。
靳月呼吸一窒,這妖孽又想使「人計」或者「拖延計」不?
「君山!」傅九卿輕喚,淡漠的嘆口氣,手捋著服上的褶子。
君山進門,躬行禮,乍見靳月如此狀態,當即明白了公子的意思,忙不迭開口,「夫人這是收拾行囊,要去追靳大夫嗎?」
「廢話!」靳月抬步往外走,「誰也別攔著我,否則我爹出事,我定不會與你們罷休。」
「可是靳大夫已經走了!」君山忙道。
靳月駭然瞪大眼睛,「你說什麼?什麼時候走的?我爹不是說明、後天嗎?你們又在誆我!」
「盤纏是你親手遞出去的。」傅九卿的語氣淡淡的,似帶了幾分笑意,指尖隨手翻弄著窗邊的書冊,長睫垂著,也不知藏了什麼緒。
靳月當場石化,僵在原地,嗓子裡發不出半點聲音。彷彿全的氣力被離,跌坐在凳子上,將包袱重重的擱在桌案上,眼皮耷拉著,有東西在眼眶裡盈。
他明明知道,最在乎的就爹,當初嫁傅家沖喜,亦是為了父親平安。
可現在……
傅九卿的指尖輕輕瞧著書冊,微落在他的手背上,泛著些許無言的蒼白。
室,一片死寂。
霜枝從外頭進來,沖著傅九卿和靳月行了禮,「飛鴻閣那頭派人來說,鴻影的手已斷,請公子和夫人放心。」
傅九卿的指尖作稍稍一頓,君山當即沖著霜枝使了個眼,二人快速退出房間。
「你為何這麼做?」靳月衝到他麵前站著,氣鼓鼓的樣子,像盆裡養的河豚一般,扯著嗓門喊,「戲弄人也該有個度,你三番四次的捉弄我,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口氣說完這些話,彷彿心頭的怨氣也跟著散了不,靳月心口砰砰跳,眨眼著傅九卿,生怕他心一橫,把毒啞了。
就像打斷鴻影的手一樣,隻是他輕飄飄的一句話。
「氣消了,就坐下來說話。」傅九卿間微啞,子往側稍移。
靳月咬著,別開頭不去看他。
誰說氣消了?
還生著氣呢!
傅九卿也不管,拿著書冊若無其事的翻著,極是完的側,籠在微中,額頭潔,鼻樑筆,薄微微抿起,漸漸浮起抹不開的涼意。
清冷,孤傲。
邊的墊子稍稍一沉,靳月終是坐了下來,隻是……背對著他。
他一扭頭,正好看到齊腰輕垂的青,如新墨,澤如綢緞。他下意識的後,修長如玉的指尖,輕輕纏了一縷青,指尖的,讓他的心頭微微一。
傅九卿眸深深,角不自覺的挽起,嗓子裡有些莫名的發。
靳月背對著他,自然不知他的小作,顧自生著氣,打定主意不想理他,除非他能給一個合理的解釋。隻是,驕傲如他,定不會解釋!
「立個威,到了京都城,就不會有人敢你。」他彎腰,伏在肩頭對著的耳畔淺聲輕語,「誰讓傅雲傑那個蠢貨招惹你……嗯!」
尾音拖長,帶著些許抑的緒輕。
突如其來的暗啞在耳畔迴旋,驚得靳月駭然轉,溫暖的,猝不及防的了上去……近在眼前的模糊,彷彿是守株待兔的狐貍,等到了不安分的小兔子,主和解!
靳月心驚,慌忙仰退開,誰知腰間一。
狐貍圈著的腰,眸幽邃,音沙啞而極盡蠱,「月兒說原諒的方式,很特別!」
呼吸一窒,靳月的手腳,莫名的發,「你你你故意的!」
「乖乖聽話,你爹會在京都等你!」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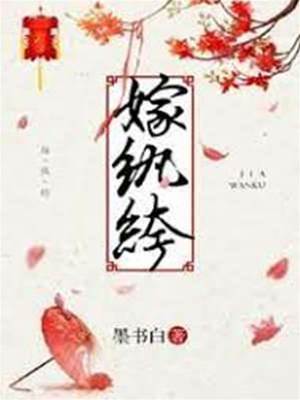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94 章

驚雀
虞錦乃靈州節度使虞家嫡女,身份尊貴,父兄疼愛,養成了個事事都要求精緻的嬌氣性子。 然而,家中一時生變,父兄征戰未歸生死未卜,繼母一改往日溫婉姿態,虞錦被逼上送往上京的聯姻花轎。 逃親途中,虞錦失足昏迷,清醒之後面對傳言中性情寡淡到女子都不敢輕易靠近的救命恩人南祁王,她思來想去,鼓起勇氣喊:「阿兄」 對上那雙寒眸,虞錦屏住呼吸,言辭懇切地胡諏道:「我頭好疼,記不得別的,只記得阿兄」 自此後,南祁王府多了個小小姐。 人在屋檐下,虞錦不得不收起往日的嬌貴做派,每日如履薄冰地單方面上演著兄妹情深。 只是演著演著,她發現沈卻好像演得比她還真。 久而久之,王府眾人驚覺,府中不像是多了個小小姐,倒像是多了個女主子。 後來,虞家父子凱旋。 虞錦聽到消息,收拾包袱欲悄聲離開。 就見候在牆側的男人淡淡道:「你想去哪兒」 虞錦嚇得崴了腳:「噢,看、看風景……」 沈卻將人抱進屋裡,俯身握住她的腳踝欲查看傷勢,虞錦連忙拒絕。 沈卻一本正經地輕飄飄說:「躲什麼,我不是你哥哥嗎」 虞錦:……TvT小劇場——節度使大人心痛不已,本以為自己那嬌滴滴的女兒必定過得凄慘無比,於是連夜快馬加鞭趕到南祁王府,卻見虞錦言行舉止間的那股子貴女做派,比之以往還要矯情。 面對節度使大人的滿臉驚疑,沈卻淡定道:「無妨,姑娘家,沒那麼多規矩」 虞父:?自幼被立了無數規矩的小外甥女:???人間不值得。 -前世今生-我一定很愛她,在那些我忘記的歲月里。 閱讀指南:*前世今生,非重生。 *人設不完美,介意慎入。 立意:初心不改,黎明總在黑夜后。
21.3萬字7.83 21942 -
完結866 章

神醫魔后
21世紀玄脈傳人,一朝穿越,成了北齊國一品將軍府四小姐夜溫言。 父親枉死,母親下堂,老夫人翻臉無情落井下石,二叔二嬸手段用盡殺人滅口。 三姐搶她夫君,辱她爲妾。堂堂夜家的魔女,北齊第一美人,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個笑話。 她穿越而來,重活一世,笑話也要變成神話。飛花爲引,美強慘颯呼風喚雨! 魔醫現世,白骨生肉起死回生!終於,人人皆知夜家四小姐踏骨歸來,容貌傾國,卻也心狠手辣,世人避之不及。 卻偏有一人毫無畏懼逆流而上!夜溫言:你到底是個什麼性格?爲何人人都怕我,你卻非要纏着我? 師離淵:本尊心性天下皆知,沒人招惹我,怎麼都行,即便殺人放火也與我無關。 可誰若招惹了我,那我必須刨他家祖墳!
228.2萬字8 394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