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和他的白貓師尊》 師尊的回憶
兩人來到飛花島的一海崖邊,那裏怪石嶙峋,下頭就是波濤洶湧的大海,海浪撞擊在巖石上頃刻碎萬點雪沫,四周什麽都沒有,唯剩茫茫海,一新月。
墨燃召來與自己定契的那把佩劍,而後轉頭問楚晚寧:“師尊為何不會劍?”
“不是不會。”楚晚寧,“是不擅長。”
“怎麽個不擅長法?”
楚晚寧一揮袖,神裏多了幾分矜傲,但耳朵卻紅了:“我隻能在離地麵不遠的地方飛。”
墨燃有些驚訝,劍這種東西,離地一寸和離地百米,所消耗的靈力都是一樣的,既然楚晚寧能在離地不遠的地方飛,沒道理不能升到高空去,便:“師尊你試一試,我看看。”
“……”楚晚寧倒是沒有召劍,而是麵容寡淡道,“我平日不願劍,是覺得武終究需被敬重,踩在腳下,未免不妥。”
“?”
不知道他為何忽然解釋起來,但墨燃還是點了點頭。
“師尊的不錯。……但……我們總不能躺在劍上,或者掛在劍上飛吧。”
Advertisement
楚晚寧一時語塞,抬頭卻見月下,那個男人笑地瞧著自己,不由惱恨,道:“平日裏,若有急事,我都是用升龍結界飛行的。”
墨燃微怔:“那條龍?”
“它可以變大。”楚晚寧道,似乎稍微挽回了些麵,但很快又有些尷尬,“不過遇到儒風門之變那場大火,就全然沒有用武之地了。它怕火。”
墨燃恍然:“所以師尊要學劍,是想——”
“以備不時之需。”
墨燃不吭聲了,臨沂滾滾濃煙,怒焰火海,吞噬了多命。那個時候,楚晚寧立在自己劍上,看著下麵的凡人被劫火吞噬,一攏一簇的被燒灰,連碎骨都不會剩下,而堂堂仙尊卻什麽都做不了,不能劍去載任何一個人,當時的楚晚寧,會是什麽心?
難怪這個出門寧願乘馬車,都懶得劍的人,會忽然間跟自己的徒弟提出這樣的要求。
“我知道了,師尊不必擔心,我一定好好教你。”
聽他這麽,楚晚寧也沒作聲,垂落眼簾,不知道在想些什麽,但他最後還是歎了口氣,抬手道:“懷沙,召來。”
一道金倏忽凝起,墨燃便在這靜謐安詳的海月裏,再次見到了那把前世和他生死對決時才出現過的神武。
楚晚寧的殺伐之刃——
懷沙。
那是一把一看就很楚晚寧的長劍,這世上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比楚晚寧更適合當它的劍主了。它紋飾寡淡,通流金,因為金太刺目,甚至微微泛著蒼白。那芒源源不斷,十分從容地從劍上流淌下來,垂落於夜之中,猶如燃燒著的煙花線,又像落的白細沙。
“這是懷沙。”楚晚寧看著它,道,“你沒見過,它戾氣太重,我不常用。”
墨燃心複雜,半晌點了點頭,低沉道:“是把好劍。”
夜風習習,墨燃踏上了自己那把佩劍的劍,腳尖微,佩劍就馴順地緩緩抬起,離地數寸。
墨燃回頭對楚晚寧:“師尊也試試。”
楚晚寧也站在了懷沙上,懷沙十平八穩地也上升了數寸,載著楚晚寧原地繞了一圈。
“這不是好的麽?”墨燃,“再起來一些試試。”他著,控劍飛到了約為五尺的位置,低頭朝楚晚寧笑了笑,“上來這裏。”
“……”
楚晚寧抿了抿,不吭聲地將懷沙升到與他齊平的位置。
墨燃道:“沒什麽問題,師尊,你不是會麽?我們再——”
他驀地住了,因為他忽然注意到楚晚寧臉蒼白,整張麵容的線條繃地極,一雙垂落的睫和風中卷草般簌簌抖著,似乎在竭力忍著什麽。
墨燃低頭看了看才離地五尺不到距離。
再抬頭,難以置信地瞪著楚晚寧。
他心中忽然有個非常荒謬的想法——
師尊不會劍,該不會是因為……怕高吧??
墨燃:“……”
這就非常尷尬了,他也覺得很匪夷所思。楚晚寧這個人輕功很好,巍巍樓宇上就上,下就下,足尖一點掠地數丈,這樣的人怎麽會恐高?可是觀察立在劍上的這個人,確實是麵難看,目遊離,哪怕極力按捺,眉宇間依舊出些薄薄的惶然。
墨燃試探道:“師尊?”
楚晚寧的反應有些激烈,他倏忽抬頭,夜風拂了他的碎發,但他也不抬手去掠,一雙吊梢目裏閃著惱意,在紛的額發後頭迸濺著警惕的花火:“嗯?”
“咳……噗。”
“你笑什麽!!!”
“我是嗓子幹了,咳嗽。”
墨燃拚命忍著笑,他想,沒跑了,原來真的是恐高,難怪剛剛解釋了那麽多,就是想給自己留點麵。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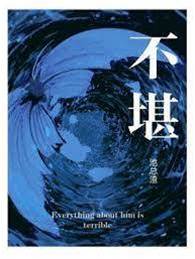
不堪
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三觀不正,狗血淋頭,閱讀需謹慎。】 每個雨天來時,季衷寒都會疼。 疼源是八年前形如瘋魔,暴怒的封戚所留下的。 封戚給他留下了痕跡和烙印,也給他傷痛和折磨。 自那以后,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高人氣囂張模特攻x長發美人攝影受 瘋狗x美人 封戚x季衷寒 標簽:HE 狗血 虐戀
20.2萬字8 6022 -
完結178 章

浮京一夢
蘭燭見到江昱成的那天,她被她父親帶到他面前,父親卑躬屈膝地討笑着,叫着對方江二爺。 江昱成隨意翻着戲摺子,頭也不擡,“會唱《白蛇》?” 蘭燭吊着嗓子,聲音青澀的發抖。 江二爺幫着蘭家度過難關,父親走了,留下蘭燭,住在江家槐京富人圈的四合院閣樓裏。 蘭燭從那高樓竹窗裏,見到江昱成帶回名伶優角,歌聲嫋嫋,酒色瀰漫。 衆人皆知槐京手腕凌厲的江家二爺,最愛聽梨園那些咿呀婉轉的花旦曲調, 不料一天,江家二爺自己卻帶了個青澀的女子,不似他從前喜歡的那種花旦俏皮活潑。 蘭燭淡漠寡言,眉眼卻如秋水。 一登臺,水袖曼妙,唱腔哀而不傷。 江昱成坐在珠簾後面,菸灰燙到手了也沒發現,他悵然想起不知誰說過,“青衣是夢,是每個男人的夢。” 他捧蘭燭,一捧就是三年。 蘭燭離開江家四合院閣樓的那天,把全副身家和身上所有的錢財裝進江昱成知她心頭好特地給她打造的沉香木匣子裏。 這一世從他身上受的苦太多,父親欠的債她已經還完了,各自兩清,永不相見。 江昱成斂了斂目,看了一眼她留下的東西,“倒是很有骨氣,可惜太嫩,這圈子可不是人人都能混的。” 他隨她出走,等到她撞破羽翼就會乖乖回來。 誰知蘭燭說話算話,把和他的關係撇的乾乾淨淨。 江昱成夜夜難安,尋的就是那翻轉的雲手,水袖的輕顫。 他鬼使神差地買了名動槐京蘭青衣的票場子,誰知蘭燭卻不顧這千人看客,最終沒有上場。 江昱成忍着脾氣走到後臺化妝間,看到了許久的不見的人, 幾乎是咬着牙問到:“蘭燭,爲什麼不上場” 蘭燭對鏡描着自己細長的眉,淡漠地說:“我說過,不復相見。” “江二爺,這白蛇,實在是不能再爲你唱了。”
28.1萬字8 1560 -
完結161 章

離婚那天,傅少跪在她裙邊求原諒
結婚五年,她以為自己可以焐熱傅宴禮的心,等來的卻是他的一紙離婚協議,他前女友的回歸更是成了壓垮她們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姜瑤看著朋友圈老公為前女友慶生的照片徹底的心灰意冷,主動簽下離婚協議成全他。傅宴禮不愛姜瑤,這是一個圈子里皆知的秘密,當年傅宴禮是被逼婚娶了姜瑤,所有人都為他鳴不平,等著姜瑤被休下堂,傅公子可以迎娶心上人幸福一生。 然而,真到了這一天,一向尊貴無雙的傅公子卻固執的拉住她的手,紅著眼卑微祈求,“瑤瑤,我知道錯了,咱們不離婚行不行?”
30.2萬字5 125 -
完結93 章

晚一點愛上你
穿著自己媳婦兒設計的西裝完成婚禮,季則正覺得自己計劃周全,盡在掌握。自從遇見她,記住她,他開始步步為營,為她畫地為牢。 帶著傷痛的她,驕傲的她、動人的她,都只是他心中的陸檀雅。 這一回陸檀雅不會再害怕,因為冥冥之中上天早有安排,錯的人總會離開,對的人方能共度余生。 “遇見你似乎晚了一點,但好像也剛剛好。”
26.4萬字8 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