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后,港圈大佬強制愛!》 第1卷 第199章 歡迎回港
漆黑的房間開了一盞小夜燈,暖晃的線勾勒上側臉廓,酣睡著,周溢出的氣息都是溫無害。
小,白,看起來就很好欺負。
男人如鬼魅般掩藏在暗,仗著看不見,肆無忌憚的將渾看遍,灼熱的似要將看才罷休。
倏然,目定在往外出的小,瘦弱的腕骨之下,腳趾可的挨靠,底板暈。
他眸沉一寸,結滾了滾。
手忍不住出去,在墻面映出壯的影,大掌強勢籠住孩的腳踝,糲指腹在青管挲。
久違的,讓男人眼尾泛起紅。
他什麼都沒做,將的塞回薄毯中,半跪下,保持著一個姿勢,持續很久。
他目貪,癡。
病態的澤染紅,眼球可怖可泣,似思念到盡頭,終于…終于,得到一點,一點點靠近的機會。
曉浮出,孩安靜沉睡,熾熱的線爬上地板,快蔓到他腳邊,他突然起,手掌很輕的下的發。
鶴行止沒再停留,走出房間。
他知道,天大亮時,他必須得離開,他在京初這,只能做個孤魂野鬼。
清晨。
京初睡個飽覺,起來個懶腰,側頭發現外面已經風平浪靜,臺風過去,地上忙碌一群人。
下午需要趕飛機去參加鄰國的邀約演出,洗漱好,拉開房門。
腳步一停,瞳孔驟。
只見,開門的一霎,隔壁的門也開了,男人手握住酒杯,上的浴袍松松垮垮,風大泄。
Advertisement
察覺的眼神,他有意無意攏下浴袍帶子。
京初:“?”
把當狼了?
手扣著門把,急忙避開視線,卻聽見頭頂傳來一聲,“看夠了?”
“我可沒想看!”
那是無意的。
聽他意味深長的語氣,恨不得時倒轉,躲在房間晚點出來。
“哦”
男人淡瞥眼,低啞的聲線慵懶,“沒看,你臉紅什麼。”
驚,急忙用手心捂下臉。
是有一點燙,但只有一點。
鶴行止無視在原地的凌,躺在沙發上,灌完杯中的紅酒。
他鎮定的很,京初想過去解釋又覺得沒必要,看都看了,又不是了,算不上擾,再說是他自己不好好穿服。
風馬蚤的一如既往,怪誰?
思來想去,準備出去,房門打開,鶴行止的視線看過來。
“咔”
門合上。
他垂眸,放下杯子,疊著長,仰頭靠在沙發上,結猛烈過,吞云吐霧,指尖的猩紅燙過手背。
他呼吸一停。
五個字。
和他說了五個字。
日子一如既往進行著,京初一個月的工作行程還算滿,忙忙碌碌中出一周時間陪母親回京市,在國外待久,恰好京初也畢業,工作各地飛,總要有落腳的地方。
思來想去,回家。
原先司買下他們的別墅,他獄后這棟別墅被法院流拍,落一戶人家手中。
回國前抱著僥幸,問對方能不能轉讓,奈何價太高,本以為事就這樣不了了之,對方又說可以借租。
呂玉玲當時眼睛都亮了,也沒多猶豫,立馬答應。
踏時隔已久的別墅,看院子里盛開的芍藥花,京初愣在原地,眨下眼,眼模糊眼球,劃的一個圈旋轉起一幀畫面。
年時,父親白玫瑰,芍藥,于是院子里種滿這兩種花。
司接手后,院子里變蔬菜園。
而如今,院子里芍藥花布,蝴蝶盤旋在香中,在金燦的中,出現丁達爾效應,夢幻如畫。
“真巧,這家主人竟然也喜歡芍藥。”
呂玉玲看到久違的別墅,慨,“我們回家了,要是你父親在,就能看到他種的白玫瑰。”
到母親的傷,京初抱住的胳膊,目從花中挪開,“我們進去吧。”
洋樓別墅上下都收拾的很整潔,看得出買家應該是干凈的,一進去,一塵不染,都不需要打掃。
收拾完,母倆晚餐吃的餃子。
臨睡時,接到一份來自港城某劇場的工作邀約,京初想了會,還是應下。
港城有朋友,三年不見,借此機會見一面也好。
至于鶴行止...
窗外的月飄進室,撒在眼里清冷一片,孩咬,回憶起在法國那晚,他眼里對沒有以往的病態偏執,全是疏離。
也是,三年過去,誰都該放下了。
更何況,他應該也有朋友了。
劇院后臺。
京初換好舞服在候場,背對著門口,約聽見路過的舞蹈演員說:“我去,港城那位爺來了。”
“誰啊?”
“鶴行止”
名字的尾音飄耳廓,鏡子里,京初臉白了寸。
怎麼會這麼巧?
心里閃過一陣惶恐,來不及多想,工作人員通知候場。
紅幕拉開,站在臺上翩翩起舞,繃足旋轉時能到臺下一道炙熱的目。
眸微轉對上第一排,正中央,鶴行止的黑眸。
他勾,舞畢時,漫不經心的鼓掌。
謝幕后,京初心有余悸,滿腦子想的都是他為什麼會來?
看演出?他以前也沒這麼閑。
在后臺桌上,一如既往收到jing先生的花束,瞥過卡片,驚訝發現這次竟然不是法語,是一句筆鋒剛勁的中文。
【歡迎回港】
換完服往外走,路過拐角,一雙黑皮鞋踏眼底,目跟隨長往上抬,鶴行止盯住不放。
手提包,“你又要做什麼?”
防備,警惕寫在臉上。
鶴行止斂眸,含笑道:“京初,路不是你家開的,你這姑娘是不是太霸道了點?”
他裹上溫潤的氣質,手撥弄佛珠,優越高的鼻梁架著金眼鏡,一雙眸波瀾不驚,領口懶散的敞開,結輕的弧度著幾分。
勾時,妥妥一斯文敗類。
他看起來目并無侵略,京初心安定下來,準備繞過他離開。
忽然,后一聲:
“行止”
京初走在圓柱旁,腳步定了定。
一金長,金發碧眼的寧千月踩著高跟鞋過來,熱的挽住他的胳膊,語調親昵,“久等了,親的”
空氣沉寂幾秒。
的目和京初對上,眼里劃過一戲謔,朝擺了擺手,“你好,京初”
京初看著男人的背影,垂下眼簾。
他竟然和寧千月走到一起。
這次,原來是陪看演出。
京初輕扯,低聲,“我先走了,寧小姐。”
“嗯,再見。”
孩走遠,并未看見鶴行止翳的臉,正折過人的手臂,幾要碎,冷聲,“別做沒意義的事。”
寧千月臉鐵青,“我爹給我下聯姻的令,你要真喜歡,我不介意你娶了我,把養在外面。”
“又不肯嫁你……”
“嘶”
他手勁更大。
仿佛聽到骨頭碎裂的聲音。
就在快痛暈過去時——
鶴行止冷著臉,甩開的手,下高定外套,扔進垃圾桶。
離開時留下一句:
“我只娶一個。”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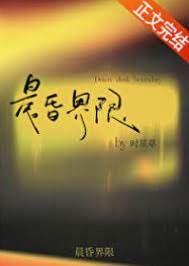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