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奴三年后,整個侯府跪求我原諒》 第817章 救人有錯嗎?
喬念立刻指揮兩名侍從將沈越扶起,送回去休息,這才轉對阿九吩咐:“去熬一碗安神湯來。”
阿九應了聲是,立刻就去忙了。
喬念一路跟著,回到了沈越的房中,親眼看著阿九小心翼翼地一勺勺將湯藥喂沈越口中。
直到確認他完全飲盡,呼吸逐漸平穩,陷沉睡,繃的神才稍稍放松。
影七悄無聲息地跟在后。
谷中的風帶著幾分涼意拂過,平白人心里難不安了幾分。
影七低沉沙啞的聲音也忽然在著寂靜的廊下緩緩響起:“解蠱的反噬竟如此猛烈……沈越這次,當真是自討苦吃了。”
喬念的腳步微微頓了頓,卻沒有回應。
繼續向前走著,影被拉得很長。
走到廊橋中央時,才突然停下了腳步,轉過來。
眸中映著清晰可見的困與掙扎。
“他為何要這樣做?”的聲音很輕,仿佛在問影七,又像是在問自己,“從一開始,他就應該清楚地知道這麼做的后果。為什麼還要執意如此?”
為了讓知道,不是什麼人都該救的?
就……需要如此大的犧牲嗎?
影七聞言一怔,隨即低下頭,避開了的視線。
他抿著,同樣無法給出答案。
庭院中只剩下微風拂過樹梢的沙沙聲。
良久,喬念才又輕聲開口,聲音里帶著幾分不確定:“難道……真的是我錯了嗎?我不該救人嗎?”
Advertisement
影七猛地抬起頭,眉頭鎖,斬釘截鐵地說道:“當然不是!救人命怎會有錯?”
話音落下,兩人再次陷沉默。
四周只有蟲的低鳴和風吹過竹林的聲音。
既然救人無錯,那沈越為何要選擇這樣一條路?
這個疑問在谷中彌漫開來,找不到答案。
時間悄然流逝,轉眼已是兩日后。
蕭衡在一片朦朧的暈中緩緩睜開了眼睛。
首先映眼簾的是陌生的青紗帳頂,空氣中彌漫著一淡淡的草藥清香。
過糊著蟬翼紗的窗欞和地灑屋,在青石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影。
細小的塵埃在柱中無聲地飛舞,如同跳躍的金。
他試著移,卻發現四肢沉重得如同灌了鉛一般。
勉強撐起子,一陣眩暈襲來,讓他不得不靠在床頭息。
就連這樣簡單的作,都讓他到前所未有的疲憊。
他長長地嘆了口氣,抬手著陣陣作痛的太,試圖理清混的思緒。
就在低頭的剎那,一段段記憶如同決堤的洪水般洶涌地沖他的腦海——
他清晰地“看”見自己如同被縱的木偶,眼神空卻招式狠厲地攻向楚知熠;
甚至能清晰地“覺”到長劍刺對方時那一瞬間的阻力,繼而劍鋒破而時傳來的令人心悸的震,溫熱的鮮濺在他手上的依然鮮明。
他……殺了楚知熠?
這個認知如同一把冰錐刺心臟,蕭衡的臉瞬間變得慘白如紙。
一寒意從脊背竄上,讓他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
他真的殺了楚知熠?
那念念呢?念念該有多麼傷心?
豈不是要恨了他?!
還未等他理清思緒,另一段更可怕的記憶接著席卷而來。
他“看”見自己的手練地將各種毒搗碎、混合,然后毫不猶豫地投丹爐;“看”見紫黑的毒煙洶涌而出,貪婪地吞噬著周圍的一切;
而最讓他心驚的是,他竟“看”見自己的雙手,死死扼住了喬念纖細的脖頸。
他能到脆弱的骨在自己掌心下無助地抖,看見因窒息而漸漸漲紅發紫的臉龐,更看見那雙總是蘊著溫和或狡黠暈的眸子,因痛苦與難以置信而迅速黯淡,最終布滿絕……
“呃啊——!”
蕭衡從間出一聲破碎的哀鳴,整個人如被無形巨錘擊中般劇烈地痙攣起來。
他猛地蜷起子,十指死死發間,指甲深陷頭皮,帶來尖銳的刺痛——仿佛唯有這的苦楚,才能稍稍抵消那幾乎要將他撕裂的愧疚與自我憎惡!
他怎能做出這種事?怎能殺了最的人?又怎能……那樣對待?!
巨大的痛苦與罪惡如同粘稠的黑泥,將他拖無底深淵,窒息的抑將他層層包裹。
他恨不得那柄長劍當時刺穿的是自己的心臟!
就在這時,門外廊下傳來極輕微的腳步聲,伴隨著喬念低低的、著幾分疲憊的沙啞嗓音,正在輕聲吩咐著凝霜什麼。
蕭衡心下一慌,剎那間竟不知該如何面對,只得匆忙重新躺下,閉雙眼,假裝仍未蘇醒。
心跳如擂鼓,生怕被察覺出異樣。
不多時,房門被輕輕推開。
他聽見喬念的腳步漸近,最終停在他的床邊。
“還沒醒麼?”輕聲自語,隨后一只微涼的手輕輕搭上他的腕脈。
一旁傳來凝霜的回應:“是,奴婢一盞茶前來看時,還未醒。”
但喬念知著指尖下跳急促的脈搏,忍不住看向了蕭衡。
面蒼白,眉頭蹙,長睫不住地輕,額間甚至滲出細的汗珠。
他明明醒了。
只是不知為何,不愿面對。
喬念沒有說破,只是淡淡笑了笑,語氣一如既往的輕:“無妨,他的已無大礙,早晚會醒的。”
聽到這話,他那濃的睫得愈發厲害,卻仍舊固執地閉雙眼。
喬念不再多言,領著凝霜悄然離去。
直到房門輕輕合攏,腳步聲漸行漸遠,蕭衡才緩緩睜開雙眼。
卻如溺水之人般,呼吸徹底失了規律,口劇烈起伏著。
他不明白……為何喬念還愿這般溫待他?
莫非楚知熠還沒死?
可是……他的記憶那般真切。
他知道自己的劍確確實實刺穿了楚知熠的心口。
那,就如同……就如同當年,他眼睜睜看著荊巖死在自己面前時一樣!
塵封太久的記憶被驟然掀開,心口痛愈來愈烈,幾乎要將他撕裂。
荊巖臨死前殷切的目,那句“照顧好念念”的囑托,如今都化作最鋒利的刀刃,一遍遍凌遲著他的心。
他究竟都做了些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2088 章

廢柴王妃又在虐渣了
蕭涼兒,相府大小姐,命格克親,容貌被毀,從小被送到鄉下,是出了名的廢柴土包子。偏偏權傾朝野的那位夜王對她寵之入骨,愛之如命,人們都道王爺瞎了眼。直到人們發現,這位不受相府寵愛冇嫁妝的王妃富可敵國,名下商會遍天下,天天數錢數到手抽筋!這位不能修煉的廢材王妃天賦逆天,煉器煉丹秘紋馴獸樣樣精通,無數大佬哭著喊著要收她為徒!這位醜陋無鹽的王妃實際上容貌絕美,顛倒眾生!第一神醫是她,第一符師也是她,第一丹師還是她!眾人跪了:大佬你還有什麼不會的!天才們的臉都快被你打腫了!夜王嘴角噙著一抹妖孽的笑:“我家王妃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是個柔弱小女子,本王隻能寵著寵著再寵著!”
400.4萬字8.08 204045 -
完結18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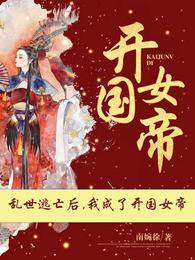
亂世逃亡后,我成了開國女帝
◣女強+權謀+亂世+爭霸◥有CP!開局即逃亡,亂世女諸侯。女主與眾梟雄們掰手腕,群雄逐鹿天下。女主不會嫁人,只會‘娶’!拒絕戀愛腦!看女主能否平定亂世,開創不世霸業!女企業家林知皇穿越大濟朝,發現此處正值亂世,禮樂崩壞,世家當道,天子政權不穩,就連文字也未統一,四處叛亂,諸王征戰,百姓民不聊生。女主剛穿越到此處,還未適應此處的落后,亂民便沖擊城池了!不想死的她被迫逃亡,開
238萬字8.18 16115 -
完結129 章

盛寵
【全文完結】又名《嫁給前童養夫的小叔叔》衛窈窈父親去世前給她買了個童養夫,童養夫宋鶴元讀書好,長得好,對衛窈窈好。衛窈窈滿心感動,送了大半個身家給他做上京趕考的盤纏,歡歡喜喜地等他金榜題名回鄉與自己成親。結果宋鶴元一去不歸,并傳來了他與貴女定親的消息,原來他是鎮國公府十六年前走丟了的小公子,他與貴女門當戶對,郎才女貌,十分相配。衛窈窈心中大恨,眼淚汪汪地收拾了包袱進京討債。誰知進京途中,落難遭災,失了憶,被人送給鎮國公世子做了外室。鎮國公世子孟紓丞十五歲中舉,十九歲狀元及第,官運亨通,政績卓然,是為本朝最年輕的閣臣。談起孟紓丞,都道他清貴自持,克己復禮,連他府上之人是如此認為。直到有人撞見,那位清正端方的孟大人散了發冠,亂了衣衫,失了儀態,抱著他那外室喊嬌嬌。后來世人只道他一生榮耀,唯一出格的事就是娶了他的外室為正妻。
31.9萬字7.92 62628 -
完結99 章

和死對頭成婚后
六公主容今瑤生得仙姿玉貌、甜美嬌憨,人人都說她性子乖順。可她卻自幼被母拋棄,亦不得父皇寵愛,甚至即將被送去和親。 得知自己成爲棄子,容今瑤不甘坐以待斃,於是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死對頭身上——少年將軍,楚懿。 他鮮衣怒馬,意氣風發,一雙深情眼俊美得不可思議,只可惜看向她時,銳利如鷹隼,恨不得將她扒乾淨纔好。 容今瑤心想,若不是父皇恰好要給楚懿賜婚,她纔不會謀劃這樁婚事! 以防楚懿退婚,容今瑤忍去他陰魂不散的試探,假裝傾慕於他,使盡渾身解數勾引。 撒嬌、親吻、摟抱……肆無忌憚地挑戰楚懿底線。 某日,在楚懿又一次試探時。容今瑤咬了咬牙,心一橫,“啵”地親上了他的脣角。 少女杏眼含春:“這回相信我對你的真心了嗎?” 楚懿一哂,將她毫不留情地推開,淡淡拋下三個字—— “很一般。” * 起初,在查到賜婚背後也有容今瑤的推波助瀾時,楚懿便想要一層一層撕開她的僞裝,深窺這隻小白兔的真面目。 只是不知爲何容今瑤對他的態度陡然逆轉,不僅主動親他,還故意喊他哥哥,婚後更是柔情軟意。 久而久之,楚懿覺得和死對頭成婚也沒有想象中差。 直到那日泛舟湖上,容今瑤醉眼朦朧地告知楚懿,這門親事實際是她躲避和親的蓄謀已久。 靜默之下,雙目相對。 一向心機腹黑、凡事穩操勝券的小將軍霎時冷了臉。 河邊的風吹皺了水面,船艙內浪暖桃香。 第二日醒來,容今瑤意外發現脖頸上……多了一道鮮紅的牙印。
25.2萬字8 140 -
完結123 章

不是聯姻嗎?裴大人怎麼這麼愛
姜時愿追逐沈律初十年,卻在十八歲生辰那日,得到四個字:‘令人作嘔’。于是,令沈律初作嘔的姜時愿轉頭答應了家里的聯姻安排,準備嫁入裴家。 …… 裴家是京中第一世家,權勢滔天,本不是姜時愿高攀得起的。 可誰叫她運氣好,裴家英才輩出,偏偏有個混不吝的孫子裴子野,天天走雞斗狗游手好閑,不管年歲,還是性格,跟她倒也相稱。 相看那日—— 姜時愿正幻想著婚后要如何與裴子野和諧相處,房門輕響,秋風瑟瑟,進來的卻是裴家那位位極人臣,矜貴冷肅的小叔——裴徹。 …… 裴太傅愛妻語錄: 【就像御花園里那枝芙蓉花,不用你踮腳,我自會下來,落在你手邊。】 【愛她,是托舉,是陪伴,是讓她做自己,發著光。】 【不像某人。】
23.8萬字8.09 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