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春山》 第96頁
“兄長…!”戚白商一驚,卻已經被戚世抱得凌空。
紅服蹭過的簪發,戚世平穩地將抱下馬車, 踏過安府門前的石板泥洼。
“了傷,就不要逞能。”
戚世嚴肅告誡。
“…哦。”
安府外的巡捕營兵卒們不悄然投過視線, 戚白商剛想將細頸往低藏一藏,就忽覺著,頸后像是被什麼涼冰冰的風刺了一下。
莫名一栗, 從戚世懷里回頭。
目所及,只有一輛陌生的員家眷制式的馬車,就停在他們的馬車后不遠。
車駕側的窗扉,正一只冷白修長的手扣回。
那只手……
骨節分明又漂亮,指節卻覆著薄繭,手背上張弛起伏的脈絡又著明顯的張力,是一只慣了刀槍劍戟的男人的手。
而且很眼。
得心口都有些栗然,只覺著上某些地方像還留著曾被它輕慢玩弄的。
不,不會的。
戚
𝑪𝑹
白商臉微白,忙轉回眼。
一定是想多了。無緣無故地,那個人怎麼會出現在這兒。
是他給留下的噩夢太深刻了。
被戚世放到踏跺上,戚白商慌忙推后了步,直起:“多謝兄長。”
從烏黑的鬢發旁出,白皙小巧的耳廓沁著的艷紅。
戚世余瞥見,微微一怔:“是冷麼,耳朵為何這般紅?”
“不是…”
“……”
隔著厚重的馬車,子乖慵赧然的聲音很快就遁宅院,再尋不見了。
“哎呀呀,畢竟不是親兄妹,這般舉止,多有些不合適了吧?”
云侵月藏不住狐貍笑,只能拿扇子遮著。
他眼睛彎得快了月牙,笑地從扇子上面窺向那個側倚在窗畔,披不住畫皮而眼神霜涼、冷面修羅似的某人。
Advertisement
“也是,戚大人一大紅袍在,最惹懷春,被他抱上一抱,可不逗得戚家姑娘臉紅嗎?”
謝清晏垂睫停了半晌。
到此刻,他才懶抬回眼,“這麼好奇,我送你去他懷里懷春?”
“哎哎,謝琰之,遷怒我,你這可就是玩不起了啊。”
“……”
安府當前,又親眼見戚白商戚世圈抱在懷中,只著半截纖白頸子。不知有沒有也靠在戚世肩上,將細碎的氣息拂過對方結與下頜,就像那日和他……
謝清晏眼神愈發沉晦,他沒了再與云侵月斗的興致,叩了下窗扉。
“其傷。轉馬,從側門府。”
“是,公子。”
“……”
謝清晏是自己一人了安府,沒許云侵月與董其傷陪同。
巡捕營是父親元鐵麾下,而京兆府的人便是認不得他,那一狐裘與抬眼間凌冽殺伐之氣,也他們不敢妄。
鎮國公也來安府了的消息在巡捕營兵卒間低傳,于是人人不敢聲張,也人人有了見之便避、權當不曾見的默契。
謝清晏便這樣一路過廊穿院,踏橋拾階,他漠然路過那些麻木的家眷,絕奔逃而被扣押在地的仆役,哭嚎的孩……
廊院一地狼藉,文墨書冊扔湖池,貴被劫掠搜盡,珍惜養護的花草折斷了腰肢,被一腳腳狠狠踐踏泥里。
謝清晏停在院中,冷漠著周遭幢幢的影。
這一幕太悉、
只是記憶里的那幅畫卷,又遠比今日更像人間地獄。
那是十五年前了,他也曾趁著火一樣的晨曦馳馬歸京,不顧呼吸里的腥氣。
為他奔死的馬駒吐出白沫,他卻不曾回頭看上一眼,只記得咬碎了牙也要朝那片火跑去,摔倒再爬起,踉蹌行至,卻還是沒能來得及。
滿府哭喊求救,滿目白骨。
哭的被活活踏死,幾步外驍勇善戰的大舅父被來自后的數柄長槍貫,面目猙獰死不瞑目。
年方弱冠的小舅父臨死前仰天怒嘯,如斷爪虎,長劍盲目四揮,淚沾襟,聲音嘶啞如惡鬼哀泣:[謝策…!!你這忘恩負義、喪盡人倫、豬狗不如的畜牲!你謝家人人不得好死——我咒你國祚斷絕、百年必亡啊!!]
然后用抱起過他無數次的那雙手,年揮劍自盡,深見白骨。
隨他之后,一顆顆人頭落地,一雙雙眼睛怒睜。
每個人都死死地瞪著他,從四面八方,從黑暗里,從他行至此的每一步,怨恨,痛苦,猙獰,絕。
直到人的手死死捂住了他的,從后栗著抱住他:
[翊兒——我的翊兒……不要去、會死的,不要去啊……]
染了長穹。
“……”
青天白日,雪地長空。
長立在兵荒馬的安府,謝清晏緩緩合上了眼,又再次睜開。
與耳畔重疊的,來自記憶里久遠未歇的哭喊,終于如水般褪去。
從恨意中平定下的眼眸落低。
穿過月門與遮掩的林木間,他見一道悉的纖細影,匆匆掠過不遠的廊下,朝挽風苑的后院跑去。
尚未褪去的恨意下,謝清晏攥了指骨。他霍然轉,反向而離,只是邁出的停了兩息,他終究轉回,又跟了上去。
——
戚白商正在安府中四尋著安仲雍。
圣上批下的雖是籍沒家產、男丁流放的旨意,道理上不該傷及命,但抄家的巡捕營兵卒們下起手來哪有什麼輕重。
初冬凜風早將安家倒臺的風聞刮了上京城中家家戶戶,從前安家在朝野黨羽眾多,如今甚至沒人敢出來為他們說上一句話——自然就更不會有人在意抄家時,是否有偶然失手犯下的幾條人命了。
說到底,如今安家里再沒什麼貴人眷,人人逃不過罪籍。
戚白商念二舅父在行宮那日為了免落人口舌,自甘頂了惡名,圣駕面前舉數安家樁樁罪行。
知今日禍,來路上便央兄長,籍沒安家家產時,給安仲雍那座書齋小院獨留一方清靜,免得傷及本就抱病多年的安仲雍。
沒曾想,方才戚世接到底下京兆府的兵回報——安仲雍竟不在他的院中!
戚世安排人去府中尋了,可那些人辨不得這位極離府的安家次子模樣,尋起來如大海撈針,戚白商等不及,親自尋到挽風苑后院附近。
戚世奉旨督辦,自然不能擅離,勸阻不得,便了兩名京兆府的校尉跟在旁護著。
只是此時府中兵荒馬,過某道院落廊下,和一群被羈押的罪奴們錯間,那兩名校尉也和戚白商走散了。
“娘——”
戚白商正返去尋那二人,便被隔壁院子一聲孩哭聲絆住了腳。
遲疑了下,朝聲音來走去。
那方院子似是仆役住,廊外,一名孩嚎著被從一個婦人旁拽離。
地上那個跪著的布打扮的仆婦爭奪不過,嚇得淚流滿面地用力叩頭:“爺,他是我的兒!是主子容我娘倆住在府里,他當真不是安家男丁啊爺……”
“廢話,是不是帶走就知道了!”
拉住男的兵啐了一口,用力拽拖起孩,就要往院外走。
婦人急了,忙不管不顧地向前一撲,抱住了兵的腳:“爺!爺您放了我們娘倆吧——”
“呸!什麼腌臜東西!”
那名兵拉了兩下,沒能開,惱怒,竟是一腳狠狠踹開了那婦人:“再耽誤辦差,我剁了你腦袋!”
“娘…!!”
男哭嚎聲頓時更加凄厲了。
折廊后,戚白商面不忍,蹙眉便要踏出山墻后。
只是那一步尚未落在實。
戚白商腰間驀地一,竟是被什麼人挾起楚楚纖腰拉回墻后,扣在了那道山墻外糙不平的巖壁上。
就連險些出口的驚呼都被對方預料,抵著修長微冷的指骨,覆回口中。
戚白商驚惱仰眸,烏瞳輕。
——謝清晏!
竟真是他?!
“什麼眼神,”謝清晏低了低,聲線輕啞疏慵,“見鬼了?”
戚白商不由地蹙眉。
……此刻在面前低的謝清晏,無論抑的眼神還是詭譎的語氣,都戚白商切實地有種見了無間鬼魅的危險。
誰又招惹謝清晏這瘋狗了?
戚白商眼下卻沒心思計較這些,此間,山墻后的廊外,爭執哭嚎之聲愈發高了些。
偏過臉,避開了謝清晏的手:“煩請謝公放開我。”
“我當你對安家多無私,這便心疼了?”
謝清晏不但未從,反而將腰錮得更,“安家害死的那些命,連哭掙扎的機會都不曾有……今日之事,不過是他們罪有應得。”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https://.52shuku.net/yanqing/05_b/bjZs4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940 章

農門長嫂富甲天下
倒霉了一輩子,最終慘死的沈見晚一朝重生回到沈家一貧如洗的時候,眼看要斷頓,清河村的好事者都等著看沈家一窩老弱病殘過不了冬呢。 她一點都不慌,手握靈醫空間,和超級牛逼的兌換系統。 開荒,改良種子,種高產糧食,買田地,種藥材,做美食,發明她們大和朝見所未見的新東西……原打算歲月靜好的她一不小心就富甲天下了。 這還不算,空間里的兌換系統竟還能兌換上至修仙界的靈丹,下到未來時空的科技…… 沈見晚表示這樣子下去自己能上天。 這不好事者們等著等著,全村最窮,最破的沈家它竟突然就富了起來,而且還越來越顯赫。這事不對呀! ———— 沈見晚表示這輩子她一定彌補前世所有的遺憾,改變那些對她好的人的悲劇,至于那些算計她的讓他們悔不當初! 還有,那個他,那個把她撿回來養大最后又為她丟了性命的那個他,她今生必定不再錯過…… 但誰能告訴她,重生回來的前一天她才剛拒絕了他的親事怎么辦?要不干脆就不要臉了吧。 沈見晚故意停下等著后面的人撞上來:啊!沈戰哥哥,你又撞我心上了! 沈戰:嗯。 ———— 世間萬千,窮盡所有,他愿護阿晚一生平平安安,喜樂無憂。
181.6萬字8.33 135289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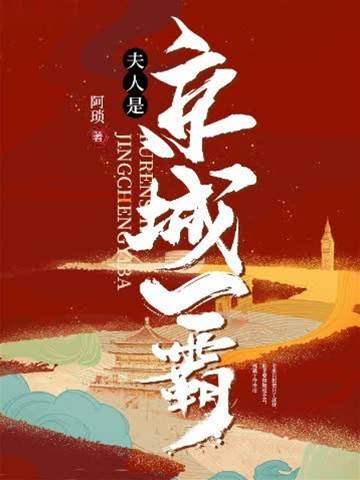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109 章

偏執太子的掌心嬌
宣威將軍嫡女慕時漪玉骨冰肌,傾城絕色,被譽為大燕國最嬌豔的牡丹花。 當年及笄禮上,驚鴻一瞥,令無數少年郎君為之折腰。 後下嫁輔國公世子,方晏儒為妻。 成婚三年,方晏儒從未踏進她房中半步。 卻從府外領回一女人,對外宣稱同窗遺孤,代為照拂。 慕時漪冷眼瞧著,漫不經心掏出婚前就準備好的和離書,丟給他。 「要嘛和離,要嘛你死。」「自己選。」方晏儒只覺荒謬:「離了我,你覺得如今還有世家郎君願聘你為正妻?」多年後,上元宮宴。 已經成為輔國公的方晏儒,跪在階前,看著坐在金殿最上方,頭戴皇后鳳冠,美艷不可方物的前妻。 她被萬人敬仰的天子捧在心尖,視若珍寶。
33.7萬字8.18 14518 -
完結942 章

重生我嫁給了未婚夫的死對頭
86.7萬字8 280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