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春靨》 第572章 求你
阮凝玉沒想到他會問出這個話題來。
很想對他說,這又有什麼關系?
他前世,不便是放手了,送出嫁麼?謝府也只有他這麼一位兄長來東宮,喝了的喜酒。
前世可以,為何今生就不能了?
何況他們之間還各自橫著一個丈夫,一個妻子。
他們前世都各自與另一半締結了夫妻,有過夫妻之!兩人心中都曾有過一個過的人,這讓阮凝玉如何越得過這樣的事實,讓跟他在一起?
這太荒誕了。
這份隔閡,就像道無形的墻,豎在他們之間,怎麼也繞不開。
阮凝玉偏過臉,“這樣不好的嗎?”
想到了前世的事,竟讓沉默了下去。
一想到明明被他過,還要另嫁郎君,謝凌竟咳嗽起來。
男人修長的影撐在旁邊的博古架。
他邊帶,眼里裹挾著山雨來的沉重,謝凌艱難地道:“可我沒辦法親眼看著你冠霞帔,嫁給旁人。”
阮凝玉震驚地看了過來。
“年前奉命去南京,我原是抱著念想的,我想,江南煙水,日子長了,總能把你從心里磨淡些。”
他自嘲地勾了勾角,眼底卻漫上一層紅,“可我錯了。”
“我做不到。”
“便是拼盡所有,我也做不到。”
謝凌間滾過一聲抑的哽咽,“我試過把你的東西放進箱籠里,把你送我的東西鎖進了屜深,我甚至遣人換了院里那株海棠樹,換上了尋常的松柏。我想讓這里干干凈凈,再沒有半分你的痕跡。可只要閉上眼,就全是你的影子。”
阮凝玉這個名字,在每個午夜夢回時,硌得他心臟生疼。
謝凌間涌上的腥甜被他生生咽下,聲音啞得沉重,“那天知道你會去花朝宴相看,我在書房枯坐了整夜,直到天亮,我才想明白,那些道理我都懂,什麼全,什麼放手。”
Advertisement
謝凌微笑:“可真要眼睜睜看著你了別家婦,我這條命,怕是熬不過那個時候。”
阮凝玉抖了,臉蛋染上了幾分薄怒,“你在威脅我?!”
謝凌沒說話。
阮凝玉心里不停地懼怕,謝凌的口吻不像是在開玩笑,他臉上那樣偏執冷漠的神,一看就是認真的!他絕不是嚇唬的而已!
他心中的偏執瘋狂得如同魔鬼,能將他給吞沒,拽地獄。
開始努力回想著前世,是不是有錯過的,藏在時角落里的被所忽略的。
前世謝凌的,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時候他自從了閣后,便很有一天不在皇宮的。
可分明記得他邊經常跟著一個道士,謝凌時常口服丹藥,那時的以為謝凌也是長生不老,于是從未放在心上。
自從當了太子妃后,便與謝府和謝凌一刀了斷,他每回寄過來的家書,一封都沒有拆開來看。他信上的每一句問候,每一句關心,都以為他虛偽至極。
可現在想來,他口服的那些或許并不是什麼丹藥,而是他吊著他命的藥!他為了掩人耳目,怕仇家發現他的心疾。
阮凝玉說不出來話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竟覺得謝凌有幾分可憐。
“你別這樣……”
阮凝玉哽塞,蒼白了,“你就不怕死嗎?”
謝凌卻走過來,角的鮮已被他去,他走過來,強行將五指的指,他垂下眼簾,“我不怕,你怕了?”
那是他的命,怕什麼?
阮凝玉覺得他瘋了。
他竟連死都不怕。
眼眸里出了幾分恐懼。
他這樣瘋,這樣魔,以至于不敢反抗掉他的手。
謝凌能得出來,的手指在自己的掌心里細微地著。
謝凌卻如同看不見般,而是手指往下,來到了的手腕,他著上面細膩如同綢緞的。
“這般瑩潤的手腕,怎好空著?”
他指腹帶著薄繭,每次,都激得在栗,如同電流經過。
說完,他便取出了一只手鐲,霸道偏執地給的皓腕戴上。
阮凝玉定睛一看,才知竟是那只當賣掉的白玉梅蝶鐲。
謝凌指尖推著玉鐲往上,直到穩穩停在腕間,與皓白相映,竟生出種驚心魄的。
戴上后,阮凝玉急忙將自己的手了回去,謝凌的手撲了個空。
他如同沒發生過,指尖微頓,將手收回。
謝凌微微瞇眼,“凝凝,聽話些,不要再惹我生氣了。不要再把我送你的東西,拿去換那些俗。”
他不想每次都這樣被這般堵心了,他真的很痛苦,他的心意被踐踏,的輕賤,他的也承不了這些沉重的緒。
他的聲音很輕,卻帶著別樣的威脅。
謝凌垂眼,見仍滿臉抗拒,于是便咳嗽一聲,不顧抵的心,繼續與十指相扣。
阮凝玉依舊偏過臉。
謝凌卻握住的下,讓看向自己。
阮凝玉瞪著他。
謝凌看了許久,蒼白卻不自知,苦笑一聲,“你不接我,可是還在意著我當初我冷眼旁觀,害你被驗之事?”
阮凝玉卻輕笑一聲,“冷眼旁觀?謝凌,你倒是說得輕巧!”
“那天們我的服,把我像牲口一樣對我驗的時候,你就站在外面站著!看著!”
“謝凌,知道那些人里的污言穢語有多難聽嗎?我在那里,像個破布娃娃一樣任人擺弄,每一次抬頭,都能看見你的影子站在廊下,連眉頭都沒皺一下!”
“現在倒來問我在不在意?謝凌,你怎麼敢?”
謝凌眸中原本升起來的一點希冀,瞬間破碎了。
眼看著謝凌驟然失,臉一點一點變蒼白,阮凝玉心中痛快,“謝凌,當初你旁觀時,可有想過你也會有這麼一天?”
“可有想過,你有一日竟會對我求而不得!像只喪家之犬對我搖尾乞憐!”
轟隆一聲,天邊滾過雷聲,雨下得更大了,仿佛整個天地都要在今夜被洗刷,被淹沒。
親眼見到,這位過去人人敬重的圣人君子,清雅又絕塵。可他竟被自己的三言兩語打擊得無完,這位高嶺之花,圣潔溫雅的臉一點一點地灰敗下去,眼里出絕。
他的示,辱。他的尊嚴,踐踏。
阮凝玉深吸一口氣,“不過這件事,我早就跟你說過了、說開了,沒什麼好計較的。你有你的難,當初也是你向老太太和族老們求,我才不至于被趕出謝府,這件事,我們已經兩清。”
“如果你只是我的兄長,這件事不會為我們的隔閡,可你偏要貪婪要更多,偏要喜歡我。”
“這不一樣,你知道嗎謝凌?當我的兄長,和喜歡我,這兩者在這件事上是不一樣的。”
“有這樣一件事橫亙在我們之間,你早就沒了喜歡我的資格,謝凌,你不配。”
謝凌無力一笑,“所以,怪來怪去,你還是怪我。”
哪里知道,他冷眼旁觀被強行驗的那日,早已了剜在他心頭的毒刺,日夜流膿淌。那是他這輩子最后悔的一件事,不敢再提,更不敢再去自揭傷疤。
沒說話,而是看向了旁邊的花瓶。
或許吧。
恨極,厭惡極了他前世對許清瑤那樣傾盡一切的寵,重生回來驗時他的漠視,更加重了對他的怨意。
謝凌:“怎麼樣,你才肯原諒我?”
阮凝玉甚至覺得,此刻的謝凌卑微到了極致。
謝凌瘋狂道:“當時在場的,過你,經過手的嬤嬤,我全都殺了!至于三嬸,只要你想,你想如何置便如何置。可好?”
阮凝玉怔住,卻是嘲諷地笑。
“殺無辜人的命來抵掉你的過失?謝凌,你從前何等溫厚,什麼時候,你竟變了讓自己最為不恥的人?你真是個瘋子!”
他為染了滿手腥,為瘋魔至此,可呢?不僅視若無睹,還要用最刻薄的話,將他這焚心蝕骨的瘋狂,碾泥,踩在腳下,罵他是個瘋子。
謝凌白了臉。
阮凝玉:“你覺得,在這件事上,還能什麼能夠彌補的嗎?”
他忽然聲音平靜了下去。
“如果我把我的命給你呢?”
阮凝玉愣住。
這才發現,謝凌的臉白得可怕,幾乎沒有一點!
謝凌則解下了腰間的佩囊,掏出了里頭的一小藥瓶,不顧掙扎,目冰冷,強行將這葫蘆形狀的藥瓶塞進了的手里。
謝凌:“我患有心疾,里頭乃我救命藥,此屋只你我二人,只要你想,不開心也好,怨我,恨我也罷,藥給你,我的命由你置。”
無論如何掙扎,謝凌還是死死地鉗住的手。
阮凝玉變了臉:“謝凌,你不要命了?!你拿你的命做賭!你是一心想尋死麼?!”
氣得發抖,又很恐懼。
“你可知,你這樣做是害了我!若是你死在了這里,我怎麼出去跟別人代?!”
知道他瘋,卻沒想到他能瘋這樣。
為了得到,連旁人的生死都不顧了麼!
謝凌抿一條筆直的線。
他捂住心口,安,對溫一笑,“放心,這藥便是不吃,我也死不了的。”
“醫說了,我心疾發作,不吃藥雖不至于傷及命,但每延遲一刻鐘吃這藥,便會短我幾年壽命。”
阮凝玉睜大瞳孔。
謝凌:“如此,你可放心了。”
“接下來的時辰,都不會有人進來。”
阮凝玉不小心手松開了,藥瓶哐當一聲掉落在地上,滾落在角落里。
而謝凌命堪憂,卻如同沒見到那白瓷藥瓶般,而是滿臉冷汗,靠在墻上著氣。
阮凝玉抖著聲音:“瘋子!”
此刻發現謝凌的臉白得嚇人,嚇得要去推開門,喊人進來。
可沒想到,大門竟被人在外頭鎖住。
謝凌抑制著痛苦,合眼,“沒用的,不會有人過來的。”
阮凝玉又去搬凳子來,企圖撞開,見真的沒法砸開這扇門,阮凝玉放棄了。
轉過,又怕又怒,眼眶冒出點兒淚花來:“你明明說,不會拿你的病來威脅我的!你食言!你撒謊!”
謝凌眼前陣陣發黑,可他卻覺得沒什麼大不了,最多不過是暈倒了,心力損,短了幾年壽命罷了。
謝凌此刻哀莫大于心死,一點求生的都沒有。他起眼皮,目寒厲,他看著眩暈場景下那張得不可方的臉龐,盯了許久,最后又合上眼,聲音虛弱:“我不過是拿我的壽命,來賭你……對我有沒有一點心而已。”
“如此,也值了。”
阮凝玉流了眼淚。
是低估了謝凌的無恥。
他本沒有給留退路,所有出口都被他堵死了,非著做出個選擇。
哦,不,他選擇也只給留了一個。
沒有別的選項。
此,要麼生,要麼滅。
阮凝玉:“為什麼一定要是我呢?天底下的人這麼多,容貌比我的,才華品比我勝的,多的是。”
謝凌:“我謝凌,從來沒有什麼得不到的東西。”
“不是你,旁人縱有萬千不同,在我眼里,又有什麼區別?”
不是,誰都一樣。
阮凝玉覺自己的心臟跳得很快,又震又麻。
他的咳嗽越來越嚴重。
謝凌從懷里取出塊帕子,須臾,上面便落下了朵刺眼紅梅。
謝凌雙目微紅,抬眼,向招手,“過來。”
阮凝玉不敢拿他的命開玩笑,聞言連忙跑了過來,剛想扶住他。
誰知謝凌竟握住了纖細的胳膊,憑著本能將的子往懷里一按,像是要將進自己骨里,連帶著腔里起伏的息都燙在頸窩,沉沉呼吸,“……讓我靠一下。”
阮凝玉在他懷里細細抖。
謝凌見狀,雙眉淡漠,手掌拍著薄薄的背,“不過是幾年壽命,你在怕什麼?”
阮凝玉不語,怎能不怕?前世死得早,不知道他究竟活到了多久。他這樣的心疾,本就注定他極有可能不是長壽的命,若再了幾年壽,他還能活多年?
阮凝玉很怕,很怕他真的就這樣死了。
謝凌自然而然地將下頜靠在了的肩上。
“凝凝。”
他眼前發黑的同時,耳邊出現了嗡鳴,他能到自己的心臟跳得非常人之快,快到他快眩暈過去,但謝凌此刻聞著輕的發香,心安地合了眼,竟覺得若命結束在這一刻,也很好,他扯了:“我賭你舍不得對我這般心狠。”
“若我僥幸賭贏了,便求你給我與慕容深、沈景鈺同等的機會。”
他要的并不多,與沈景鈺、慕容深那份一樣便好。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小公主又幫母妃爭寵了
穿書成了宮鬥劇本里的砲灰小公主,娘親是個痴傻美人,快被打入冷宮。無妨!她一身出神入化的醫術,還精通音律編曲,有的是法子幫她爭寵,助她晉升妃嬪。能嚇哭家中庶妹的李臨淮,第一次送小公主回宮,覺得自己長得太嚇人嚇壞了小公主。後來才知道看著人畜無害的小公主,擅長下毒挖坑玩蠱,還能迷惑人心。待嫁及笄之時,皇兄們個個忙著替她攢嫁妝,還揚言誰欺負了皇妹要打上門。大將軍李臨淮:“是小公主,她…覬覦臣的盛世美顏……”
105.9萬字8 170382 -
完結729 章
東風第一枝
葬身火場的七皇子殿下,驚現冷宮隔壁。殿下光風霽月清雋出塵,唯一美中不足,患有眼疾。趙茯苓同情病患(惦記銀子),每日爬墻給他送東西。從新鮮瓜果蔬菜,到絕世孤本兵器,最后把自己送到了對方懷里。趙茯苓:“……”皇嫂和臣弟?嘶,帶勁!-【春風所被,第一枝頭,她在他心頭早已綻放。】-(注: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97.7萬字8 8970 -
完結467 章

全家帶著千億物資去逃荒
【全家穿越、空間萌寵、逃荒、種田】 蘇以安撓著雞窩頭看著面前冰山臉少年,心里一頓MMP。 全家集體穿越,本以為是個大反派制霸全村的勵志故事,這咋一不小心還成了團寵呢? 爹爹上山打獵下河摸魚,他就想老婆孩子熱炕頭,一不小心還成了人人敬仰的大儒呢。 娘親力大無窮種田小能手,就想手撕極品順便撕逼調劑生活,這咋還走上了致富帶頭人的道路呢? 成為七歲的小女娃,蘇以安覺得上輩子太拼這輩子就想躺贏,可這畫風突變成了女首富是鬧哪樣? 看著自家變成了四歲小娃的弟弟,蘇以安拍拍他的頭:弟啊,咱姐弟這輩子就安心做個富二代可好? 某萌娃一把推開她:走開,別耽誤我當神童! 蘇以安:這日子真是沒發過了! 母胎單身三十年,蘇以安磨牙,這輩子必須把那些虧欠我的愛情都補回來,嗯,先從一朵小白蓮做起:小哥哥,你看那山那水多美。 某冷面小哥哥:嗯乖了,待你長發及腰,我把這天下最美的少年郎給你搶來做夫君可好? 蘇以安:這小哥哥怕不是有毒吧!
87.4萬字8 47099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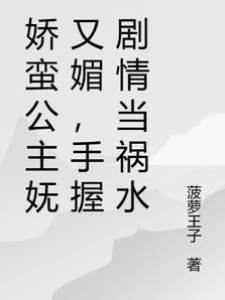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57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