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女官秦鳳藥,從棄兒到權利巔》 第1158章 等待結局
這一句話,將李瑞嚇得魂不守舍。
他不知自己是怎麽回的王府。
深夜寂寂,他獨守窗前,想起從前知意陪在邊的時候。
窗前院中有棵櫻桃樹。
春天結了櫻桃分外麗,特別是傍晚時分,夕的剛好落在樹上。
映著紅的果實,樹和果實閃閃發。
暮瀲灩,春風悠長,若在,定是人笑意嫣然。
可惜,這王府卻是沒住進來一天。
李瑞眼眶的。
如果還在,一切如初,會是什麽樣?
現在化為荒野裏的一抔黃土,他孤獨守著一座豪華的府宅。
這裏仆從眾多,白日喧囂熱鬧。
深晚卻如一座孤墳。
唉,像孤墳的不是王府,是他的心。
心裏仿佛有一個空,怎麽也填不滿。
遇到,才讓他的靈魂有了溫度。
知意對他的意義和份量比他想的還要多。
走了,連從前相不愉快的部分,在回憶中也變得有了意義。
若是不會被父皇發現,現在殺秦藥還來得及嗎?
……
第二天他一早進宮,先去了未央宮。
容妃還沒起,皇上回京沒後宮半步,連貴妃也沒召見。
皇後的死訊並未傳開,大家隻傳皇上再次圈了皇後。
太子被關掖庭雖然都已傳遍,卻人人都諱莫如深,無人敢提。
宮裏彌漫著張的氣氛,全無打了勝仗的喜悅。
Advertisement
容妃前段時間因沒了皇上消息,日日憂心,常夜不能眠。
隻是擔憂的是徐乾。
直到皇上大捷消息傳來,且沒有其他噩耗。
才放心閉眼,這一睡,日日都到日上三竿才起來。
李瑞不讓醒,自己走進寢宮。
坐在床邊看著床上的人。
他的母親,睡著時已顯出了老態。
皮隻有細細紋路,若上了妝依舊亮麗。
隻是睡著時,人是沒辦法修飾自己的。
已經鬆弛的皮與黯淡無的皮都表明了年齡。
李瑞看著,想著自己從小與為伴。
人都說見麵三分,他日日見,如今心裏為何怨比多得多。
詛咒與恐嚇般的責備,和事後抱著他痛哭。
那些半瘋癲的日子,他被困在邊,無知無覺。
等他知道別人不是這麽過日子,等他醒悟時,已經晚了。
他仿佛被一個影籠住,那片影原先隻有掌大。
現在,已經將他整個人籠在其中。
是他主走影中的。
他放任心中的惡念,放任,放任自己想傷害別人的暗想法。
後悔嗎?
不,他一點也不後悔。
容妃緩緩睜開眼睛,恍惚看到一個男子坐在床前。
有些分不清時間,好似自己還待字閨中。
還有許多的未來,有許多路可以選。
“徐乾?”半夢半醒之間出心底埋藏最深的名字——
日夜思念的男子。
突然,清醒過來,一下坐起,盯著守在床邊的兒子。
“瑞兒,你怎麽在這兒?什麽時辰了?”
“我來瞧瞧母親。”他沒提方才母親喊了其他男人的名字。
他悉了母親的。
也明白這麽多年為什麽過得歇斯底裏。
可仍然把同樣的悲劇加諸於他的上。
明知道失去所是什麽滋味,在拆散他時,毫不留。
“出了什麽事?”容妃從未見過兒子這個樣子,顧不得洗漱,慌張地問。
“要是出了事,母親又當如何?”
容妃理了下額前碎發,“母親隻有你,你若出事,我豁出命也要幫你。”
“太子出事,不知皇後要難什麽樣。”
“都是做娘的,唉。”
總是這樣,他又傷害他。
讓他想恨又不能徹底恨下去。
與恨之間的拉扯,讓他割裂又痛苦。
“什麽錯誤都可以被原諒?”
“我想殺了李嘉。差點就功了。”他平靜地訴說自己有多恨李嘉。
恨他可以活得那麽從容,恨他有那麽好、那麽寬容的母親。
他的恨意那麽多,說起來滔滔不絕。
小時候因為多病被罵“病秧子”,每發病便惶惶不可終日。
因為他一病,容妃便自責沒照顧好,又怕他就此死掉。
近乎瘋癲般罵兒子也罵自己。
有時還會做出更瘋狂的舉。
扇自己耳、用杯子碎片劃傷自己。
是瘋的。
長大後的李瑞才意識到。
可憐他跟隨著母親居於深宮,求救都沒人聽到。
他是兄弟中最喜歡去書房念書的。
讀書辛苦與麵對一個瘋狂的母親相比,本不算苦。
那裏安全又熱鬧。
隻要不麵對母親,就不必提心吊膽什麽時候發作。
就如現在,看著容妃的眼神,李瑞仍然提心吊膽,是不是馬上要跳起來狂罵自己。
可隻是瞠目結舌瞧著他,像沒聽懂他在說什麽。
於是他又慢悠悠補充說,“被他發現了。”
“李嘉沒那麽心,要是拿到你的證據,必定要上告你父皇。”
出乎意料,容妃沒責怪他,反而為他分析事嚴重。
“現在沒了李慎,隻餘你和李嘉還有李仁,太子之位隻在你們中間。”
“你不必他,太子位也最有可能傳給你。”
“母親聽不懂嗎?我殺他不隻為太子位,我嫉妒他有個寬容的母親,不像你天天責罵我。”
“外祖父也隻會訓斥我。”
“憑什麽都是父皇脈,我活得這樣辛苦。”
他直勾勾盯著容妃,他想看到慌張、疚。
可隻是驚訝,微張著,卻不知說什麽。
好半天,如泄了氣,囁嚅著,“娘親是真心為你好啊,哪有這樣記娘的仇的?”
“你對李嘉做了什麽?若被發現可以都推到母親上。”
容妃去拉李瑞的手,他躲開了,瞧著母親的眼睛,是的,直到現在,仍然不覺得自己做錯了。
他笑起來,這一切多麽荒誕。
他沒了心之人,害親兄弟沒害還暴了。
“兒子,不管你做了什麽,娘都不怪你。”
容妃終於意識到兒子做法會引來什麽樣的後果。
“你快說說,我們一起想個對策,皇上不知道便罷了,知道的話總得有個說法呀。”
好像剛從夢中清醒,急匆匆踩在繡鞋上,李瑞將鞋一踢,容妃踩在冰涼的青磚地上,驚愕地看著兒子。
“容妃娘娘,你也是有過心上人的。”
“你該懂得失去人的痛苦。”
“為什麽要把這痛苦加在孩兒上?兒子百思不得其解。”
容妃張大,半天才道,“你在說什麽?娘隻你父皇一人。”
“別裝了,你一直著徐小將軍不是嗎?做夢都喊他的名字。”
“這些日子宮說你擔心皇上夜不寐,其實你擔心的是徐乾戰死,畢竟北狄不比其他異族,十分善戰。”
他垂下頭,容妃看不清他的表,以為他在冷笑。
“好希他們都死在那裏,沒有回來啊。”
他的低語猶如惡魔的歎息在常容芳耳邊炸開。
看著李瑞,仿佛從沒認識過這個自己一手帶大的孩子。
“那是你的父親,大周的皇帝,你希他……死?”
“是他們,都去死。”
李瑞抬頭,臉上出又哭又笑的表,“我也好想死,讓你好好嚐嚐邊空無一人的痛苦。”
容妃流下淚,“娘到底哪裏沒做好?”
“哪裏都不好,我恨你,恨外祖,如果我能早點意識到我在恨你們,也許就不會走到今天這步。”
恨的外麵包著的糖,才讓人分不清楚。
他起,看著容妃因為難過蜷在床上的模樣,心裏並沒有想象中的暢快。
他對母親仍抱有,傷了,自己也痛。
李瑞踉踉蹌蹌走出未央宮,這些日子皇上免了皇子早朝。
他無可去。
猜你喜歡
-
完結1250 章

法醫王妃:我給王爺養包子
坊間傳聞,攝政王他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蘇七不過是從亂葬崗“詐屍”後,誤惹了他,從此他兒子天天喊著她做孃親。 她憑藉一把柳葉刀,查案驗屍,混得風聲水起,惹來爛桃花不斷。 他打翻醋罈子,當街把她堵住,霸道開口:“不準對彆的男人笑,兒子也不行!”
216.9萬字8.18 52483 -
完結2007 章

神醫狂妃:娘親你馬甲又掉了!
大齊國的人都以為瑾王妃只是個寡婦,瑾王府也任人可欺。可有一天,他們發現——神醫門的門主喊她老祖宗。天下第一的醫館是她開的。遍布全世界的酒樓也是她的。讓各國皇帝都畏懼的勢力是她的外祖家。就連傳說中身亡的夜瑾居然都回來了,更是將她疼之入骨,寵入…
181.2萬字8 94733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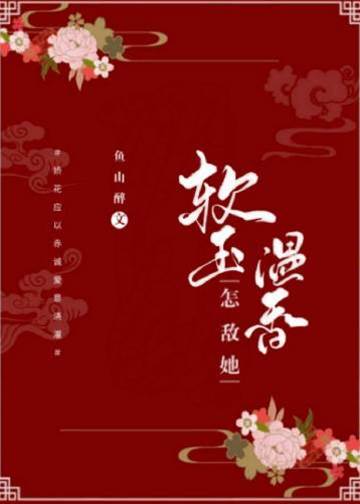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1801 -
連載2178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4.1萬字8.33 4778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