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 第45頁
司機早已下車,拉開后排車門,彎腰候著。
爹地臨上車前又看了蔣寶緹一眼。
蔣寶緹知道,這或許是爹地在國最后一次見了。接下來他要去忙他自己的正事。
蔣寶珠說的一點錯也沒有。
爹地的確只是順便看一眼。
覺得自己好像釋懷了,并接自己不被的事實。
父親有那麼多孩子,只是其中一個而已。可能他對的確是有父存在的。
但太了,分量太輕。輕到本填補不了蔣寶緹的所需。
是個貪心的人,想擁有很多的,獨一無二的。
那輛黑的奧迪rs7開走了,蔣寶緹頭垂下去,盯著路邊那顆被路人踢來踢去的石子看了很久。
路人好像都很嫌棄它,嫌它礙眼,嫌它硌腳。
它的存在是多余的。
的確,它不該出現在這里。那麼它應該出現在哪呢,它的真實歸屬又是哪呢。
它生來就沒有手腳,它不可能是自愿出現在這里的。
可為什麼對方將它帶到并不屬于它的世界,卻還將它棄,棄之不顧。
或許只有心思敏的人才適合搞藝,也或許是搞藝的大多都心思敏。
Advertisement
蔣寶緹最終還是蹲下,將那顆和自己擁有相同命運的石頭撿了起來。
給了它一個歸宿。
可石頭都有歸宿,那的歸宿又在哪里呢?
港島的那個家?那是的家嗎?
蔣寶緹默不作聲地將石頭放進了外套口袋,轉離開之時,這才發覺側那輛柯尼塞格的車窗不知是何時降下來的。
駕駛座上,男人的半張臉都在黑暗之中,黑西覆蓋下的長疊,而他的手,則松弛隨意地搭放在膝蓋上。每一條筋脈都在往外滲男的魅力。
蔣寶緹看不清他的臉,但一眼就認出了那是宗鈞行。
到了一言不發下暗流涌的低氣。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從他上到這麼明顯的緒外放。
他有意讓知道自己在生氣。
“Hop in(上車)”他沒說別的,只是淡聲讓上車。
蔣寶緹不敢多說什麼,聽話地走到副駕駛,拉開車門坐進去。
這還是第一次見到宗鈞行親自開車。
都說通過一個人開車時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的大致格。
蔣寶緹想,這番話的確很有道理。
宗鈞行開車很穩,不會急剎。哪怕被人惡意別道,他也無于衷。
蔣寶緹幾乎從他的臉上看不出任何緒波。
試圖猜測他當下的緒,也無從猜起。
一路上宗鈞行都沒有開口說話,蔣寶緹自然也不敢擅自開口。
回到家后,晚飯宗鈞行沒有吃。
蔣寶緹獨自一個人在飯廳用完晚飯。
因為貧,所以一日三餐都得按照營養師搭配的食譜吃完。
分量和所需的營養元素都是專門調配好的,以的飯量,正常況下是可以吃完的。
除非不適,或是沒有胃口。
當然了,如果哪天有剩下,Saya阿姨會單獨和宗鈞行說明。
所以蔣寶緹連減的念頭都不能。
即使現在的重甚至需要增。
用完晚飯后,蔣寶緹再三猶豫,還是去了書房。
里面很安靜,宗鈞行回來之后便將自己關在里面理公務。
蔣寶緹進去的時候他正在打電話。站在落地玻璃前,單手抄兜,背影偉岸高大。
服還沒換,仍舊是白日里的那。
無比正式的高定西裝,此時了外套,只有馬甲、襯衫和領帶。
一如既往的儒雅矜貴。
“這種事如果也需要來問我,那麼你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他低頭點煙,平淡冷靜的語氣,帶著令人畏懼的震懾力。
蔣寶緹想,他的確是個非常合格的掌控者。
不管在私人上,還是工作上,他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dom、master。
是掌控者,也是主宰者。
沒有人敢挑戰他的權勢和威。
大概是聽見了開門聲,宗鈞行并沒有回頭。
整個家里能在未經他允許的前提下就擅自進到他的書房里的人,也只有蔣寶緹了。
所以他提前結束了通話。
蔣寶緹看著他高大拔的背影,西裝廓朗,散發著穩重的氣質。
蔣寶緹聞到似有若無的煙味,從他那里傳來的。
停在原地,不知現在是該主上前還是該離開。
害怕怒的宗鈞行,因為未知。
他很生氣,喜怒不形于,所以蔣寶緹并不清楚他怒后的樣子。
但同時……
事先聲明,絕對不是變態。
雖然略微有那麼一點點點點點點的期待。的潛意識里似乎“被懲罰”
當然了,這些是發生在知道宗鈞行并不會真的傷害的前提下。
或許他對其他人心狠,可以毫不猶豫地扣下扳機。
等等……
蔣寶緹突然想到了之前在院子里看到的那一幕。
Gray的下場……
先是看了眼書桌上方的屜。記得宗鈞行之前將手槍放在了里面。
是的,沒錯,就是那把打穿Gray左右肩膀的手槍。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28 章

耳朵說它想認識你
蒲桃聽見了一個讓她陷入熱戀的聲音,她夜不能寐,第二天,她偷偷私信聲音的主人:騷擾你並非我本意,是耳朵說它想認識你。-程宿遇見了一個膽大包天的姑娘,死乞白賴逼他交出微信就算了,還要他每天跟她語音說晚安。後來他想,賣聲賣了這麼久,不當她男朋友豈不是很虧。一天睡前,他說:“我不想被白嫖了。”姑娘嚇得連滾帶爬,翌日去他直播間送了大把禮物。他報出她ID:“你知道我說的不是這個。”男主業餘CV,非商配大佬,寫著玩;女追男,小甜餅,緣更,不V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耳朵說它想認識你》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臉書和推特裡的朋友推薦哦!
6.6萬字8 5275 -
完結103 章

穿成大佬的聯姻對象
執歡穿書了,穿成了替逃婚女主嫁給豪門大佬的女配,文中女配一結婚,就經歷綁架、仇殺一系列的慘事,最后還被大佬的追求者殺掉了 執歡不想這麼慘,所以她先女主一步逃了,逃走后救了一個受重傷的男人,男人身高腿長、英俊又有錢,同居一段時間后,她一個沒把持住… 一夜之后,她無意發現男人的真實身份,就是自己的聯姻對象—— 男人:結婚吧 執歡:不了吧,其實我就是個不走心的渣女 男人:? 男人掉馬后,執歡苦逼的溜走,五個月后喪眉搭眼的頂著肚子回到家,結果第二天男人就上門逼婚了 父母:歡歡現在懷孕了,恐怕不適合嫁人… 男人表情陰晴不定:沒事,反正我是不走心的渣男 執歡:…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努力逃婚最后卻懷了結婚對象崽崽、兜兜轉轉還是嫁給他’的故事,沙雕小甜餅 外表清純實則沙雕女主VS非典型霸總男主
30.1萬字8 15224 -
完結147 章

鹿生
很多人說見過愛情,林鹿說她隻見過性——食色,性也。
28.9萬字8 9248 -
完結599 章

離職后我被前上司痛哭糾纏
她是他的特別助理,跟了他整整七年,他卻一把牌直接將她輸給了別人。藍星若也不是吃素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她一封辭呈丟下,瀟灑離開。坐擁一億粉絲的她,富二代和世界冠軍全都過來獻殷勤,全球各大品牌爭先要和她合作。可盛景屹卻發現自己整個世界都不好了。“回來吧,年薪一個億。”藍星若莞爾一笑,“盛總,您是要和我合作嗎?我的檔期已經安排在了一個月后,咱們這關系,你沒資格插隊。”某直播間里。“想要我身后這個男人?三,二,一,給我上鏈接!”
109.3萬字5 40916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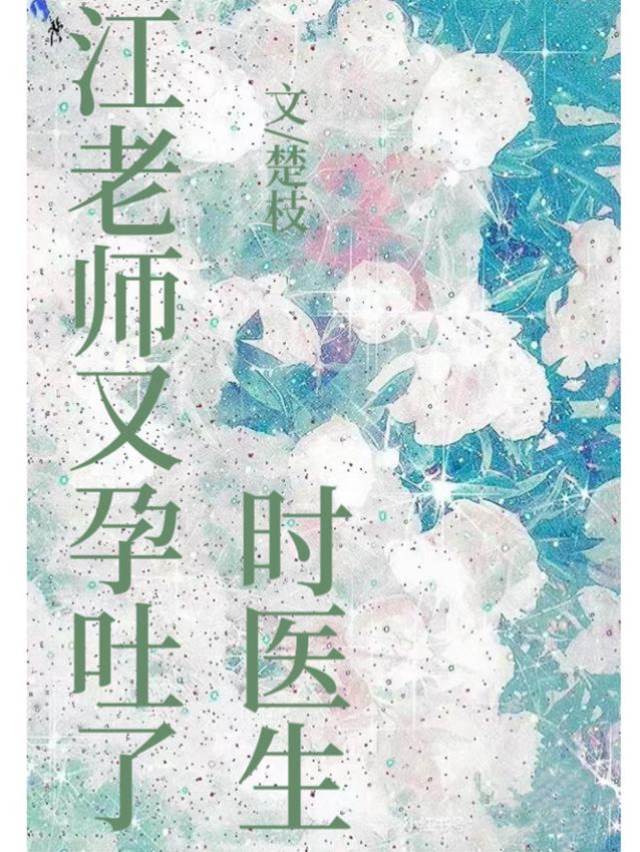
時醫生,江老師又孕吐了
【雙初戀:意外懷孕 先婚後愛 暗戀 甜寵 治愈】男主:高冷 控製欲 占有欲 禁欲撩人的醫生女主:純欲嬌軟大美人 內向善良溫暖的老師*被好友背叛設計,江知念意外懷了時曄的孩子,麵對暗戀多年的男神,她原本打算一個人默默承擔一切,結果男神竟然主動跟她求婚!*江知念原以為兩人會是貌合神離的契約夫妻,結果時曄竟然對她越來越好,害她一步一步沉淪其中。“怎麽又哭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根棒棒糖,“吃糖嗎?”“這不是哄小孩的嗎?”“對啊,所以我拿來哄你。”*他們都不是完美的人,缺失的童年,不被接受的少數,讓兩個人彼此治愈。“我……真的能成為一個好爸爸嗎?”江知念抓著他的手,放到自己肚子上:“時曄,你摸摸,寶寶動了。”*堅定的,溫柔的。像夏日晚風,落日餘暉,所有人都見證了它的動人,可這一刻的溫柔繾綣卻隻屬於你。雖然二十歲的時曄沒有聽到,但二十五歲的時曄聽到了。他替他接受了這份遲到的心意。*因為你,從此生活隻有晴天,沒有風雨。我永遠相信你,正如我愛你。*「甜蜜懷孕日常,溫馨生活向,有一點點波動,但是兩個人都長嘴,彼此相信。」「小夫妻從陌生到熟悉,慢慢磨合,彼此相愛,相互治愈,細水長流的故事。」
35萬字8 30977 -
完結20 章

傾其所有去愛你(平裝版)
【霸道總裁+現言甜寵+破鏡重圓】落難千金自立自強,傲嬌總裁甜寵撐腰!【霸道總裁+現言甜寵+破鏡重圓】落難千金自立自強,傲嬌總裁甜寵撐腰!龜毛客人VS酒店經理,冤家互懟,情定大酒店! 酒店客房部副經理姜幾許在一次工作中遇到了傲驕龜毛的總統套房客人季東霆。姜幾許應付著季東霆的“百般刁難”,也發現了季東霆深情和孩子氣的一面。季東霆在相處中喜歡上了這個倔強獨立的“小管家”。姜幾許清醒地認識到兩人之間的差距,拒絕了季東霆的示愛,季東霆心灰意冷回到倫敦。不久后,兩人意外在倫敦重逢,這次姜幾許終于直視內心,答應了季東霆的追求。正在季東霆籌備盛大的求婚儀式時,姜幾許卻與前男友沈珩不告而別。原來沈珩與姜幾許青梅竹馬,在姜幾許家破產后兩人被迫分手。季東霆吃醋不已,生氣中錯過了姜幾許的求助……
28.4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