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嬌軟夫人擺爛后,清冷權臣攬腰寵》 第1卷 第455章 “桂”字由來
花了三天時間,溫嘉月斷斷續續的地看完了冊子。
其實沈弗寒寫得不算太多,只是他總會將歡好之事寫出來,還會著重描寫的神,讓溫嘉月數次拿起又放下。
看完之后,索直接將冊子沒收了。
“以后不許寫了,”一本正經道,“再被我發現你悄悄做這種事,我就、我就把這些東西燒掉。”
沈弗寒揚眉問:“所以,這一本,你準備珍藏?”
“什麼珍藏!”溫嘉月面紅,“我是怕你又念給我聽!”
這兩日也是躲著沈弗寒看的,生怕一個注意就被他搶走。
“不過我有一事不明,”溫嘉月好奇道,“你在冊子里也寫了‘桂’字極好,要用作昭昭的名字,但是你還是沒說好在哪里,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吧?”
沈弗寒的神有些不自然,半晌才道:“只是覺得好聽而已。”
“我才不信,”溫嘉月作勢要走,“既然你不說,那我不理你了。”
這個字肯定是有寓意的,只是想了許久也沒想出個所以然。
沈弗寒拉住,猶豫道:“我怕我說了之后,你會笑話我。”
溫嘉月:“……”
清清嗓子,道:“我保證不笑,你放心吧。”
沈弗寒觀察了一下的神,這才決定開口。
“你名為月,在我眼里便是月宮嫦娥,月宮里有棵桂樹,我便想給昭昭用桂字,取蟾宮折桂之意。”
Advertisement
溫嘉月確實沒笑,但是陷了沉默。
他的心思,怎麼能比還七拐八繞?
又問:“既然你這麼喜歡這個字,怎麼改了?”
“你不喜歡,而且我又想起了吳剛伐桂的典故,寓意不太好。”
“換玉,是不是也有深意?”溫嘉月琢磨道,“讓我猜猜,不會是因為嫦娥懷里抱著玉兔吧?”
沈弗寒輕咳一聲,微微頷首。
溫嘉月無語地看著他,簡直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最終只好說道:“不愧是沈大人,心思可真是深不可測。”
若沈弗寒沒有告訴,可能猜一輩子也猜不出來。
“不說這個了,”沈弗寒岔開話題,“明日我帶你去見長公主。”
溫嘉月詫異地問:“這麼快?”
“原本我確實想拖延幾日,最好拖到的死期,只是那時可能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便定在了明日。”
從昨日開始,李知瀾的癥狀便加重了。
溫嘉月點點頭:“這樣也好,早日解決,不留后患。”
翌日傍晚,兩人前往詔獄。
溫嘉月第一次來這種地方,只覺得森森的,不得不抓沈弗寒的袖口。
沈弗寒握住的手,安道:“別怕。”
他瞥了眼早已等在一旁的俊秀男人,男人行了禮,自覺地跟在他們后。
沈弗寒邊往里走邊問:“我與你說的,你可記清楚了?”
男人喏喏道:“沈大人放心,奴全都記住了。”
溫嘉月回頭看了他一眼,覺得他的聲音有些耳,但是又不記得在哪里聽過。
小聲問:“他是誰啊?”
沈弗寒低聲道:“長公主的面首。”
溫嘉月這才想起,那日外出遇見長公主、皇上和沈弗寒一同游船時,在茶館里聽到了他和另一個面首的對話。
那時的李知瀾有多意氣風發,今日便有多狼狽不堪
溫嘉月平靜地向監牢最深的紅子。
李知瀾形容枯槁,面無,子蜷在一起,形抖,正忍著病痛的折磨。
閉著眼睛,一聲接一聲地咳嗽著,臉上滿是痛苦之,看起來甚至已經有些神志不清了。
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勉強睜開眼睛,恢復幾分清明。
瞧見為首的男人,驚一聲,拖著病軀進角落里去,口中卻怒斥道:“沈、沈弗寒,你敢……咳咳咳!”
只是剛開口便已經落了下乘,聲線虛弱,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沈弗寒淡聲問:“蝕骨散的滋味可還好?”
“本宮沒想害你!”李知瀾咬牙道,“是你非要喝下那盞酒,怪得了誰?如今、如今竟這樣報復本宮,你好狠的心!”
沈弗寒冷聲道:“新仇舊恨一起算,長公主服下蝕骨散是應該的,也該讓您嘗嘗這種滋味。”
“那溫若歡呢?”李知瀾扶著墻勉力站起,“又到了什麼懲罰?”
沈弗寒拍了下手,獄卒便將五花大綁的溫若歡送了過來。
時隔數月,這是溫嘉月第一次見到溫若歡,險些沒認出來。
比起李知瀾,更是慘不忍睹,頭發和汗漬、跡黏在一起,臉上灰撲撲的,上的裳也破破爛爛,蓬頭垢面,瘦骨嶙峋,都快沒了人樣。
獄卒丟開手,溫若歡本站不穩,直地倒在地上,呼吸微弱。
的眼珠緩慢地轉了兩圈,終于看到了溫嘉月。
像是死而復生一般,手去抓溫嘉月的。
的嗓子里不斷發出“嗬嗬”聲,終于說道:“姐姐,姐姐,救我……”
在到溫嘉月之前,沈弗寒一腳將踢進監牢,將溫嘉月護在后。
溫若歡一陣陣地發懵,瞥見墻角的長公主,又充滿希地爬了過去。
“長公主,救救臣,臣為您辦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您不能見死不救啊!”
李知瀾早已自顧不暇,哪有工夫管,怒聲道:“滾開!”
溫若歡卻已經豁出去了,抱住了的大,任如何拳打腳踢都不放手。
這段時日過得太苦太苦,每日不是大刑伺候便是拷問,十二個時辰不間斷,沒有得過片刻安閑。
好不容易從那個生不如死的地方逃出來,死也不會回去!
沈弗寒看了片刻狗咬狗的好戲,問:“長公主對這個結果可還滿意?”
李知瀾一邊咳一邊開口:“讓出去,出去!”
沈弗寒幽幽道:“長公主可想清楚了,若是出去了,您的面首就要進去了。”
面首適時開口:“奴時刻準備為長公主解憂。”
李知瀾神一僵:“本宮絕不會辱而死,本宮要見皇上!”
“皇上日理萬機,沒空管您的事,”沈弗寒平靜道,“長公主有什麼話,代給微臣便好。”
在他說話時,一道影悄悄靠近,立在蔽的角落里。
猜你喜歡
-
完結2088 章

廢柴王妃又在虐渣了
蕭涼兒,相府大小姐,命格克親,容貌被毀,從小被送到鄉下,是出了名的廢柴土包子。偏偏權傾朝野的那位夜王對她寵之入骨,愛之如命,人們都道王爺瞎了眼。直到人們發現,這位不受相府寵愛冇嫁妝的王妃富可敵國,名下商會遍天下,天天數錢數到手抽筋!這位不能修煉的廢材王妃天賦逆天,煉器煉丹秘紋馴獸樣樣精通,無數大佬哭著喊著要收她為徒!這位醜陋無鹽的王妃實際上容貌絕美,顛倒眾生!第一神醫是她,第一符師也是她,第一丹師還是她!眾人跪了:大佬你還有什麼不會的!天才們的臉都快被你打腫了!夜王嘴角噙著一抹妖孽的笑:“我家王妃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是個柔弱小女子,本王隻能寵著寵著再寵著!”
400.4萬字8.08 204045 -
完結18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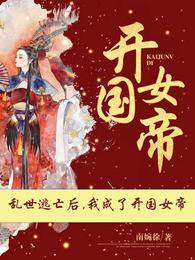
亂世逃亡后,我成了開國女帝
◣女強+權謀+亂世+爭霸◥有CP!開局即逃亡,亂世女諸侯。女主與眾梟雄們掰手腕,群雄逐鹿天下。女主不會嫁人,只會‘娶’!拒絕戀愛腦!看女主能否平定亂世,開創不世霸業!女企業家林知皇穿越大濟朝,發現此處正值亂世,禮樂崩壞,世家當道,天子政權不穩,就連文字也未統一,四處叛亂,諸王征戰,百姓民不聊生。女主剛穿越到此處,還未適應此處的落后,亂民便沖擊城池了!不想死的她被迫逃亡,開
238萬字8.18 16115 -
完結129 章

盛寵
【全文完結】又名《嫁給前童養夫的小叔叔》衛窈窈父親去世前給她買了個童養夫,童養夫宋鶴元讀書好,長得好,對衛窈窈好。衛窈窈滿心感動,送了大半個身家給他做上京趕考的盤纏,歡歡喜喜地等他金榜題名回鄉與自己成親。結果宋鶴元一去不歸,并傳來了他與貴女定親的消息,原來他是鎮國公府十六年前走丟了的小公子,他與貴女門當戶對,郎才女貌,十分相配。衛窈窈心中大恨,眼淚汪汪地收拾了包袱進京討債。誰知進京途中,落難遭災,失了憶,被人送給鎮國公世子做了外室。鎮國公世子孟紓丞十五歲中舉,十九歲狀元及第,官運亨通,政績卓然,是為本朝最年輕的閣臣。談起孟紓丞,都道他清貴自持,克己復禮,連他府上之人是如此認為。直到有人撞見,那位清正端方的孟大人散了發冠,亂了衣衫,失了儀態,抱著他那外室喊嬌嬌。后來世人只道他一生榮耀,唯一出格的事就是娶了他的外室為正妻。
31.9萬字7.92 62628 -
完結99 章

和死對頭成婚后
六公主容今瑤生得仙姿玉貌、甜美嬌憨,人人都說她性子乖順。可她卻自幼被母拋棄,亦不得父皇寵愛,甚至即將被送去和親。 得知自己成爲棄子,容今瑤不甘坐以待斃,於是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死對頭身上——少年將軍,楚懿。 他鮮衣怒馬,意氣風發,一雙深情眼俊美得不可思議,只可惜看向她時,銳利如鷹隼,恨不得將她扒乾淨纔好。 容今瑤心想,若不是父皇恰好要給楚懿賜婚,她纔不會謀劃這樁婚事! 以防楚懿退婚,容今瑤忍去他陰魂不散的試探,假裝傾慕於他,使盡渾身解數勾引。 撒嬌、親吻、摟抱……肆無忌憚地挑戰楚懿底線。 某日,在楚懿又一次試探時。容今瑤咬了咬牙,心一橫,“啵”地親上了他的脣角。 少女杏眼含春:“這回相信我對你的真心了嗎?” 楚懿一哂,將她毫不留情地推開,淡淡拋下三個字—— “很一般。” * 起初,在查到賜婚背後也有容今瑤的推波助瀾時,楚懿便想要一層一層撕開她的僞裝,深窺這隻小白兔的真面目。 只是不知爲何容今瑤對他的態度陡然逆轉,不僅主動親他,還故意喊他哥哥,婚後更是柔情軟意。 久而久之,楚懿覺得和死對頭成婚也沒有想象中差。 直到那日泛舟湖上,容今瑤醉眼朦朧地告知楚懿,這門親事實際是她躲避和親的蓄謀已久。 靜默之下,雙目相對。 一向心機腹黑、凡事穩操勝券的小將軍霎時冷了臉。 河邊的風吹皺了水面,船艙內浪暖桃香。 第二日醒來,容今瑤意外發現脖頸上……多了一道鮮紅的牙印。
25.2萬字8 140 -
完結123 章

不是聯姻嗎?裴大人怎麼這麼愛
姜時愿追逐沈律初十年,卻在十八歲生辰那日,得到四個字:‘令人作嘔’。于是,令沈律初作嘔的姜時愿轉頭答應了家里的聯姻安排,準備嫁入裴家。 …… 裴家是京中第一世家,權勢滔天,本不是姜時愿高攀得起的。 可誰叫她運氣好,裴家英才輩出,偏偏有個混不吝的孫子裴子野,天天走雞斗狗游手好閑,不管年歲,還是性格,跟她倒也相稱。 相看那日—— 姜時愿正幻想著婚后要如何與裴子野和諧相處,房門輕響,秋風瑟瑟,進來的卻是裴家那位位極人臣,矜貴冷肅的小叔——裴徹。 …… 裴太傅愛妻語錄: 【就像御花園里那枝芙蓉花,不用你踮腳,我自會下來,落在你手邊。】 【愛她,是托舉,是陪伴,是讓她做自己,發著光。】 【不像某人。】
23.8萬字8.09 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