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高枝》 第1卷 第164章 要你眾叛親離
宋句清在南州一事后被陛下召回了上京,安獎賞一番后,暫留他在上京住兩個月。
于是張知序就經常在宮門或者刑部校場里看見他。
一開始他沒太在意,覺得這人就是無聊了找地方活筋骨。
但每次自己目掃過去,都能撞見宋句清正在打量自己,張知序就覺得不對勁了。
“他閑得慌?”他問寧肅。
寧肅神復雜:“這人一直在打聽陳大人的向,說是想再跟陳大人切磋一回,陳大人沒搭理他,他估是不甘心,就沖您來了。”
“哦?”張知序眉梢高挑,“在外人眼里,我與已經是一家人了?”
“倒也沒有。普通百姓覺得您二位只是同僚,關系并不親;稍有些接的小吏覺得您二位有些愫,但未得名分。”
“那接得更多的朝中員們呢?”他連忙追問。
寧肅沉默半晌,老實道:“當然是覺得您二位沆瀣一氣狼狽為,要以兩人之力掀翻大盛制,與所有人為敵。”
張知序:“……”得,雌雄雙煞了。
他不滿意地撓了撓眉,剛想走,卻見宋句清突然穿過校場朝自己迎來。
“聽聞張大人文武雙全,在下久在云州,不曾見識。”宋句清朝他拱手,“想請張大人賜教一二。”
張知序手里還著文書,寬大的袖袍飛揚起來,像枝頭上被風吹拂的潔白的玉蘭。
他有禮地頷首:“張某乃文臣,不善武事。”
Advertisement
“可你是陳侯的朋友。”宋句清上下打量他,“那麼勇猛的將軍,邊難道會有腳蝦?”
好拙劣的激將法。
張知序眼皮都懶得抬。
“十支箭,誰中紅心多誰贏。”宋句清大咧咧地就給他塞了把弓,“來,讓我看看傳聞里陳將軍的心上人,到底有幾斤幾兩。”
“……”
為一個講禮守序的文臣,是絕不能與這些蠻橫的武將較勁的。
——但他說他是陳將軍的心上人。
“來。”張知序拉開了弓弦。
宋句清哈哈直笑,接過手下遞來的弓,與他一起搭箭引弦。
兩支箭幾乎同時飛出去,他的箭卻比張知序的先中靶心,且位置更正。
宋句清滿意地點頭,又搭下一支箭。
“主子。”寧肅掃了一眼他手里的弓,低聲道,“這人使詐,自己用的是輕弓,給了您一把重的。”
張知序當然一拉就察覺了,這起碼得是一石的弓,靶子離得不遠,他很吃虧。
但箭已出去一支,現在喊停像是輸不起。
搖搖頭,他繼續搭箭。
張知序準頭已經好了,七支箭只失一支,但這弓實在費力,第八支箭搭上來,他手腕都有些不穩。
宋句清十箭中八,轉頭看過去:“張大人,沒力氣了?”
箭搭弦上,卻半晌也沒能拉開弦。
宋句清正想笑,卻突然有三支羽箭從后方破空而來,越過他側,刷地一聲正中張知序的靶心。
“……”他錯愕回眸。
左側后方,陳寶香一紅白騎裝,手里重弓弓弦仍,發髻間綴紅絨的金釵在秋日之下閃閃發。
“你贏了。”收弓揚眉,朝張知序綻出燦爛的笑意。
來上京的時候宋句清就聽人說過,陳寶香此人險狡詐,唯利是圖,待人只有利用沒有真心。
可現在,這人正一蹦一跳地朝張知序走過去,臉上不見毫算計。
“正好巡到這邊,一起回去?”拉著人家的胳膊問。
“好。”張知序神和地應。
宋句清突然覺得什麼唯利是圖沒有真心可能都是假的,只有張知序是心上人這事是真的。
“陳大人。”他回神開口,“難得有空,比一場?”
“啊,宋大人也在啊。”像是才看見他一般,轉過來拱手,“不巧,今日怕是比不了了。”
宋句清不服:“先前你說公務繁忙沒空比試也就罷了,眼下你分明已經下了工要回家了,怎麼還能說是沒空?”
兩人手兩回,他兩回都沒贏,心里多是有些膈應的。如今已經沒機會再戰,那宋句清想,能在校場里找回點場子也是好的。
結果陳寶香笑瞇瞇地道:“今日不是我沒空,是大人你沒空。”
宋句清:?
不是,他人就在這兒站著呢,還能給安排活兒不?
還真能。
陳寶香話音落了沒多久,后頭就跑來個大理寺的小吏,拱手對他道:“宋將軍,請您隨小的往大理寺走一趟。”
他詫異地看向陳寶香,后者只抓著張知序的胳膊朝他揮手作別。
宋句清:“……”
他以為自己犯了什麼事了,亦或者在上京用輕弓對重弓是犯法的。
結果進去大理寺,謝蘭亭卻問他:“你可知程槐立有個兒?”
宋句清一臉莫名:“程槐立只有兩個侄兒,一直不曾再添子嗣,哪兒又能冒出來個兒?”
“陳寶香。”謝蘭亭道,“有人指認乃程槐立之。”
宋句清震驚,宋句清不解。
宋句清最后打量著謝蘭亭,恍然又好笑:“你們上京城里卸磨殺驢的章程這麼麻煩,還非得給人找個爹不可?看不順眼直接下旨將斬了呀,我們當武將的宿命如此,不會太意外的。”
謝蘭亭:“……”
這些武夫怎麼一個比一個的不講理,他是在查案,又不是在栽贓陷害。
將一本手抄的《藥經》拿過來在他面前攤開,謝蘭亭解釋:“大理寺收集的證據很多,樁樁件件都表明陳寶香跟程槐立早有舊怨,我不是在冤枉。”
這《藥經》據程府的大夫說,是陳寶香手抄的,上頭關于生草的外形描述與敗草一模一樣。
程槐立當初就是用錯了這種藥,才失難治,只能斷保命。
宋句清看了兩眼,更茫然了:“我不識字,這寫的什麼?”
謝蘭亭抬手抹了把臉。
不識字是什麼為大盛的名將的門檻嗎!
“我自邊塞城起就跟著程槐立,對他不可謂不。”宋句清,“他若有這麼厲害的兒,早該將嫁出去為自己換好回來了,豈會藏著直到死才被人發現。”
謝蘭亭聽得都有些懷疑自己了。
“不對。”他搖頭,“什麼都能作假,但那張賣契做不得假,程槐立與陳鳶兒若不是夫妻,就無權做主賣掉的尸;他倆只要是夫妻,那陳鳶兒懷著的就應該是程槐立的骨。”
宋句清倚在椅子里看著謝蘭亭,突然低笑出聲。
“謝大人,你好像沒懂這案子的提告人到底想做什麼。”
謝蘭亭怔然抬眼。
“殺程槐立是圣人的旨意,陳寶香無論是不是程槐立的兒,君臣二字都在父子二字之前。”
宋句清嘆息,“提告人自己想必也知道陳寶香不會獲什麼實罪,鬧這麼一出,無非是想聲名狼藉眾叛親離。”
“的目的達到了,估已經不怎麼在意這案子的結果,只有大人你還執著于此。”
猜你喜歡
-
連載2084 章
王妃又逃跑了
天才醫學博士穿越成楚王棄妃,剛來就遇上重癥傷者,她秉持醫德去救治,卻差點被打下冤獄。太上皇病危,她設法救治,被那可恨的毒王誤會斥責,莫非真的是好人難做?這男人整日給她使絆子就算了,最不可忍的是他竟還要娶側妃來噁心她!毒王冷冽道:「你何德何能讓本王恨你?本王隻是憎惡你,見你一眼都覺得噁心。」元卿淩笑容可掬地道:「我又何嘗不嫌棄王爺呢?隻是大家都是斯文人,不想撕破臉罷了。」毒王嗤笑道:「你別以為懷了本王的孩子,本王就會認你這個王妃,喝下這碗葯,本王與你一刀兩斷,別妨礙本王娶褚家二小姐。」元卿淩眉眼彎彎繼續道:「王爺真愛說笑,您有您娶,我有我帶著孩子再嫁,誰都不妨礙誰,到時候擺下滿月酒,還請王爺過來喝杯水酒。」
352.4萬字8.17 497707 -
完結777 章
玄醫梟後
青南山玄術世家展家喜添千金,打破了千年無女兒誕生的魔咒。 滿月宴上言語金貴的太子殿下一句「喜歡,我要」,皇上欣然下旨敕封她為太子妃。 這位千金從出生開始就大睡不醒,一睡就是三年。都傳是因為她三魂七魄隻覺醒了命魂,是名副其實的修鍊廢物。 不但如此,這位千金還被展家給養歪了,是紈絝中的翹楚。沒有修為但各種法寶層出不窮,京城中金貴公子沒被她揍過的屈指可數,名門閨秀見到她都繞道走,唯恐避之不及。 所有人都不明白,生在金玉富貴堆、被展家捧在手心裡長大的千金小姐,怎麼就養成了這幅模樣,都很佩服展家「教女有方」。 展雲歌,玄術世家展家的寶貝,玉為骨、雪為膚、水為姿,名副其實的絕世美人。出生以來隻喜好兩件事,看書、睡覺,無聊時就去鞏固一下自己第一「梟」張紈絝的名頭。 南宮玄,華宇帝國太子,三魂七魄全部覺醒的天才。容貌冠蓋京華、手段翻雲覆雨、天賦登峰造極、性子喜怒不形於色,嗜好隻有一個,就是寵愛他從小就看入眼的人兒,從三歲開始就勵誌要在她的喜好上再添上一個南宮玄。 自從展雲歌知道自己滿月時就被某太子貼上屬於他的標籤後,就發誓,既然這麼完美的男人,主動投懷送抱了,而且怎麼甩也甩不掉,她自然是要把人緊緊的攥在手心裡。 世人皆知她廢材紈絝,隻是命好投胎在了金玉富貴頂級世家裡,唯獨他慧眼識珠,強勢霸道的佔為己有。 「梟」張是她前世帶來的秉性。 紈絝是她遮掩瀲灧風華的手段。 看書是在習醫修玄術,睡覺是在修鍊三魂七魄。 當有一天,她的真麵目在世人麵前展開,驚艷了誰的眼?淩遲了誰的心? 心有錦繡的世家貴女展雲歌和腹黑奸詐的聖宇太子南宮玄,在情愛中你追我逐,順便攪動了整片大陸風雲。 他以江山為賭,賭一個有他有她的繁華盛世。 --------------------- 新文開坑,玄幻寵文,一對一,坑品絕對有保證!陽光第一次這麼勤奮,昨天文完結,今天就開新文,希望親們一如既往的支援陽光,別忘記【收藏+留言】外加永不刪除。 推薦陽光的完結文: 絕品廢材:邪尊的逆天狂妃:玄幻 婿謀已久之閑王寵妻:古言、架空 浮世驚華之邪王謀妻:古言、架空 霸道梟少狂寵妻:現代、豪門 絕戀之至尊運道師:玄幻
213.4萬字8 68793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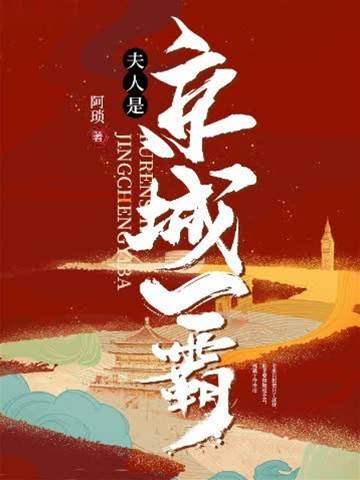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687 章

腹黑萌寶神醫娘親惹不起
【本書又名《我假死後,冷冰冰的王爺瘋了》假死追妻火葬場後期虐男主白蓮花女主又美又颯】一朝穿越,蘇馥竟成了臭名遠昭醜陋無鹽的玄王妃,還帶著一個四歲的拖油瓶。 玄王對她恨之入骨,要挖她的心頭血做藥引,還要讓她和小野種為白月光陪葬。 她絕處逢生,一手醫術扭轉乾坤,將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一心盼和離時,誰料玄王卻後悔莫及。 曾經冷冰冰的王爺卑微的站在她身後「阿馥,本王錯了,你和孩子不要離開本王,本王把命給你好不好?」 等蘇馥帶著兒子假死離開后,所有人以為她們葬身火海,王爺徹底瘋了!
67.5萬字8 1041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