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高枝》 第1卷 第138章 知人善用的長公主
上京里形勢愈發地了,今日有人政見不合當堂對罵,明日就有人橫死街頭難以追兇。
朝中人人自危,不高位之人白日進宮面圣,夜晚又戴帽前往長公主府,就為誰都不得罪,多條路走。
造業司主張知序卻在這個節骨眼上站出來,當堂言明制腐朽民生凋敝,不止造業司的條例該修,大盛的律更是該明。
此話無異于將滿堂的員一起得罪個遍。
誰都清楚,大盛律法維護的是統治的穩定、皇權的威嚴、百的地位,百姓的權益只不過是夾雜在各個篇章里的點綴罷了,憑什麼修?還憑什麼要往損害他們利益的方向修?
一時間群激憤,張家好幾個叔伯站出來斥罵割席,請陛下重罰于他;當朝宰輔更是直言荒唐,說年輕人空談闊論,豈能上臺面。
張知序就在他們的喊聲里,將自己修訂過的《大盛律·賦稅篇》一擲而出。
雪白的卷軸飛滾鋪開,清秀的筆跡麻麻地延到了帝王玉階之下。
“張知序,你大膽!”李束震怒。
這人是他看中的駙馬,眼看弱冠將至婚事將,他怎麼敢在朝堂上扔出這樣的東西。
“陛下。”張知序雙手抵額,一磕到地,“律法不明執行者便會權勢過重,執行者權重則易失本心傾軋人命,百姓乃國之基,盛律嚴明是民心所向,修律之事迫在眉睫,請陛下三思。”
“你只是造業司的,怎麼敢妄議修律之事!”
Advertisement
“就是,三省的大人們還沒吭聲呢,這不越俎代庖麼。”
“請陛下務必嚴懲張知序,以正風氣!”
群臣喧鬧,罵聲不止。
李秉圣站在前頭看著,暗道一聲這是真有種,居然敢直接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這燙手的東西往朝堂上一甩,樹敵何止在場的諸位,新帝若再點他當駙馬,豈不就是告訴群臣他其實也是支持這事的。
“這就是你們張家教出來的好兒郎。”李束沉怒,目下掃。
張元初立馬出列跪地,拱手道:“陛下,張家與此人已然斷絕了關系。此人狂悖,不忠不孝,無父無母,今朝犯事,自然任由陛下置。”
張知序垂眼跪著,手指微。
“好。”李束閉眼,“那就褫奪他的符印,打大牢,聽候發落。”
晨鐘被木樁一撞,遠遠傳來沉悶又厚實的回響。
·
陳寶香急匆匆地進長公主府的大門。
張知序說會自己理,但也沒說是這麼理啊,張家明哲保,他又把人都得罪了,進大牢哪還能囫圇出來。
一頭沖到長公主跟前,剛想開口求令牌,卻發現旁邊客座上坐了個人。
“跑這麼急做什麼。”李秉圣打著扇子笑。
張知序側頭,將手邊的茶放到面前:“不燙。”
陳寶香端起來就咕嚕咕嚕喝了個干凈,一雙眼瞪得老大:“你,你怎麼在這里?”
張知序看向李秉圣。
后者唏噓搖頭:“如卿所言,咱們這個大盛吶,律是真的不嚴明。這不,私權一傾軋,犯人就被放出來了。”
陳寶香大喜:“多謝殿下!”
“別謝這麼早,本宮費那麼大勁撈他出來,自然不是只為了讓他給你倒茶喝的。”
此話一出,兩人都是一頓。陳寶香眉頭微皺,甚至已經開始盤算自己能有什麼籌碼去換。
結果李秉圣瞥了一眼旁邊矮幾上放著的案卷,說的卻是:“這東西他得接著寫,本宮也很好奇,他到底能把人得罪到什麼地步。”
張知序心口一跳,驟然抬頭。
接著寫……嗎?
陳寶香眉頭驟松,哇地就驚呼出聲:“殿下您也太識貨了吧。”
李秉圣扶額:“我這知人善用,什麼識貨。”
“都一樣都一樣。”欣喜地拍手,“總之比皇城里那位可強多了。”
這話說得大逆不道,旁邊的張知序背脊都了。
但李秉圣似乎已經習慣了,見怪不怪,還搖著扇子笑出了聲:“你這張啊。”
旁邊的屬恭敬地上來收卷軸。
李秉圣想了想,吩咐:“讓人把這個多謄抄幾份,往各大書院里散一散,再讓人去給陛下送盞安神茶。”
李束當然不會同意這樣修律,但民間學士們一看就知道張知序是為民謀福沒有私心。
這樣的人在李束手下,只會被打大牢。
皇位上坐著的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們心里也該有數。
李秉圣收斂了笑意,微微瞇眼。
在十歲那年就被父皇立為皇儲,隨軍征戰三年、掌管國庫七年,治國之策倒背如流,輔國三年更是功績累累,朝廷外無不盛贊,在民間也頗有威。
若李束是堂堂正正打敗了而后繼位的,李秉圣無話可說。
可這賊豎子卻是安了人在邊長達十年,專挑父皇病重時對當時懷六甲的下藥,要讓一尸兩命。
掙扎了半個月才勉強從地府邊緣爬上來,李束卻又以是子、尚無子嗣且還要經歷生產這等丟命之事說無法承擔繼任之責。
李秉圣死也咽不下這口氣。
要李束滾下那皇位,不是禪位,也不是傳位,一定是作為臣賊子被清理,再被刻在史書上萬世唾罵。
合攏香扇,李秉圣詢問屬:“軍那邊況如何?”
屬汗道:“尚未事。”
嘖了一聲:“先前吳時不是已經坐上了軍副統領之位?”
“是有這麼回事,但軍有三十來位副統領,他一個人也實做不了什麼事。”
“史大那邊呢?”
“史錄事奉命接管江南一帶的行宮,但似乎遇見不阻礙,尚未事。”
“尤士英那邊?”
“尤將軍雖武力過人,但邊的謀士不太堪用。”屬了額上的汗水,“與程槐立麾下的宋句清在云州附近相遇,惜敗。”
李秉圣臉黑了大半。
“殿下恕罪。”副重新跪下,“勝敗乃兵家常事,況且這幾位大人所行之事本就艱難。”
他們行的事艱難,陳寶香行的事就容易了?人家怎麼就能順利完的任務還不找任何借口。
剛這麼想,一旁的謀士花令音就回稟:“殿下,陳統領麾下的趙懷珠昨日與程槐立麾下的孟天行在西郊外相遇,對方不知為何主手,趙懷珠大勝,但由于下手過重,今日被史臺參奏了。”
“哦?”李秉圣終于又笑了,“怎麼個‘太重’法兒?”
“孟天行帶了五百多人出去,回城的時候……”花令音微微一頓,拱手,“不知怎麼就只剩一半了。”
在場眾屬臣皆驚,陳寶香卻是一臉理所應當。
懷珠師姐就該這麼厲害,折對面一半都算輕的。
“既然是對方先的手,那又怎麼能怪在頭上呢。”李秉圣一臉慈祥地搖頭,“程槐立也是,一把年紀了還那麼小心眼,日地跟寶香過不去。”
“這樣吧,本宮做東,在樂游原給程將軍和陳統領辦一場和解宴,你去傳話,請程將軍務必要來。”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小公主又幫母妃爭寵了
穿書成了宮鬥劇本里的砲灰小公主,娘親是個痴傻美人,快被打入冷宮。無妨!她一身出神入化的醫術,還精通音律編曲,有的是法子幫她爭寵,助她晉升妃嬪。能嚇哭家中庶妹的李臨淮,第一次送小公主回宮,覺得自己長得太嚇人嚇壞了小公主。後來才知道看著人畜無害的小公主,擅長下毒挖坑玩蠱,還能迷惑人心。待嫁及笄之時,皇兄們個個忙著替她攢嫁妝,還揚言誰欺負了皇妹要打上門。大將軍李臨淮:“是小公主,她…覬覦臣的盛世美顏……”
105.9萬字8 170382 -
完結729 章
東風第一枝
葬身火場的七皇子殿下,驚現冷宮隔壁。殿下光風霽月清雋出塵,唯一美中不足,患有眼疾。趙茯苓同情病患(惦記銀子),每日爬墻給他送東西。從新鮮瓜果蔬菜,到絕世孤本兵器,最后把自己送到了對方懷里。趙茯苓:“……”皇嫂和臣弟?嘶,帶勁!-【春風所被,第一枝頭,她在他心頭早已綻放。】-(注: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97.7萬字8 8970 -
完結467 章

全家帶著千億物資去逃荒
【全家穿越、空間萌寵、逃荒、種田】 蘇以安撓著雞窩頭看著面前冰山臉少年,心里一頓MMP。 全家集體穿越,本以為是個大反派制霸全村的勵志故事,這咋一不小心還成了團寵呢? 爹爹上山打獵下河摸魚,他就想老婆孩子熱炕頭,一不小心還成了人人敬仰的大儒呢。 娘親力大無窮種田小能手,就想手撕極品順便撕逼調劑生活,這咋還走上了致富帶頭人的道路呢? 成為七歲的小女娃,蘇以安覺得上輩子太拼這輩子就想躺贏,可這畫風突變成了女首富是鬧哪樣? 看著自家變成了四歲小娃的弟弟,蘇以安拍拍他的頭:弟啊,咱姐弟這輩子就安心做個富二代可好? 某萌娃一把推開她:走開,別耽誤我當神童! 蘇以安:這日子真是沒發過了! 母胎單身三十年,蘇以安磨牙,這輩子必須把那些虧欠我的愛情都補回來,嗯,先從一朵小白蓮做起:小哥哥,你看那山那水多美。 某冷面小哥哥:嗯乖了,待你長發及腰,我把這天下最美的少年郎給你搶來做夫君可好? 蘇以安:這小哥哥怕不是有毒吧!
87.4萬字8 47099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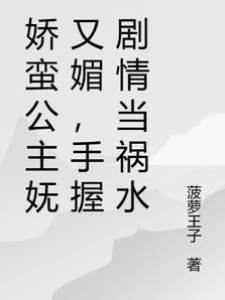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57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