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冷[先婚後愛]》 傷口結痂
傷口結痂
臺風剛剛過去, 但可能還會有餘震,島上的人現在都在山上的酒店和暫時搭建的志願者營地這邊。
梁棲月把小孩給了當地認識的志願者,跟著商牧之一起乘坐當地居民的搜救車回了山上的酒店。
商牧之來這邊是談一筆訂單的, 按照訂單的數額其實本用不著他親自跑一趟,要不然也不會遇上這場臺風。
搜救車很簡陋, 像是那種改裝的只有三個子的車, 一路上開到山頂路段坑坑窪窪的,梁棲月幾次沒太坐穩往商牧之那邊倒了幾下, 肩膀跟他在一起, 但商牧之沒手扶的意思, 側臉在籠罩著樹影的線裏顯得特別冷。
從剛才看見, 把水遞給之後他就沒有跟自己講過話, 也沒問為什麽會忽然在這裏。
梁棲月看了他好幾眼, 他也都沒像完全沒有察覺到一樣。
梁棲月有些後悔,自己剛才看見他的時候就應該沖上去抱住他,哭著出來眼淚都蹭到他服上,然後說出自己從港城專程跑過來找他的,不想離婚了, 後悔了。
但是錯過了剛才的機會, 現在好像什麽話都有些講不出來。
地上還有些泥濘, 搜救車經過幾個坡度, 積了水的窪地裏髒水濺到上,梁棲月沒有管, 在搜救車又把往商牧之那邊摔的時候扶穩了自己的座椅,沒有再靠過去擾他。
搜救車到達了山上的酒店, 商牧之跟送他們上來的當地人說了謝謝,然後走到位置那邊, 手幫把行李箱拿下來。
梁棲月愣了下,以為他剛才手是要扶自己的,幸好沒有把手出去。
“酒店房間不多,你住我的房間。”
商牧之提著的行李箱走在前面,言簡意賅地說。梁棲月愣了愣,下意識地問,
Advertisement
“那你呢?”
商牧之腳步停頓了下,轉頭看了一眼,眼神很平淡,甚至有點冷漠,又轉過,
“我跟助理一。”
梁棲月攥著掌心,有點失地哦了一聲。
供電系統還沒完全恢複,電梯壞掉暫時沒辦法用,他們走的樓梯。
酒店建築不算高,商牧之的房間在七樓,但走上去還是有些累。
梁棲月爬上樓的時候盡量沒有表現的自己很累,不過商牧之可能是在山下幫忙了一整天有些累了,走的很慢不說,中間還休息了一下,去三樓那邊的自販賣機那邊買了兩瓶礦泉水,遞給了一瓶。
兩個人在安靜漆黑的樓道裏喝水,商牧之幫擰開瓶蓋後才遞給,但依舊沒有跟講話。
視線裏很暗,梁棲月聞到了商牧之搜救服外套上的海鹽味道,還有一腥味。
“你傷了嗎?”
小口的喝著水,主開口先問他。
商牧之站在樓梯角,後是酒店的走廊開的一扇小窗,因為臺風和地震帶來的災害還沒過去,外面的山上都很亮,有從窗口映照進來,不是很清晰地照著他的側面的廓線條。
梁棲月看見他仰頭喝水,結滾了下,又擰上蓋子,在問完這句話後轉過臉,似乎是在看自己,不過背的位置看不清他此刻的表,只是覺到他的視線在自己上,目沉甸甸的,又沒有太多的溫度。
“跟你有關系嗎?”
他口吻很輕、很淡地說。
梁棲月愣在原地,覺手中握著的礦泉水變得很重,有些握不住。
商牧之說完,好像什麽都沒發生一樣,重新提起行李箱繼續上樓。
終于到了七樓,梁棲月撐著膝蓋氣,商牧之走到一扇門前面,輸碼,打開房間門,把行李箱提了進去。
梁棲月跟上去,覺得他態度實在冷淡的讓人難。
轉機的時候都沒有好好休息過,乘船的時候還很擔心臺風會不會折返,一直都在擔心他。
商牧之把行李箱提進去,簡單收拾了一下他自己的東西放進他的黑行李箱裏。
梁棲月站在房間門口,看著他提著箱子要走,往後站了一步,擋住出去的門。
商牧之停下腳步,垂眸視線平靜地看著,好像是等著先開口,
梁棲月抿了下,
“你不問問我為什麽會出現在這裏嗎?”
商牧之沒有說話,只看了一會兒,沒什麽語氣地說,
“林肅告訴你的?”
梁棲月點頭,
“嗯,”又擔心他誤會了什麽立刻搖頭補充道,“是我自己要來的。”
商牧之沉默地看著,沒有放下他手上的黑行李箱。
梁棲月仰頭著他,擔心自己講的還不夠清楚,
“我擔心你。”
商牧之依舊沒有說話,只是垂著眼看著,靜了兩秒才說,
“嗯,知道了。”
他說完推著行李箱還是要出去。
“我,”梁棲月有些著急了,手抓住他的袖,
“商牧之,我不想,不想跟你分開。”
商牧之作停頓了下,拿開的手,低頭看著梁棲月,用一種很理智平靜地口吻說,
“今晚好好休息,明後天供電就會完全恢複,其他事等回港城再說。”
“可是我,”
梁棲月不想讓他走,抓著他還想說什麽。
商牧之將的手腕拿掉,一句話也沒說,帶上房間門離開。
—
梁棲月第二天一早就醒了,外面還在繼續搜救和重修房屋,發出的聲音很大。
了眼睛,照鏡子的時候發現的眼睛腫了起來。
昨天晚上睡覺之前沒忍住哭了,最後都不記得是睡著的。
洗漱完下樓,梁棲月原本想去找商牧之,但是發現自己好像沒有他現在的聯系方式,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間房。
酒店的前臺在給外面因為臺風失去房子的小孩們發盒飯,梁棲月過去充當志願者幫忙。
一上午都在跟幾個志願者一起幫忙這些小朋友們找家長,中午在酒店簡單吃了盒飯,又跟著他們一起到山下去搜救。
商牧之昨天就在志願者營地那邊,他肯定今天一早也是去幫忙了。
梁棲月想到昨天在樓梯口那邊聞到的他上的腥味道,不知道他是哪裏傷了。
到了志願者營地,梁棲月又看見了昨天晚上到的那個小孩,對方正一個人坐在外面的石頭上,看上去很可憐的樣子。
梁棲月走過去的時候好像認出自己來了,一雙眼睛頓時變得有些潤,很可憐地看著自己。
梁棲月愣了愣,猶豫了下走過去,用英文問怎麽了。
小孩不知道有沒有聽懂,好像哭了兩下,然後抱著的腰埋進懷裏面。
梁棲月僵了下,下意識地想要手推開,但手掌放到的肩膀上的時候又變了很輕地拍了拍。
從志願者那邊得知,小孩的父親很早就已經去世了,母親在外務工很早就沒有回來了,一直跟著爺爺生活,但臺風來的時候他們的房子剛好在山腳,加上地震,房子直接塌了,爺爺也被送進了醫院,現在還沒離危險。
下午在營地幫忙的時候梁棲月一直帶著小孩一起,等到晚上天黑了對方還有點舍不得的樣子。
不過梁棲月要回酒店了,因為已經天黑了,再晚點可能不太安全。
白天一整天都沒在島上見商牧之,梁棲月回酒店的時候有些不放心,問了一下跟一起的志願者,描述了下商牧之的外貌,問有沒有見過他。
對方聽的描述,好像一下子就猜到了是誰,說商牧之在剛剛出事的時候就組織了島上的游客和當地的居民一起,幫了很大的忙。
不過昨天晚上他好像為了救埋在廢墟裏的人了傷。
梁棲月心口一跳,立刻問是哪裏。
對方比劃了下,說是後背那塊。
梁棲月立刻想到之前在瑞士那一次,才過去半個月,可能是傷口又裂開了。
回到酒店,梁棲月先問了下前臺知不知道商牧之隨行助理的房間在哪裏,前臺說不清楚,酒店的系統維修,有些住宿信息調不出來,又提醒早點回房間去,今天可能會有餘震。
梁棲月擔心商牧之的況,問前臺要了理傷口的碘伏棉簽和紗布,心不在焉地先回了自己的房間。
島上的信號還沒好,梁棲月聯系不到商牧之,自己的手機也一起沒了信號。
把剛才問前臺要的那些紗布碘伏都放好,梁棲月直接去了浴室洗澡。
一整天在山下幫忙,覺得自己現在渾都是臭臭的。
洗完澡出來,梁棲月準備吹頭發,剛剛拿到吹風機,還沒電,房間的燈忽然閃了閃,地面也有點震。
立刻想到剛才前臺說的餘震,放下吹風機就先準備下樓。
七樓不太方便,從走廊穿過到安全通道,不人這會兒也都在往樓下跑。
梁棲月忽然想到商牧之,不知道他在幾樓在哪間房,萬一他現在正在房間睡覺怎麽辦?
樓道昏暗,聲音又嘈雜,腳步聲到都是還有人推了一把。
梁棲月沒有多想,又從樓上折返回去。
商牧之的助理房間可能也在七樓,或者就在那附近,他知道出事肯定也會回去找的。
梁棲月逆著人流又回到七樓,這會兒人基本上都已經跑了,好在地板房屋也沒像剛才那樣晃。
走廊空空,還有幾間房間的門因為走得太急都沒關,地毯上還有人掉的拖鞋。
梁棲月看著空落落的走廊,松了一口氣之餘,心口又有種像被綿絮塞住一樣的覺。
商牧之沒有回來找自己。
慢慢地往房間裏走,聽到樓梯那邊又有斷斷續續的腳步聲往回走,應該是樓下通知說餘震幅度小,不用擔心所以有人回來了。
剛才走的很急,梁棲月發現自己腳上的鞋子不知道什麽時候也被掉了一只,頭發還沒吹幹就跑了出來,巾也不見了,答答的落下來在往下滴著水。
現在肯定看上去特別狼狽可憐。
走回房間,裏面燈剛才出門之前被記得關掉了,房間暗暗的,進門坐在靠著門那邊牆壁的沙發上,沒有關門,一個人開始發呆。
商牧之真的要跟分開了嗎?
怎麽這麽快呢,才三天、四天、還是五天?
梁棲月坐在沙發上,聽見走廊那邊有聲音在跑的很焦急,沒有去管,只是在想自己應該要怎麽辦。
現在還沒有簽字,可是商牧之想做的事能阻止嗎?
離婚了的話,自己要重新追求他嗎?
不會追人。
而且商牧之應該很難追。
“梁棲月!”
思緒七八糟的時候商牧之的聲音很突然地從頭頂響起,手臂被人一把用力拽了起來,
“你是白癡嗎?這個時候還在房間不知道往下跑?”
“臺風地震你是不是以為鬧著玩的?”
“到底他媽的是誰讓你過來的?!”
他語氣難得的充滿暴怒的焦躁和張,邊說邊拉起就往外走。
梁棲月整個人還有點沒太反應過來,但注意到商牧之很明顯著的呼吸和他上穿著的被汗水打的黑T恤衫。
很明顯是跑了很長一段路來找的。
跟著他走了一段,到外面樓梯口的時候不再了。
商牧之停下腳步,轉頭看,眉擰得很,顯然還沒從剛才的怒意中回緩過來,
“你是到跑不了?”
他語氣明顯很生氣,但卻彎下腰抱起準備下樓。
“不是。”
梁棲月被他抱在懷裏後才開口,
“剛剛酒店前臺說已經沒事了,不用跑。”
商牧之作停住,整個人很明顯的放松了幾分,但額角繃得很的青筋上有汗水正在往下滴。
梁棲月手掉他臉上的汗水,手臂環住他,看著他說,
“你是專門回來找我的嗎?”
商牧之沒有說話,只是沉默著好像慢慢變得冷靜了下來,也恢複了理智,松開手,要把放下來。
梁棲月手抱著他的脖頸不放手,有些不講道理地說,
“你是不是也本不想離婚,你還喜歡我對不對?”
猜你喜歡
-
完結367 章

前妻,敢嫁別人試試
三年前,她在眾人艷羨的目光里,成為他的太太。婚后三年,她是他身邊不受待見的下堂妻,人前光鮮亮麗,人后百般折磨。三年后,他出軌的消息,將她推上風口浪尖。盛婉婉從一開始就知道,路晟不會給她愛,可是當她打算離去的時候,他卻又一次抱住她,“別走,給…
95.4萬字8 74666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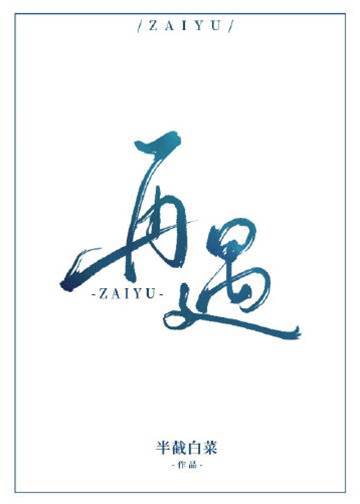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8890 -
完結641 章
重返七零之空間小辣妻
末世大佬唐霜穿到年代成了被壓榨的小可憐,看著自己帶過來的空間,她不由勾唇笑了,這極品家人不要也罷; 幫助母親與出軌父親離婚,帶著母親和妹妹離開吸血的極品一家人,自此開啟美好新生活。 母親刺繡,妹妹讀書,至于她……自然是將事業做的風生水起, 不過這高嶺之花的美少年怎麼總是圍著她轉, 還有那麼多優秀男人想要給她當爹,更有家世顯赫的老爺子找上門來,成了她的親外公; 且看唐霜在年代從無到有的精彩人生。
121.5萬字8 68733 -
完結2314 章

第一名媛:奈何嬌妻太會撩(盛莞莞凌霄)
“我愛的人一直都是白雪。”一句話,一場逃婚,讓海城第一名媛盛莞莞淪為笑話,六年的付出最終只換來一句“對不起”。盛莞莞淺笑,“我知道他一定會回來的,但是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父親車禍昏迷不醒,奸人為上位種種逼迫,為保住父親辛苦創立的公司,盛莞莞將自己嫁給了海城人人“談虎色變”的男人。世人都說他六親不認、冷血無情,誰料這猛虎不但粘人,還是個護犢子,鑒婊能力一流。“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麼?”“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說你不好,那個人依然把你當成心頭寶。”
426.6萬字8 397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