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澳春潮》 第1卷 第70章 脾氣
凌晨四點多,謝之嶼把床單丟進洗機。
他單手抄著兜,停在老舊洗機前冥想。
多久沒跟頭小子似的控制不了自己了?
……太久了。
久到他都快忘了人是有的。
以他的地位,不會愁沒人。可就是因為多年前陸坤的一招人計,還沒近便被他發現暗藏殺機,以至于在這種環境下,旁人說起他不近都覺得有可原。
沒人會主往他邊送人。
除了何氿。
至于何氿送的那些,謝之嶼連看都懶得看一眼。
他評價何氿眼太差,何氿直呼放屁。
后來何溪替他擋了那些七八糟的人,溫凝又替他擋了何溪。一環接一環,所有環節理應是一樣的。
他固執地這麼認為。
也或許連他都不敢承認,某些環節已經變了質。
在一個平平無奇的夜晚,他的夢多了許多不可控。握得他嚨發,他的自制力猶如馬奇諾防線,太瘋狂跳,在夢境顛覆的前一秒,忽然醒了過來。悉的天花板,窗外悉的擁夜。
一涼。
他慢慢起,腔里狂跳的心臟因為這份現實趨于平緩。極力控制的和念在聽到臺玻璃門輕輕一聲響后忽然山崩海嘯來臨。
凌晨三點的冷水澡,凌晨四點的換洗。
Advertisement
這些驗堪稱奇妙。
以至于早上坐在餐桌前,溫凝用睡不醒的朦朧調子問他“謝之嶼,你夜里是不是去做賊”時,他作一怔,筷子上的東西了出去。
“大半夜不睡覺,我真的服了你。你知不知道這間房子隔音很差!”
溫凝咬一口蛋撻,咀嚼,咀嚼,咀嚼。
沒聽到他有反應,抬眼。
他正坐在餐桌另一頭,薄薄的眼皮垂斂,專心致志用左手夾一筷腸。
腸,昨晚還使得好好的餐,今天偏不聽話。
夾起,掉下。
忍住想替他去夾的沖,忍了一秒、兩秒、三秒……算了,忍不下去。
溫凝夾起一筷子遞過去:“啊。”
“……”
“吃不吃啊?”眨眼。
并不是很想。
結不著痕跡了,謝之嶼后仰:“放下。”
呵,男人的面子。
溫凝腹誹。
可不是什麼樂于助人的好標兵,被拒絕一次絕不會提出第二次。于是這頓早餐順利到結束,直到吃完起。
余一瞥,又看到一顆錯的扣。
所以說人沒了慣用手真的不行。
提醒:“謝之嶼,系錯了。”
大概因為今天要出門,謝之嶼恢復了先前的打扮。白襯每顆扣都順著,在他不曾注意的位置,錯位了一顆。他聞言用左手去捋,一路往下:“這顆?”
“下一顆。”
溫凝說著湊近,幫一次是幫,幫兩次也是幫。很自然地替代了他沒有章法的左手,隨口道:“你們賭場該不會有什麼不穿襯衫要扣著裝分的奇怪要求吧?”
“賭場沒有。”
賭場沒有,那是哪里有呢?
溫凝腦子胡地轉。忘了自己總是在他穿襯的時候習慣關注他的領口。一截漂亮又修長的線條,讓人口干舌燥。
于是今早起來原本是要拿套頭衫的,手指在柜子里一圈,最后還是鬼使神差選了襯衫。這件襯暗紋打底,有垂墜的。如果沒記錯,連何氿那樣的挑剔男都夸過這個牌子的版型括又修。
去賭場,這麼穿很正常。
謝之嶼說服自己。
“扣好了沒?”他低頭。
這樣的姿勢,他能看到溫凝發頂很小的旋兒,幾乎被濃長發遮蔽。用慣了的果木香源源不斷鉆進他鼻腔。像在懶洋洋的午后,躺在松草地上聞到一片果樹林。
睜眼,卻是現實里仄的四方地。
溫凝幾下扣好他的扣,拍一拍:“這件襯好像是我常買的那個牌子。”
眼睛真毒。
謝之嶼面不改:“嗯,今天要見的人重要。”
……
十點不到,他出門,也出門。
小鐘和阿忠同在巷口等著。
謝之嶼放慢腳步:“你去哪?”
“你管呢!”
溫凝說著出手包里正在震的手機,看一眼來電顯示:“喂,清柏哥。”
是那種面對他時不曾有的雀躍語氣。
謝之嶼眸深暗,自嘲地扯了下。
“嗯,我出門了。現在過來。”
“一會見,拜拜。”
電話掛斷,他的緒也斷在那截。于是再開口,聲音變冷了許多:“原來是去見普通先生,難怪。”
普通先生這個梗還沒過去呢?
難怪什麼難怪?
溫凝想氣氣不出,想笑又笑不了,對著他的冷臉擺半天表只剩下一個對著任何人都一樣的標準笑容:“是是是,我就是去見清柏哥。謝先生,你這副拈酸吃醋的表會讓我很誤會的。”
被敷衍的笑刺到。
謝之嶼轉開臉:“想得真多。”
到底想沒想多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溫凝說:“那你老是管著我做什麼?”
“隨口一問。”他道,“你也可以當什麼都沒聽見。”
“可是我已經聽見了。”溫凝抓著不放,“你自己消失可以一聲不吭,我就在澳島見見朋友還得告訴你行程?謝之嶼,你這人好沒意思。”
好沒意思的人停下去拉車門的手。
“我沒意思?”
“不然?”
“你的清柏哥就這麼有意思,是嗎?”
“這和他有什麼關系?我在說你。”溫凝抿了下,眼睛直勾勾看著他,“你就不能就事論事?扯旁人做什麼?”
如果不是來了脾氣,溫凝一定會發現,的口而出里,將宋清柏劃作了旁人。
眼下,只記得得不到消息的那四個白天,三個夜晚,問了無數遍阿忠。
“阿忠,你老板到底去哪了?”
阿忠說不出所以然。
又問小鐘。
小鐘的回答反反復復也是一句:“唔好意思啊溫小姐。嶼哥出去做什麼,幾時回,我們都不知。”
好一個不知。
活該白白擔心,活該每天一次糖水鋪,去到老板都揶揄:“哇,大明星。我家糖水這麼好吃,天天看你來,想來是我要發達了哦!”
是啊是啊,都是活該。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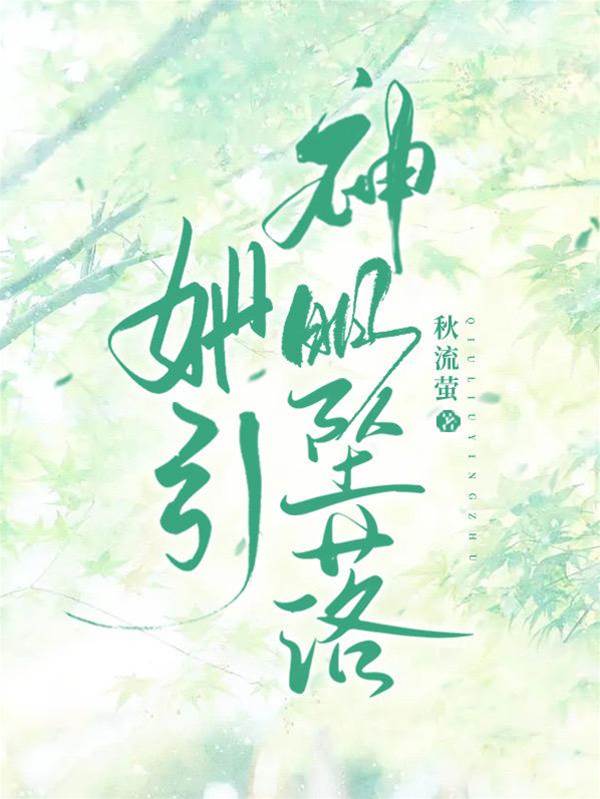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