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你萬千》 第四十八章 祝裴總前程似錦
是裴云闕先放開的。
那力道松開的瞬間,手臂也留有一道紅印,以眼可見的速度漸漸變淡。
他們都盯著那道印子,不約而同地失神剎那。
廖宋也不知道怎麼會巧這樣,大學時還算相的學弟通過群里聯系,他們今晚有個本市的活,缺翻譯閑著沒事來湊人頭。
在這里到他和……其他人,確實是意外。
但又不只是意外。
打的那個照面,裴云闕垂下眼簾的那個瞬間,廖宋都沒意識到這是誰。
裴云闕,從見第一面起,臉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表。
一次也沒……不,一秒也沒有。
那不是神冷漠與否的問題,于廖宋來說,那幾秒里,他就像陌生人。
裴云闕有脾氣很差的時候。
他格里挑剔、尖銳、敏的部分非常清晰,但是又像一個刺猬,稍微給點溫度就把的部分又出來,是有時候還哼哧哼哧地打個滾的小。
如果說脆弱氣質像是[我容易被傷害],那裴云闕就是這類人的極端。
他不單單是可以被傷害,廖宋能看到的這個人,還有[不住了也會扛著]的部分。
在這段漫長又短暫的時間里,不只是在他。
也在探索他,接近他,知他,保護他……保護不了也想保護,怕他發現,悄悄地保護。
這也是廖宋意識到的起點從何而來。
是從心疼來的。
很明顯,讓眼生的這個裴云闕,是在他那個世界時的慣常狀態。
像一道不見底不反的深淵,隨便丟個石子下去永遠也不會響。誰也不會在這個漠然、鷙的男人上找到半點試圖被保護的痕跡。
Advertisement
廖宋站在原地那一分鐘,是真切地陷了茫然。
知道眼見不一定為實,但也不是這樣的。
不該是這樣的。他完全像是另個人,當然可以。可這樣的話,哪副面孔該信?
這種割裂讓廖宋恍惚。
一生所信,唯有真實。不怕真相殘酷不夠,只是要不被蒙不被騙。
“小宗,你先上去吧,我跟他聊點事,等會兒就來。”
廖宋沉默片刻,把牌子摘下來還給了他。
能預料到他們今晚不會談得太順利,但沒料到會那麼不順。
廖宋去了地下停車場,負三樓,他無聲跟在后面。
直到廖宋突然停下腳步。
“裴云闕。”
“我有多想問的,本來。但我現在,現在一時想不起來了。”
“就一個。你在裴氏,做的事……”
廖宋這些天輾轉反側,不得好眠,對方在電話里跟說了,裴氏會參與的事,件件目驚心,樁樁不像人事,讓廖宋自己去找他求證。知商場慘烈,但不包括這些。
有些底線任誰沾,被揭在下只有死。
想過要怎麼問出口,心間問了上萬次,不同措辭,臨到頭了,還是卡殼。
五個字,廖宋問得很難,輕得幾不可聞:“問心無愧嗎?”
裴云闕退兩步,沉默靠住墻角才站得住,神晦暗不明。
廖宋的視線期待地在他面上找答案,目殷切,仿佛那樣就能把答案勾出來。
“有別的問題麼?”
裴云闕最后抬了眸,很淡地笑了笑。
廖宋:“這算答案嗎?”
裴云闕抿了下,角的弧度變得很苦,但也只是一瞬,他飛快把這苦咽了回去。
今天抬頭看見時,裴云闕差點以為是幻覺。
那幻覺讓他手腳都凍住,不,就不會被推出幻覺似的。
穿著很上的淺,淺藕的修短袖,黑牛仔,手腕上套了個櫻桃頭繩,不知道是不是的,總之,很好看。
好像返回高中時代,眼里閃著一抹,但又是清清楚楚的現在的廖宋,篤定、懶散,強大。
只是,認出他的瞬間,廖宋從錯愕轉向失神。那點也消散了。
裴云闕心沉到了底。
廖宋是誰,無需點燃,自有蠟燭在心無窮無盡燃燒的人。沒有,至在他面前沒有出過這個神態。
那樣的震,一支支蠟燭被掐滅般。
他知道在問什麼,也知道自己在答什麼。
“算吧。”
廖宋仿佛頃刻間被卸了力,肩膀都有些塌了,眼一眨不眨盯著他,不愿錯過任何一細微表:“你知道你承認的是什麼嗎?刀被造出來,只有一個用,你知道嗎?”
裴云闕回凝視,淡淡道:“嗯。”
匕首鍛造來就是見用的。
廖宋看了他一會兒,了幾下眼睛,著著,把臉埋在手心里,失笑。
“你讓我活得像個笑話,裴云闕。真有你的。”
這個世界上,比殘酷的真實更殘酷的,是從頭到尾都活在虛幻里,卻全然無知。
這個世界上,也不存在絕對的良善,做惡的善良人,才能保護自己,不介意另一半是這樣的。
但不能……
不能只有惡。
廖宋沒想到,有一天會對地下車庫的構造這樣謝,不需要花多力氣說話,對方就能聽清。
“我無話可說。”
廖宋:“就當我們沒認識過。我樓下的人,不管你還是姓程的派的,撤走。”
很這樣說話,干凈冷淡到沒有半點多余。
裴云闕頭滾過幾滾,略有些艱地開口:“那是——”
指尖將將快到手背,廖宋直接甩開,干脆退后了一步,把所有可能的肢接統統躲了過去。
可以保護你。
他想說,卻沒能說出口。
整件事,他確實一開始就沒打算將牽扯進來。現在也不打算,確實沒什麼可以補充的。
廖宋:“滾。”
閉了閉眼,隨便指了個方向,聲線從來沒有這樣冷過。
“我不需要。我只需要你,從我面前消失。現在。”
裴云闕也是到今日此時才得見,廖宋決絕起來是這個樣子。
他有預,這一轉,可能就真的沒有以后了。
但他又手足無措到,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多像他們在海灘試過的,越地握住手中沙,沙就越快地落下。
“行,我走。”
廖宋笑了笑,冷漠到有些諷刺:“祝裴總前程似錦。”
沒有回頭,回家后大病一場。
許辛茹在醫院陪時,上廁所間歇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自稱姓程,要找廖宋接下。
許辛茹呸了一聲:“有完沒完,你自己說說,大家都雙邊拉黑的關系了,還煩什麼煩?你讓那個姓裴的有時間去長點人的心肝,宋宋也不會被氣到快掛了!那是人能有的臉嗎?裴云闕是不是把魂吸走了?”
“你轉告也行。最近會有人找麻煩,別讓接電話,看吧。”
那邊淡淡道:“最后一個問題,我還想問你呢。”
沒人樣是真的,行尸走一樣。不過,就這還知道找人回了趟廖宋送骨灰的地方,準破,把那繼父的破墓炸了。程風致算是看明白了,雖然炸了也沒讓他心好多,但至讓別人心更壞了。
許辛茹很久沒回應。
程風致皺了皺眉:“聽到沒?”
許辛茹僵在病房門口:“看不……會去哪?”
程風致還沒來得及說什麼,耳差點被刺穿。
“你大爺的你說得太晚了!!!!跑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6 章

不見面的男朋友
謝桃交了一個男朋友。他們從未見面。他會給她寄來很多東西,她從沒吃過的零食,一看就很貴的金銀首飾,初雪釀成的酒,梅花露水煮過的茶,還有她從未讀過的志怪趣書。她可以想象,他的生活該是怎樣的如(老)詩(干)如(部)畫。因為他,謝桃的生活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不用再打好幾份工,因為他說不允許。她的生活也不再拮據,因為他總是送來真金白銀。可她并不知道,她發給他的每一條微信,都會轉化成封好的信件,送去另一個時空。
33.7萬字8.18 24275 -
完結493 章

重生歸來,家里戶口本死絕了
前世,顏夏和顧家養女一起被綁架。無論是親生父母、五個親哥哥,還是青梅竹馬的男朋友,都選了先救養女,顏夏被撕票而死。重生歸來,和父母、渣哥斷絕關系,和青梅竹馬男朋友分手,她不伺候了。為了活命,她不得不卷遍娛樂圈。大哥是娛樂圈霸總。轉眼親妹妹開的明星工作室,居然變成了業內第一。二哥是金牌經紀人。轉眼親妹妹成了圈內的王牌經紀人。三哥是超人氣實力派歌星。轉眼親妹妹一首歌紅爆天際。四哥是知名新銳天才導演。轉眼親妹妹拍的電影票房讓他羨慕仰望。五哥是頂流小鮮肉。轉眼...
89.8萬字8.5 160248 -
完結244 章

一眼著迷
五歲那年,許織夏被遺棄在荒廢的街巷。 少年校服外套甩肩,手揣着兜路過,她怯怯扯住他,鼻音稚嫩:“哥哥,我能不能跟你回家……” 少年嗤笑:“哪兒來的小騙子?” 那天起,紀淮周多了個粉雕玉琢的妹妹。 小女孩兒溫順懂事,小尾巴似的走哪跟哪,叫起哥哥甜得像含着口蜜漿。 衆人眼看着紀家那不着調的兒子開始每天接送小姑娘上學放學,給她拎書包,排隊買糖畫,犯錯捨不得兇,還要哄她不哭。 小弟們:老大迷途知返成妹控? 十三年過去,紀淮周已是蜚聲業界的紀先生,而當初撿到的小女孩也長大,成了舞蹈學院膚白貌美的校花。 人都是貪心的,總不滿於現狀。 就像許織夏懷揣着暗戀的禁忌和背德,不再甘心只是他的妹妹。 她的告白模棱兩可,一段冗長安靜後,紀淮周當聽不懂,若無其事笑:“我們織夏長大了,都不愛叫哥哥了。” 許織夏心灰意冷,遠去國外唸書四年。 再重逢,紀淮周目睹她身邊的追求者一個接着一個,他煩躁地扯鬆領帶,心底莫名鬱着一口氣。 不做人後的某天。 陽臺水池,紀淮周叼着煙,親手在洗一條沾了不明污穢的白色舞裙。 許織夏雙腿懸空坐在洗衣臺上,咬着牛奶吸管,面頰潮紅,身上垮着男人的襯衫。 “吃我的穿我的,還要跟別人談戀愛,白疼你這麼多年。”某人突然一句秋後算賬。 許織夏心虛低頭,輕踢一下他:“快洗,明天要穿的……”
36.7萬字8 11823 -
連載332 章

禁止離婚!傅先生強寵小甜妻
認識不到兩小時,姜蔓便和傅政延領證結婚。 她爲了臨時找個地方住,他爲了應付家族聯姻。 婚後,姜蔓一心搞事業,努力賺錢,想早點買房離婚搬出去, 然而,傅先生卻對這小妻子寵上癮了, “老婆,禁止離婚!“ “我不耽誤你搞事業,你上班的時候,還可以順便搞一搞我~” 姜蔓這才知道,原來自己的閃婚老公,竟是公司的頂級大老闆! 公司傳聞:傅總裁寵妻無度,和太太天天在辦公室搞甜蜜小情趣~
58.4萬字8 3247 -
完結2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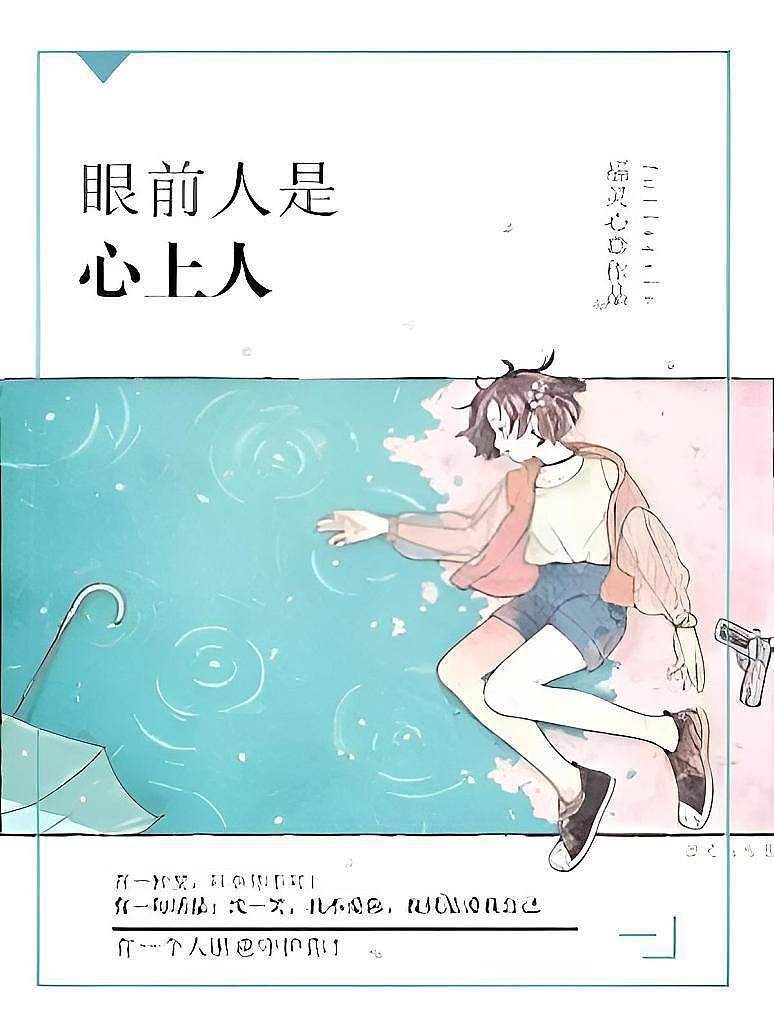
眼前人是心上人
巫名這兩個字,對于沈一笑來說,就是掃把星的代名詞。 第一次她不走運,被掃把星的尾巴碰到,所以她在高考之后,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離開。 卻沒想到,這掃把星還有定位功能,竟然跟著她來到了龍城! 本來就是浮萍一般的人,好不容易落地生根,她不想逃了! 她倒要看看,這掃把星能把她怎麼著。 然而這次她還是失算了。 因為這次,掃把星想要她整個人……
25.9萬字8 1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