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春靨》 第490章 一刻也離不開他
像暴雨前的悶雷轟然炸開,心跳聲一陣蓋過一陣。
的瓣上還殘留著那又涼意的。
阮凝玉怎麼也沒想到,謝凌竟會趁自己睡著的時候,對自己告白。
驚得睫抖了一下。
這點細小的靜,很快被近在眼前的謝凌察覺到了。
馬車上陷了詭異的寂靜。
謝凌的作停住,而是垂眼,目帶著探究,如有實質般落在了的臉上。
燭火在銅燈盞里明明滅滅,映得兩人疊的影子忽長忽短,他的睫在燭中投下細小的影。
他垂眸,看著榻上睡中的人。
“表妹可是醒了?”
阮凝玉合著眼,繼續“沉睡”下去。
等不到回應。
謝凌墨目里含著察一切的凜厲。
阮凝玉心跳快到要驟停。
接著,影搖曳下,阮凝玉聽到他手指過來時,擺落在邊上的靜。
他的長指拂開了落在眼上的青,如蝶翼掠過水面。
月過車簾隙灑進來,在他泛著冷白的指尖鍍上銀芒。
天暗沉,于是謝凌將幾上的金燈盞舉了起來,舉至臉前,不想錯過臉上任何一個細微的表,細細探尋。
他將金燈盞緩緩低。
正當他目要繼續探究時。
原本睡安寧的表姑娘卻突然握住了他的手。
“娘親,別…別丟下我……”
謝凌頓住了。
只見在鎏金般的暈下,隨著影流,的容也隨之無與倫比地發生變化,像是一幅巧奪天工的牡丹國畫,每個犄角都有著不一樣的。
只見表姑娘蜷著子,黛眉蹙起,眼睫發,纖弱的肩膀也止不住地發抖,在空中胡地抓住了他的手。
紅飽滿的瓣有些干,如同夢到了什麼駭人的妖怪。
Advertisement
“娘親,我好冷,好怕……”
“人不是我推的,我沒有陷害許姑娘,我不知道許姑娘們為什麼要這麼說,他們都不相信我……”
“是不是因為我出不好,所以連辯白的資格都沒有?”
淚珠大顆大顆地砸落在吹彈可破的臉頰上,如剝了殼的荔枝。
不多時,的睫,雪,,都沾染上了深淺得宜的水。
謝凌只覺心臟被狠狠攥住。
原來是做噩夢了。
他還以為。
可正是在夢中才會流出點兒脆弱來,才更讓他心疼。
袂翻飛間,金燈盞被擱在了幾上,謝凌已然將輕輕摟懷中,掌心著單薄的后背,能清晰到后背止不住的抖。
他的作帶著克制的心疼。
阮凝玉沒想到自己隨便裝一下,便能輕而易舉地騙過男人,更沒想到……他會將抱在懷里,如對待名貴珍寶。
阮凝玉的哭聲僵了一下,便繼續盡職地演了起來。
還好玩?
也沒想到,只是演了一下,便能讓這位鐵錚錚的男人共起來,都能聞到他上心疼的氣息。
于是阮凝玉素白指尖便抓住了他的襟,繼續跟小貓似地嗚咽起來,任由淚沾他的襟。
想到了許清瑤喜歡對他賣慘。
那也來裝綠茶,看誰能茶得過誰。
阮凝玉哭得更起勁了,還忘地代了,戲癮發作。
“我真的不懂,許姑娘為什麼要這麼說,是不是…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讓許姑娘討厭我了?只要許姑娘能平安,就算所有人都誤會我,我……”
泣不聲,像只他小時候養過的小兔子,無助又可憐。
但很快,阮凝玉就后悔了,發現裝綠茶、裝可憐的代價好像有些沉重……
謝凌結劇烈滾,看著睫上沾著的晶瑩淚珠,只覺呼吸都被走。
他那麼冰冷無的一個人,此刻竟將在懷中圈得更了,指腹輕輕去滾落的淚珠,他圈住了連贅都沒有的細腰,下抵著的發頂。
謝凌周寒意驟起,他垂著眼睫,不知在想些什麼。
頓時,阮凝玉徹底被他上的雪松氣息給包圍了,他因滿心自責,摟更的時候,阮凝玉能覺到自己的形是與他完全地合了起來,連個隙都沒有。
能覺到自己前的飽滿沉甸甸地在了他的膛上。
就像是引火自焚。
阮凝玉在他懷里僵了,不敢再了。
連哭聲都沒有適才那般起勁了。
還是……收斂些吧。
阮凝玉哭聲漸漸變小,最后消失不見。
謝凌垂目,便見表姑娘在懷里繼續沉睡下去,呼吸勻長,不再蹙眉。
他總算放下心來。
表姑娘在懷里抱久了,竟舍不得松開了。
這時車碾過路上凸起的碎石,車轅震了一下,謝凌抱著表姑娘順著慣向前傾。
須臾,表姑娘的額頭便撞在了他膛上。
謝凌忽然僵了。
燭火在琉璃燈罩里瘋狂搖曳,連同沉甸甸的也跟著漾,一同撞了過來,如同波濤洶涌,即使隔著冬日厚重的裳,亦能得出它的。
馬車的顛簸,連空氣都跟著泛起升溫的漣漪。
謝凌嚨微干。
他一時局促起來,想了想,自己為兄長,實在不妥,于是便溫地將放在了臥榻上。
而后,便當做什麼都沒發生。
眼見就這麼騙過了謝凌,阮凝玉松開了攥的手。
但是與他單獨相一室,還是到難熬。
最后,終于抵達了謝府。
謝凌醒了。
阮凝玉這才迷糊地“醒”了過來,支起子,傾瀉下來的青過他的手背,冰冰涼涼的,謝凌沒忍住,面無表,蜷了下手指。
“表哥,我們到了?”
眼見惺忪杏目里噙了水,月眉彎,梨云淺。
謝凌只覺得像被電了一下,眸微沉。
他撇開目,嗯了一聲。
二人很快下了馬車。
“醒”來后,阮凝玉其實是有些尷尬的,他不久前抱了,還在的上落下一個羽般的吻。
以至于讓此刻,有些無法直視冷淡矜貴的謝凌了。
兩人視線短暫地接了一下。
很快,謝凌就仿若前面沒有與吵過架似的,扶著下了馬車。
等雙腳落穩地面后,他迅速離,收回了胳膊,與保持距離。
阮凝玉沒忍住,看了他一眼。
有時候是佩服他的,沒想到他喜歡到了此等地步,竟還能這麼的會忍,仿佛能忍到死。
抱玉已經在府門那接了。
兩盞朱紅燈籠垂掛在府門檐角,斑駁門釘被映得忽紅忽暗。
阮凝玉回首,便對上了男人映著淡火的幽暗目,仿佛被燙到了一樣,很怕被他發現。
不過多逗留,“表哥,表妹先回去了。”
說完,轉便走。
眼見真的不知道馬車上發生了什麼事,謝凌停了下來,眉頭皺。
他有些失。
說不出來的失。
他無法抵抗,這種消極的緒恨不得能將他給淹沒。
明明在馬車上弱無措地握住他的手,一刻也不肯松開,還哭著他別離開……
在他懷里啜泣,撒,一刻也離不開他。
而醒來后,這一切仿佛從未發生過,看向他的目清明、平淡,又回到了先前。
謝凌恨不得能將眸里的冷靜盡數碎,憑什麼對這些什麼都不知道,只留下他一個人備煎熬,他寧愿在那時聽到了他那句晦吐的長告白。
他任由離開。
阮凝玉走之前,卻能察覺到他的目掃了自己的裾一眼。
心里留了個神,于是低頭看了眼上,什麼都沒發現。
謝凌不過是輕輕一掃,便能發覺形更滿了些,連寬松的冬日裾怎麼也遮擋不住,腰部以上隨著的走出若若現的弧度,轉看過來時,人的漣漪勾勒得更了。
他想到了馬車顛簸時撞在他膛上的。
謝凌眉擰得更。
猜你喜歡
-
完結232 章
腹黑郡王妃
一覺睡醒,狡詐,腹黑的沈璃雪莫名其妙魂穿成相府千金.嫡女?不受寵?無妨,她向來隨遇而安.可週圍的親人居然個個心狠手辣,時時暗算她. 她向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別人自動送上門來討打,休怪她手下不留人:姨娘狠毒刁難,送她去逛黃泉.繼母心狠手辣,讓她腦袋開花.庶妹設計陷害,讓她沒臉見人.嫡妹要搶未婚夫,妙計讓她成怨婦.這廂處理著敵人,那廂又冒出事情煩心.昔日的花花公子對天許諾,願捨棄大片森林,溺水三千,只取她這一瓢飲.往日的敵人表白,他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心,她纔是他最愛的人…
155.2萬字5 59507 -
完結752 章

盛世凰歌
擁有精神力異能的末世神醫鳳青梧,一朝穿越亂葬崗。 開局一根針,存活全靠拼。 欺她癡傻要她命,孩子喂狗薄席裹屍?鳳青梧雙眸微瞇,左手金針右手異能,勢要將這天踏破! 風華絕代、步步生蓮,曾經的傻子一朝翻身,天下都要為她而傾倒。 從棺材里鑽出來的男人懷抱乖巧奶娃,倚牆邪魅一笑:「王妃救人我遞針,王妃坑人我挖坑,王妃殺人我埋屍」 「你要什麼?」 「我要你」
132.9萬字8 10928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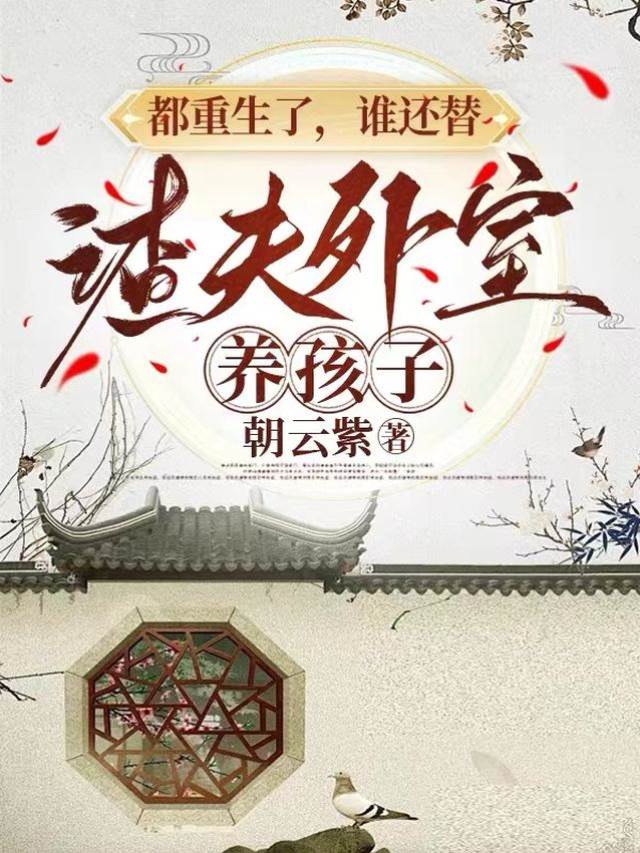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