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姐逼我做側房,重生二嫁上龍床》 第40章 玉足
裴寂自小算在馬背沙場上長大的,一些簡單的醫他都會,這等崴了腳在他眼中就是小打小鬧。
可傷的人不是他,也不是那些皮糙厚的下屬們。
他自覺沒用什麼氣力,只輕輕著手中的腳踝,就傳來幾聲哼唧的喚。
“疼疼疼,輕點,你會不會啊。”
裴寂眉宇間已經有幾分不耐了,偏偏一對上那雙淚目,便又低下了頭,著腳掌的手再放輕了些。
“腫了。”
“廢話,這還用你說,都腫饅頭了,是個人都看得出來。”
裴寂剛想說只是腫了并沒有骨折或是開裂,不過小傷,就被生生堵了回來。
的腳就搭在他的膝蓋上,他上所謂的新是被套上的,是件墨藍繡竹紋的長袍,本就骨勻稱白細,搭在那墨藍的袍上,更襯得那微微隆起的包有種目驚心之。
罷了,和子講道理,還是這等緒失控之時,哪有半點道理可講。
他一手托著的腳,一手挖出膏藥涂抹在那傷口。
膏藥冰涼,他的手掌卻是微微發燙的,讓下意識往后了。
不是疼,是太過刺激了。
但不等回去,就被著腳踝又給拖了回來:“別,還想不想要你這腳。”
他的手掌著的腳心,的腳竟與他手掌齊長,無比契合,另一只手作練地在那傷輕輕著。
Advertisement
疼自然是疼的,可衛南熏能分清他是故意在折騰,還是真心給上藥。
便咬下雙手,不讓喚聲溢出。
可即便知道是上藥,這樣的姿態還是太過親了些,即便是裴聿衍,也從來沒有過的腳。
許是藥開了,那疼勁也過去了,就變了微微發燙的覺。
一抬眼,便能看見裴寂低頭躬神態認真的模樣,他的睫很長,時仿若蝶翼,他側著半邊臉,可以看到那清晰的下頜線,以及微微抿著的。
他雖然不說話,還總是兇的,可作卻無比輕,讓衛南熏頭次覺到了安穩。
不再是仰著某個男人,而是有人愿意在面前低下那高貴的頭顱,兩人不再是上位者和屈膝者,他們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對他好,他也同樣回報。
就像是剛經歷過風雨的雀鳥,終于有了個可以躲避風雨的棲之所。
裴寂將的腳放下道:“好了,晚上再上一次藥,不要太過用力,休息兩日就能走了。”
衛南熏恍若夢醒,眼神飄忽地道:“這便好了?”
裴寂卻誤以為不相信他的判斷,擰了擰眉不快道:“不信我?”
“不,不是,只是覺得,快……”
太快了,居然有些依依不舍,恨不得他的手指再多停留久一些。
突然意識到自己在想什麼,衛南熏猛地臉紅起來,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啊!
這也太不知恥了點。
“我,我只是說你厲害,我…我該去用膳了。”
說著便要起,又忘了自己的腳還沒好全,甚至鞋都沒穿,一起就又撞在了他那結實的膛上。
裴寂真是被磨得半點脾氣都沒了,深吸了口氣,吐出兩個字來:“莫急。”
衛南熏本來是又又臊的,可不知怎麼的,聽到他略帶幾分無奈的莫急,突然間腦海里就浮現出他捧著書冊,搖頭晃腦像個老先生的樣子。
不有幾分好笑。
算了,為何要和一個自尊心強,迂腐又古板的書呆子計較那麼多呢。
他能放下自己的原則,為上藥就已經很不容易了,該高興才是。
衛南熏如此想著,就仰頭看向他,雙眼亮晶晶地道:“你不生氣了?”
裴寂無法直視那雙眼,太過明亮澄澈,烏黑的瞳孔里甚至映著全是他的模樣,怎有如此不害臊的子。
生氣?他有什麼可生氣的。
他不自然地移開眼去,卻看見了衛南熏懸在腰間的東西,目驀地一凝。
衛南熏還在等他說話,不想那只手卻徑直拿起了腰間的玉佩。
“你怎麼會有此?”
低頭去看,才想起來出門時帶著玉佩去換了條系繩,若不是中間來哄他了,早就拿回屋小心放起來了。
衛南熏一把將玉佩給拿了回來,十分珍重地護在手心里。
“不許這個。”
等把玉佩拿回來后,才聽清裴寂說的話,不免出了幾分詫異,他的反應為何如此大,看樣子似乎認識這個玉佩?
“你怎麼對我的玉佩如此好奇?”
“你的玉佩?”
裴寂將這四個字在齒間咬了咬,不免眉頭鎖,他的之何時變的了?
這塊玉是他打下第一個城池,砸了那狗屁皇帝的玉璽所制,那上面的寂字是他一筆一劃親自雕刻而。
他這些年偶爾會頭疼意識不清,老和尚說他是殺戮孽障過重,需要每隔些日子就去他的白云寺靜休調養。
此番便是前往白云寺的路上頭疼裂,他又不喜靜休之所被人知曉,未曾帶隨從,這才會被刺客襲落下了山崖。
許是心里作祟,他平日喜歡思考事的時候就一這玉,總覺得這塊玉可以替他一上的戾氣。
從丟了玉起,他的手便有些空落落的。
難怪之前怎麼也找不到,原來是那次掉在那了。
衛南熏被他盯著有些心虛,這是恩公的,并不是的。只是這輩子與恩公都再難相見了,留著恩公的東西也算是一些惦念。
“不是我的,難道還是你的?你為何如此張,難不是認得這玉佩?”
早就沒哭了,但雙眼還是微紅,被淚水洗滌過的雙眼,似乎更加澄澈干凈。
將他的一個是字徹底憋了回去,是了,他現在是季守拙不是裴寂。
這個玉佩又怎麼會是他的。
他輕輕地咳了幾聲:“不認得,只是覺得這玉極好,上面的字也刻得很好,且不似子之。”
衛南熏沒發覺他的不自在,聽他夸這玉好,跟著認同的連連點頭。
“算你有眼,這玉當然是極好的了,此雖不是我的,但它的主人對我很重要。”
裴寂揚了揚眉尾,詫異地看向。
就見衛南熏將玉佩寶貝地在了自己的心口,用很輕的聲音道:“重要到我可以用命去守護。”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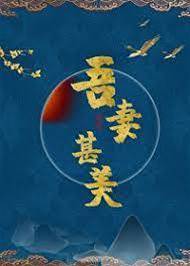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2238 章

天下第一妃
她,二十一世紀Z國軍情七處的頂尖特工,一朝穿越成為懦弱無能的蕭家廢物三小姐!未婚夫伙同天才姐姐一同害她遍體鱗傷,手筋腳筋被砍斷,還險些被大卸八塊?放肆!找死!誰再敢招惹她,休怪她下手無情!說她是廢物?說她沒有靈獸?說她買不起丹藥?睜大眼睛看清楚,廢物早就成天才!靈獸算個屁,神獸是她的跟屁蟲!丹藥很貴?別人吃丹藥一個一個吃,她是一瓶一瓶當糖豆吃!他,絕色妖媚,殺伐決斷,令人聞風喪膽的神秘帝王。當他遇上她,勢必糾纏不休! “你生生世世只能是我的女人!
411.7萬字8 36333 -
完結1065 章

新婚夜和離,失寵醫妃冠絕京城
醫學天才穿越成淩王棄妃,剛來就在地牢,差點被冤死。身中兩種蠱、三種毒,隨時都能讓她一命嗚呼。她活的如履薄冰,淩王不正眼看他就算了,還有一群爛桃花個個都想要她的命。既然兩相厭,不如一拍兩散!世間美男那麼多,為什麼要天天看他的冷臉?……“我們已經合離了,這樣不合適!”“沒有合離書,不作數!”就在她發覺愛上他的時候,他卻成了她殺母仇人,她親手把匕首插入他的心口……真相大白時,他卻對她隻有恨,還要娶她的殺母仇人!“可是,我懷了你的孩子。”“你又要耍什麼花招兒?”
177.9萬字8.18 12197 -
完結274 章

醜女絕色,瘋批暴君夜夜囚寵
前朝覆滅,最受寵愛的小公主薑木被神醫帶著出逃。五年後她那鮮少接觸過的五皇兄平叛登基。她易容進宮,為尋找母親蹤跡,也為恢複身份……一朝寒夜,她忽然被拉入後山,一夜雲雨。薑木駭然發現,那個男人就是龍椅之上的九五之尊……她再次出宮那時,身懷龍胎,卻在敵國戰場上被祭軍旗,對麵禦駕親征的皇帝表情冷酷無比,毫不留情的將箭羽瞄準於她……他冷聲,“一個女人罷了…不過玩物,以此威脅,卻是天大笑話!”(注:此文主角沒有冒犯任何倫理)不正經文案:……獨權專斷的暴君為醜女指鹿為馬,即便醜陋,也能成國家的絕美標桿!恢複真容的醜女:……那我走?——————種植專精小能手,從人人厭憎的“禍國妖妃”,變為畝產千斤的絕色皇後!
49萬字8 2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