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泰蘭德》 第1卷 第196章 他從沒在她眼里,如此具象過
昂威換了不眼的車,護送去了機場,那雙沉黑的眼一路都盯著窗外,但攥著的手,再無言語。
機場人群集,是他這樣份的人絕不可能進的,危險的地方之一。
幾輛黑轎車止步在路邊,緩緩停穩,前車后車的保鏢都迅速下車,站定車旁,按著藍牙耳機,警惕巡視四周。
下車他沒阻止,也沒告別,隨了的意,只派了阿努護送進去。
仿佛生著悶氣,又好似沒有,他總是這樣捉不。
進機場大門前,還是回頭看了一眼,那個人沒下車,也沒看,在墨車窗里,單手襯在窗框上一下下咬著拇指指甲,也不知什麼時候有的壞習慣。
單薄的影落在他剛毅英的側臉,臉廓卻模糊不見,仿佛再也看不清。
看到他打了個響指的手勢,那輛車緩緩啟引擎,駕著塵囂離去,也沒再回頭。
收回了淡漠的視線,同時也收回了心,轉朝著候機廳走去。
此時,看不穿也不揣,因為有更重要的事等著。
阿努一路領直到抵達VIP候機廳,說爺特意安排的。
黛羚站在門口,轉頭吩咐阿努,“你回去吧,還有半個小時,我在這里休息一會就登機了。”
垂下眼眸,還是補充了一句,“你跟他說一聲。”
阿努點頭,“好。”
在候機室的半個小時里,想了很多事,恍恍惚惚才憶起監聽查弄的事兒,抬手看手機,已經晚上十一點多,也許正是好時機。
N給的那枚小小竊聽芯片,容積不大,很大可能是通過無線信號接收訊息的類型,如果是這樣,電磁波的傳播在距離上就會到一定限制。
也就是說,一旦離開泰國,很有可能就沒法再接收任何信息。
Advertisement
不知道那枚竊聽在查弄上哪個地方,是否隨時都有可能離開他的,也不能保證還能聽多久。
所以,必須抓時間,就算五分鐘。
戴上耳機后,調試了一下,那頭的喧鬧聲便約出,試著調高了音量,電波的尖銳耳鳴刺了的耳,淡淡皺眉。
“這幾乎是目前亞洲市面上最好的冰糖,沒有再比這更純更好的貨了,不過老實說,降三,雖說也賺,但分到你我頭上,剩的就不多了,大頭都被上面了,這買賣不怎麼劃算啊,真搞不懂頭兒怎麼想的。”
一個男人抱怨的聲音,背景有音樂,還有打火機一下一下被打響的聲,清嚨聲,像極了夜總會之類的club。
聽到冰糖這個詞,幾乎一下就判斷出,他們聊的是什麼。
所謂冰糖,是黑話,其實就是冰毒,當今世界最恐怖最令人聞風喪膽的毒品,沒有之一。
看來這個查弄所謂的其他生意,是販毒。
“頭兒的想法很明顯,四海幫賭場遍布東南亞,如果能公然借太子爺的手,先把市場拿到手里,等他跟頭兒同一條船之后,都是同一條線上的螞蚱了,再談價不遲,說不定,還能一不做二不休,嘿嘿,玩個黑吃黑,直接取而代之。”
“你他媽當那個閻王吃素的,你別看他年輕,殺人不眨眼,比他老子還狠。”
......
黛羚的心猛地了一下。
場子里你一言我一語,但都很謹慎,沒有出現任何人的名字或代號,所以聽得云里霧里。
但四海幫和太子爺幾個字,卻聽得清清楚楚。
耳機尺寸不合,按了,眉頭也不自覺高聳。
“弄,太子爺這次這麼爽快的答應易,不會有詐嗎?”
另一個人接了話,“他們還不同意卸武進山,這要是干起來,我們能斗得過他們嗎?太子爺現在可是有自己的軍工廠,全泰國獨他一份,要是把咱們全圍剿了,也不是不可能啊,風險這麼大,玩得起嗎。”
有人笑,“你當頭兒也吃素的,他可是家的人,你想到的當他沒想到?”
沉默了一陣,有個年輕男人才開了口,聲音帶著輕蔑的笑。
“頭兒這回是在試探他,太子爺真上鉤好說,如果有詐,手下毒蟲都不要命,何況還有家的背書,量他逃不出五指山,你怕個。”
他沉聲囑咐一句,“頭兒都有打算,別多話。”
“弄,頭兒究竟何方神圣,說實在的,在座只有你見過真,大家真的好奇得厲害,有如此手段敢挑釁太子爺的人,整個泰國我怕除了軍方那幾位,應該沒幾個。”
查弄悶哼一聲,“這不是你們該心的事,做好自己的本分,別妄自揣測,下周先在清邁和太子爺了手探底再說。”
……
就在這時,機場廣播響起,猛然意識清醒,才意識到自己該走了。
匆匆收了耳機,走向機艙的每一步,心里都無法完全平靜,一直翻來覆去在琢磨著剛才那群人的對話。
頭兒?
清邁手?
堆山的疑問在的心底,沉重得要命。
縱然有很多不解和疑,直到落座,看著外面的夜,長吁了一口氣后,思緒才得片刻短暫的安寧。
這是他生意上的事。
告誡自己,不能管這些事。
管不著,也不到管。
飛機開始行,遮板全開,在即將上升的那一刻,瞥頭隨意地朝機艙外去。
那輛黑轎車,此刻穩穩停在跑道的圍欄外——
雖然很遠,卻那樣清晰可見。
倏地坐直了,單手在窗邊,想看得更清楚。
那個倚在車旁的影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越來越小,但清晰地記得,他今天穿了黑西裝馬甲,還有純白的襯衫,膛那樣寬厚。
他上那清新的剃須水味,和分別時沉黑的一張臉,還有抱時那冷徹骨的軀。
隨著兩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那個廓卻在腦子里放大,明晰,仿佛喚醒了已然刻在了腦子里關于他的一切。
忽然就憶起他上每一個孔,每一顆痣,每一塊傷疤,他睫煽的頻率,他獨特的氣息,弄脊背的修長手指,吻的時候那萬般呵護和溫。
還有他頻頻看向,那眼底不可言說的落寞之意……
他從沒在眼里,如此象過。
明明他們擁抱時,心隔得那麼遙遠,此刻真的隔了這麼遠,卻仿佛被捆在了一起,像烏云布的同時,又旭日高照,一切都奇妙得像了套。
一言不發,靜靜瞧著地面上的那個影。
他一如往常,著兜,悠閑地站在那里,形那樣迷人拔,就算隔得這麼遠也能看到他與周圍的與眾不同。
昂威抬頭看著這架飛機,視線隨著緩緩移,抬腳有一下沒一下地踢著面前的鐵圍欄,后散落著數個黑影,站得筆直,襯得他無比耀眼的白,那樣醒目,像特意為。
黛羚的視線也隨著他位置的變幻而轉,兩個人都同時遙遙看著對方,卻都沒找準那雙想看的眼睛。
直到再也看不見,脖子也酸掉,才不得不回了頭。
原來,他一直沒走,一直在那里等......
心里不知為何,還是刺痛了一下,閉上眼,努力平靜。
還好,擅長自我說服。
黛羚,醒醒。
……
緩緩睜開眼,仿佛才活過來。
花姐以前說的那句話,自始至終都縈繞在耳邊,時刻提醒。
自古就是利劍,偏偏斬的都是有一邊,就算參幾分他的心思,又如何能傻。
雙手十指攥得,也不知道自己幾時放松的。
也許是想到,這樣表面專的男人,實際上轉就投了別的人的懷抱。
結婚?跟幾個人說過呢。
扯了扯角。
飛機進平流層,開始平穩,兩個空姐竊竊私語,其中一位朝走來,禮貌蹲下。
“黛羚小姐是嗎?”
點了點頭,十指才緩緩松開,白印漸消,恢復了該有的。
空姐笑容很親切,一不茍的態度,“是這樣的,我們航空公司做機上活,中一位客人臨時免費升艙,可以升到頭等艙,您很幸運,恭喜。”
黛羚淺淺一笑,沒有拒絕。
但心里,怎麼不知道。
過分熱的待遇,還有機組人員落到上似有若無的眼神,視若無睹,著窗外漆黑的某,眼神凝固,沒了彩。
午夜紅眼航班,曼谷到香港的三個小時的飛行時間里,沒有踏實睡著過一刻,用眼神足足丈量了這約兩千公里的所有天際線。
猜你喜歡
-
完結1497 章

天才雙寶:傲嬌前妻抱回家
一場意外,她懷了陌生人的孩子,生下天才雙胞胎。為了養娃,她和神秘總裁協議結婚,卻從沒見過對方。五年後,總裁通知她離婚,一見麵她發現,這個老公和自家寶寶驚人的相似。雙胞胎寶寶扯住總裁大人的衣袖:這位先生,我們懷疑你是我們爹地,麻煩你去做個親子鑒定?
267.8萬字8 65089 -
完結100 章
萌妻迷糊︰第一暖男老公
他陰沉著臉,眼里一片冰冷,但是聲音卻出其的興奮︰“小東西,既然你覺得我惡心,那我就惡心你一輩子。下個月,我們準時舉行婚禮,你不準逃!” “你等著吧!我死也不會嫁給你的。”她冷冷的看著他。 他愛她,想要她。為了得到她,他不惜一切。 兩年前,他吻了她。因為她年紀小,他給她兩年自由。 兩年後,他霸道回歸,強行娶她,霸道寵她。
8.9萬字8 26664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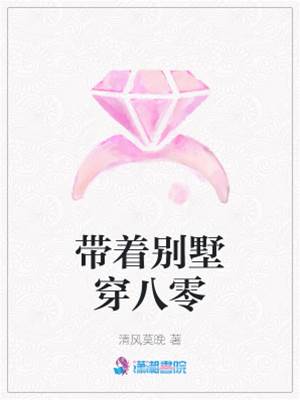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32 章

辣妻致富1990
身價千億的餐飲、地產巨亨顧語桐,訂婚當天被未婚夫刺殺! 再次醒來的她,發現自己竟然穿越到了生活在1990年的原主身上! 原主竟然跟一個傻子結了婚? 住進了貧民窟? 還在外面勾搭一個老流氓? 滿地雞毛讓她眉頭緊皺,但她顧語桐豈會就此沉淪! 一邊拳打老流氓,一邊發家致富。 但當她想要離開傻子的時候。 卻發現, 這個傻子好像不對勁。在
61.2萬字8 14929 -
完結921 章

一胎三寶:夫人又又又帥炸了
被設計陷害入獄,蘇溪若成為過街老鼠。監獄毀容產子,繼妹頂替她的身份成為豪門未婚妻。為了母親孩子一忍再忍,對方卻得寸進尺。蘇溪若忍無可忍,握拳發誓,再忍她就是個孫子!于是所有人都以為曾經這位跌落地獄的蘇小姐會更加墮落的時候,隔天卻發現各界大佬紛紛圍著她卑躬屈膝。而傳說中那位陸爺手舉鍋鏟將蘇溪若逼入廚房:“老婆,什麼時候跟我回家?”
229.5萬字8 73055 -
連載342 章

從摸魚開始成為學霸
【校園學霸+輕松日常+幽默搞笑】“你們看看陳驍昕,學習成績那麼優異,上課還如此的認真,那些成績不好又不認真聽課的,你們不覺得臉紅嗎?”臺上的老師一臉恨鐵不成鋼地
83.3萬字8.18 41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