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泰蘭德》 第1卷 第126章 帕爺的辦法,不如一試
回到曼谷是在兩天后。
那天晚上,在海湖莊園門口,黛羚只看到了坤達,諾執的影并未出現,心里不知為何落下一口氣。
“黛羚小姐,你沒事吧?”
翁嫂快步迎上來,接過手中的包,又彎腰遞上拖鞋。
的眼神里帶著一擔憂,言又止。
關于前陣子警署酒店發生的那件事,消息被封鎖得嚴嚴實實,只是偶然聽到坤達打電話時提到幾句,心里便一直懸著。
小Leo聽到主人的聲音,從二樓了個懶腰,一路喵著就跑下了樓。
黛羚搖了搖頭,似乎并不想多談。
小Leo翻了翻肚皮,細聲細氣地喵了一聲,用小腦袋使勁蹭的拖鞋。
看到小貓,忍不住笑了一聲,眉眼間的疲憊似乎也被這抹笑意沖淡了些。
“它最近吃得怎麼樣?”
翁嫂打趣,“它是吃得正常得很,貓能有什麼煩心事吶。”
言外之意,有人吃得不好。
“那個拉蓬,一看就知道不是什麼好東西。”
翁嫂一邊整理著桌上的茶,一邊低聲嘟囔著,語氣里帶著毫不掩飾的厭惡。
“阿船說他親眼看到他屢次對你手腳,膽大包天,死了真是便宜他了。”
房間里一時安靜下來,只有小Leo偶爾發出的呼嚕聲。
翁嫂似乎意識到自己說得太多,瞥了黛羚一眼,見神淡淡,便也不再繼續,只是嘆了口氣。
黛羚環視一圈周圍,著翁搜進進出出的影,盡量裝作隨意地提起了那天的事。
“翁嫂,Leo和阮夫人的關系怎麼樣……是不是不太好?”
的語氣里帶著一試探,“拉蓬是阮夫人的心腹,這次發生這樣的事,會不會對他們母子有不好的影響,如果是這樣,我心其實有點愧疚。”
Advertisement
翁嫂將一杯冒著熱氣的花茶遞到黛羚手中,神凝重,言又止,沉默了片刻,終于嘆了口氣,在黛羚旁邊的單人沙發上坐了下來。
“黛羚小姐,我們做下人的,本不能主家的事。”
低聲說道,語氣里帶著一猶豫,“爺算是我小時候帶大的,早已超越了主仆義,我了解他,他做事有分寸,雖然外人看來他是個混蛋頭子,但其實我知道,他從不干混事。”
黛羚捧著茶杯,指尖輕輕挲著杯沿,靜靜地聽著。
“爺小時候因為一次綁架了驚,老爺為了鍛煉他的心智,很小就把他送出國歷練,他和阮夫人之間相不多,沒什麼基礎,自然不親,做事也就理智些。但這次的事兒,確實是拉蓬不對,阮夫人沒有理由護著他,有可原。”
說著,手輕輕拍了拍黛羚的手背,語氣溫和卻堅定,“這件事,你千萬不要愧疚,和你沒關系,那人囂張已久,我早就聽說過,這個下場是他應得的。”
黛羚微微一愣,抬頭看向翁嫂,眼中帶著一驚訝,“綁架?Leo小時候被綁架過?”
翁嫂的眉頭了,像是意識到自己說了,微微俯,朝窗外瞥了一眼,低聲音說道,“黛羚小姐,多的我不能再說了,在爺邊,很多事知道得越越好,不然容易惹禍上,你要切記。”
沒有再追問,只是低頭抿了一口茶,溫熱的茶水過嚨,卻沒能驅散心底的那一寒意。
諾執和翁嫂的話像一把鑰匙,輕輕打開了的思緒。
昂威早就想解決拉蓬,這讓上那僅有的罪惡得到了極大緩解。
忽然意識到,自己或許只是這場博弈中的一枚棋子,而真正的棋手,早已布好了局。
當晚,四海集團的天大樓樓頂,夜風凜冽,城市的喧囂在腳下化作一片模糊的影。
昂威單手在袋中,站在停機坪的邊緣,指尖夾著一支煙,煙頭在黑暗中忽明忽暗,偶爾被他輕輕一彈,煙灰隨風飄散。
他的目穿夜,俯瞰著這半城的煙火,半城的佛,眼里仿若燈火盡頭,看盡鋼筋森林里眾生螻蟻的意味深長。
這萬丈浮華之下,藏著多骯臟的勾當,多見不得的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因為他也是這浮華的締造者之一。
夜風拂過他的面龐,帶來一涼意,卻吹不散他眼中的深邃與冷峻。
“爺,察邦總司令旁敲側擊攻了兩個月,幾乎沒什麼進展,正如帕爺所說,此人剛正不阿,簡直是金剛不壞之,難度極高,可能這也是歐紹文布局泰國這麼久,卻遲遲沒有拿下他的原因,所以,歐紹文只能退而求其次,轉而進攻五虎上將中的其他人,雖然他們的權力都不及察邦,但只要察邦沒有被任何人拉攏,再加上其他幾位的支持和庇佑,歐紹文幾乎可以所向披靡,無人能敵。”
“錢和人都試過了?”昂威挑了半邊眉。
坤達誠實回答,“無所不用其極,察邦是前總理西那瓦的侄子,背景本就顯赫無比,如今在泰國的地位更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厭惡攀龍附,對阿諛奉承嗤之以鼻,這樣的做派倒也說得過去。”
“金剛之軀?這世上哪有什麼真正的金剛不壞之,不過是還沒找到他的肋罷了。”
昂威微微瞇起眼睛,指尖的煙灰跌落半截,“接的過程份暴了嗎?”
“那倒沒有,但察邦這個人極其謹慎,邊的防護也滴水不,我們的人很難直接與他有集。基本上,還沒接近到他本人那一步,就被他邊的人攔了下來。”
昂威睨著夜,沉默不語。
坤達觀察著他晦暗的眼,還是開口說出了自己想說的,“爺,帕爺的辦法......事不宜遲,不如一試。”
昂威沒接他的話,目不斜視問他,“北邊的軍工廠和特區的賭場,進展怎麼樣了?”
“軍工廠已經接近尾聲,預計月底就能完工。魏榮那邊也已經將制造殲擊機的材料全部進口妥當,您放心,一切都盡在掌控之中。至于東盟特區的賭場,我們一直對外宣稱是酒店項目,目前滴水不,沒有走風聲,何況中國那邊的名義合伙人親自坐鎮,進展也十分順利,歐紹文安在紅鸞禧的眼線,就算再明,恐怕也突破不了我們設置的障眼法。”
昂威微微點頭,“嗯,到了關鍵時期要盯一些,別出任何差池。”
坤達揚了揚眉,“爺,印尼的拉查登、俄羅斯的鮑里斯,還有尼可爺那邊,你都已經打點妥當,我們現在就只等歐紹文這尊佛的作了,他一旦開始大行,我們也不會坐以待斃。”
坤達鷙地笑了笑,豎起大拇指,“你這一招布下天網,見招拆招,實在是高明,屬實佩服。”
“歐紹文不是等閑之輩,別高興得太早,掉以輕心。”
坤達收斂了笑意,鄭重地點頭,“是。”
“歐紹文現在還在國?”昂威揚眉。
“尼可爺那邊給他整了好幾個子,牽制得他彈不得,你大可放心,他現在應該焦頭爛額,在軍工廠完之前,他絕對回不來坐鎮。”
昂威微微頷首,目沉靜如水,卻著一難以捉的深邃,他沉片刻。
“備直升機,我今晚去一趟北邊,通知魏榮,讓他明天上午在軍工廠等我,就說有要事要談。另外,跟老頭說一聲,明晚我會去看他。”
坤達立刻應聲,“好,馬上安排。”
昂威轉,邁步向前,皮鞋踩在地面上發出輕微的聲響。
然而,剛走了幾步,他又突然緩慢地停住了腳步,像是想起了什麼。
“諾執那邊最近有沒有什麼反常的地方。”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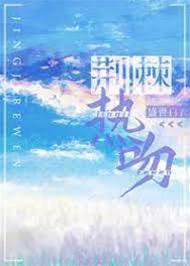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