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億萬老婆買一送一》 790
他的眸掃過的口,別有所指,安許諾的臉驀然紅了,眸浮起薄怒,口一陣起伏,這芯片一時無法藏在別,又知道短時間出不了酒吧的門,電火石間,為了避免搜索的危險,把芯片放在之,本該萬無一失,想不到,會被葉寧遠神不知,鬼不覺地拿走。
且他竟還敢出言消遣,分明是故意的。
狼!
葉寧遠笑意不減,車子下了高速,往山上開去。
山路崎嶇,彎道極多,一連有幾個三連彎,一旁就是峭壁,另外一旁是山崖,山勢險峻,安許諾一時不知葉寧遠到底要做什麽。
本以為路上沒什麽人,卻沒想到,偶爾有不轎車和托車從旁邊經過下山,心中不免好奇,這山上是什麽地方?
一路無話到了山頂,竟是一家格局高雅的天咖啡廳,名喚happy咖啡廳,咖啡廳外停了幾輛車子,天咖啡廳布置高雅,不遠的石欄上種植著幾株夜蘭,正開得燦爛,幽香盈盈,令人心曠神怡。天咖啡廳外還有一架鋼琴,有一名穿燕尾服的男人正在彈奏著貝多芬的名曲——致麗。
Advertisement
曲子彈得極好,天上一明月,輝點點,朦朧溫,繁星燦爛,夜空一片璀璨,許諾心中詫異,在倫敦,極能見到如此麗的夜空景,如此清晰的夜空。
天咖啡廳中零零散散坐著三對,一對青年的男子,都在低聲談,時而夾有笑語。
一聲口哨聲傳來,一名穿著白西裝,眉目俊秀,二十歲上下的年輕男子翩然而來,“寧遠,你怎麽跑上來了?”
“喝咖啡,小鐵叔最近好嗎?”葉寧遠笑問。
那男子回答道,“帶老婆去玩了。”
葉寧遠莞爾,詫異地看著一旁的安許諾,又吹了聲口哨,“哇,你什麽時候了個漂亮的朋友?”
他笑而不語,安許諾冷聲道,“我不是他朋友,你好,我安許諾。”
“咦,漂亮的小姐,既然你不是他朋友,那可以當我的朋友嗎?你看我一表人才,風度翩翩,學富五車,才高八鬥,再說我被小姐迷得神魂顛倒,你來當我朋友吧?”年輕男子出妖孽的笑容,癡迷地看著安許諾。
“無聊!”許諾沉冷了聲音,眉梢一挑,厲眸掃過他,“你們認識?”
“不巧穿著一條子長大。”年輕男子笑道。
“你話真多。”葉寧遠淡淡一笑。
那男子看看葉寧遠,又看看許諾,哈哈一笑,帶他們過去坐好,附耳不知在葉寧遠耳朵邊說了句什麽話,被葉寧遠敲了敲頭顱,笑著離開。
“這環境不錯吧?”
“你帶我來,就是要我陪你一起喝咖啡?”安許諾蹙眉,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聽到什麽,就喝咖啡這麽簡單?本以為他會刁難。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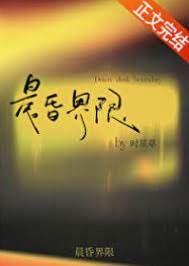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