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輩子被冷落的前夫,他不理我了》 第1卷 第九十五章 失控
屋只有一張榻,榻挨著窗,洶涌的雨點噼里啪啦濺在玻璃上。
他抱著,將人推到榻上,手到遙控,厚重的窗簾緩緩移,將暗沉的天和洶涌的雨關在窗外。
屋徹底陷黑暗。
他又按了下遙控,星空燈瞬間亮起,點點藍在雪白的墻面閃爍,既不刺眼,又恰好夠看清楚的臉。
他將按在榻上,著親,瘋狂掠奪屬于的氣息。
不知過了多久,他放開了,一只手臂撐著床微微抬起,和拉出大概五厘米的隙。
另一只手住尖巧的下頜,意味不明的著的瀲滟眼眸。
黯啞低沉的聲音在充滿曖昧氣息的空間里緩緩響起,“都分手了,你親我干什麼?”
半瞇著眼睛,剛剛的激烈緒還未平息,長發散在耳側,額頭的碎發被薄汗打,黏在鬢角。
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忽而勾著他的脖子微微近他,溫熱的氣息噴灑在他耳尖,沙啞著嗓子問,“親爽了嗎?”
Advertisement
他漆黑的眼眸越發深邃,猛的抓住作的小手,另外一只手按在窄薄的肩頭,將人按住,不許。
“岳寂桐,我的生日禮呢?”
這是見面以后,他第一次出的名字。
所有人都給他送了禮,只有沒有。
著他,眼睛仿佛裝著一池秋水,意濃濃。
“你的生日禮……”反握住他的手,輕輕一拽,按著他的手放到自己心臟,“在這兒呢。”
隔著輕薄的料,手掌心傳來的溫熱讓他手背繃起條條青筋。
將兩只極細的手腕疊在一起,用一只手握住,猛的舉過頭頂,嗓音啞的厲害,“想干嘛?”
瞇著眼睛,似狡黠的貓兒,角綻出一個清淺的笑,聲音清甜又勾人,紅輕啟,吐出兩個字,“睡,嗎?”
莫西樓扯出一個不屑的笑容,結卻狠狠滾了一下,心跳如鼓,“憑什麼和你睡?”
那雙卷著一池秋水般的眼眸微微睜大,意濃到仿佛要將他溺斃。微微拱起腰,領口敞開著,勾魂攝魄般問他,“確定不睡?”
他著,錮手腕的手驀的用力收,另一只手揪住本就微敞的襯領子,嗓音啞到極致,“確定要睡?”
“你好啰嗦。”嘟起,細眉微蹙,輕聲抱怨
他咬著牙,膛劇烈起伏,眼角猩紅,“睡就睡。”
揪著襯領口的手,猛然用力向外一扯……
白襯上方的三顆扣子崩裂,與地板撞擊,響聲清脆。
圓滾滾的扣子轉了兩圈,不知滾到哪個角落里去。
“你好暴力……”
他低頭埋在頸間,細急促的wen如窗外雨點般瘋狂落下來,一路向下。
失控……
一把將拉起來,下抵在肩頭,手環在背后,搗鼓半天,語氣頗為急切,“怎麼弄不開?”
“我自己來吧。”反手到背后,輕輕一推。
那一點點鐵的細小響聲,在他耳中仿佛八音盒開關轉的那一秒聲響,瞬間敲響了新的樂章。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狙擊蝴蝶
李霧高考結束后,岑矜去他寢室幫忙收拾行李。 如果不是無意打開他抽屜,她都不知道自己曾丟失過一張兩寸照片。 - 所謂狙擊,就是埋伏在隱蔽處伺機襲擊。 ——在擁有與她共同醒來的清晨前,他曾忍受過隱秘而漫長的午夜。 破繭成蝶離異女與成長型窮少年的故事 男主是女主資助的貧困生/姐弟戀,年齡差大
27.7萬字8 8157 -
完結521 章

錯惹惡魔總裁
洞房對象竟不是新郎,這屈辱的新婚夜,還被拍成視頻上了頭條?!那男人,費盡心思讓她不堪……更甚,強拿她當個長期私寵,享受她的哀哭求饒!難道她這愛戀要注定以血收場?NO,NO!單憑那次窺視,她足以將這惡魔馴成隻溫順的綿羊。
141.7萬字8 14730 -
完結169 章

盛寵之權少放過我
她千不該萬不該就是楚秦的未婚妻,才會招惹到那個令人躲避不及的榮璟。從而引發一系列打擊報復到最后被她吃的死死的故事。
45.5萬字8 11480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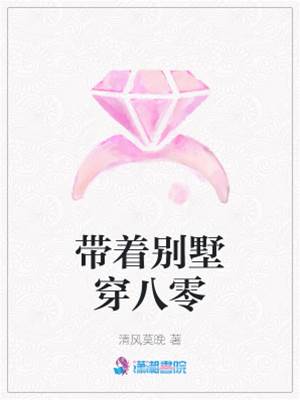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94 章

千億前妻帶崽歸來,馬甲藏不住了
江司妤和薄時宴協議結婚,做夠99次就離婚。 在最后一次情到深處的時候,江司妤想給男人生個孩子,不料男人記著次數,直接拿出離婚協議書。 江司妤愣住,回想結婚這三年,她對他百依百順,卻還是融化不了他這顆寒冰。 好,反正也享受過了,離就離。 男人上了年紀身體可就不行了,留給白月光也不是不行! 江司妤選擇凈身出戶,直接消失不見。 五年后,她帶崽霸氣歸來,馬甲掉了一地,男人將人堵在床上,“薄家十代單傳,謝謝老婆贈與我的龍鳳胎..”江司好不太理解,薄總這是幾個意思呢?
72.4萬字8 5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