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君同》 第34頁
到底面皮有多厚,眉眼有多冷,才能說出這樣可笑又卑鄙的話。還讓思考, 思考不出還要關,囚……隋棠呼吸急促而重,膛起起伏伏, 面一陣白過一陣, 很快如紙般脆, 整個人似散盡了力氣就要窒息不上氣,卻又在箍住面頰的五指松開的瞬間,牟足勁一口咬上了男人虎口。
是不要命發了瘋的一擊, 雙手死死攀住他那條臂膀,讓口的皮被咬得扎扎實實。
像一只備刺激后發怒的小,即便拼盡僅剩的力氣也要撕下對方一塊,也要讓他嘗一嘗苦痛,不許他如此得意猖狂。
說什麼不許離開府邸,還不許回家……好不容易才回的家
!
隋棠狠狠地咬著,齒間開始彌漫出淡淡的腥味。是他的,便更興了,扯著那點皮在兩排貝齒間磋磨,啃噬。
被啃咬的男人在吃痛的一瞬,那只手聚起力氣就要推開,但是這樣一推,勢必雙手骨折、下頜臼;他也可以用另一只手并指刀,一記手刀下去,當場便暈了。然習武之人被襲后的本能,這日在這個婦人面前被全部制。
藺稷看著脖頸突起的青筋,虎口愈發深刻的疼痛,半晌垂首吻過發頂,手背脊,容發泄。
原也沒有太久,那點疼痛就消散了,就剩一點力道撞擊在他膛。
隋棠被氣暈了,整個人綿綿下去,跌在一雙臂彎里。
也是這日暈厥后,隋棠許久不曾清醒過來。
林群說是了風寒,加之驚懼所致,引起了高熱。沒有大礙,但切不可讓高燒持續,恐影響了白上的塊。
聞“白”三字,藺稷難免生出幾分無力。但好在當夜隋棠用藥后發出一汗,有些退燒了。他松下口氣。
Advertisement
卻不料第二日凌晨時,高燒退而又起,至天明渾的溫度比之前更甚。藺稷推了政事堂的事,按照醫的意思,嘗試給以冷敷降溫。
長澤堂中提前燒起了地龍,烤得整間屋子干爽溫暖,如此剩小,掀開被褥也無懼著涼。
藺稷也不假以人手,皆親力親為。從銅盆擰干在溫水中浸的帕子,敷在額頭、頸部、腋窩。每隔一個時辰,便給更換一次帕子。
第三日晌午,雖沒有徹底退燒,但溫度稍降下些。只是人還是迷糊混沌,不甚清醒。藺稷不解帶地照顧。
第四日下午開始,恐長久冷敷適得其反。醫建議只拭便可。重點在耳朵后面和腋窩兩,以冷水涼帕拭,還是一個時辰一次。
涼帕拭降溫是有要求的,需在相關部位來回敷,以促進道散熱。本也可以躺著拭,但恐弄被褥,之后更換累寒。于是便都是藺稷將人抱起,圈在懷中進行。
耳后還好,藺稷給敷時,人很老實,除了一開始對涼帕的一點應激,其他時候都安靜垂著頭,在他口,由他擺弄。許是冰涼的帕子在滾燙,讓舒緩了些,道上又力道適宜,不是他膛便是湊向他握帕的手掌。
夜深人靜的夜里,病弱的婦人面紅,蹙的眉宇因郎君的細心照顧而微微舒展開來,濃的睫羽輕輕垂覆,落下兩道淡淡的影,的角概因子這一刻短暫的舒適而噙起了一點笑。
藺稷在琉璃燈盞昏黃的燈下看,或許是他的錯覺。
但有一點,他很肯定,便是在此時此刻,品到了一點耳鬢廝磨的味道。
夫妻兩世,到今日,他才頭一回用心照顧。
原也不是很好照顧的。
譬如給腋窩敷時,實在太過敏,本不得一點,抬起的手臂在帕子到腋窩時,瞬間便了回來,又是夾又是推開,鬧得被褥中熱氣全散了。強控,竟還會使出一些市井婦人的計量,又撓又抓。
藺稷垂眸看被扯開的襟口,驟然添出的兩道紅痕,還有下頸刮去的一點皮,在一些特殊時候且算了,說不定他還能心甘愿湊上去讓多撓兩下,但這會也太虧了。他將被衾拉來給人裹得只有一個腦袋在外頭,放棄了敷腋窩,只一個勁拭耳后。
……
第五日午后,隋棠的溫降下來;第六日晌午,徹底退燒穩定下來。人有些醒了,但是力不濟,人也疲乏,便依舊躺著不曾下榻。
這日晚間,藺稷沒有再來。
從白馬寺回來的這些日子,長澤堂寢侍奉隋棠的人,一直只有藺稷一人。以至于六七日過去,藺稷回來自己的臥房,人有些發昏。
直待用過藥,沉沉睡了一個下午,人才有些回神,握拳松掌間到幾分力道。其實以往行軍,幾天幾夜不合眼是常有的事。但自八月在鸛流湖傷后,他的力便遠不如從前,人也容易疲乏的多。且每每這等時候,他總會心悸,心口發疼。
已近日暮,林群給他切脈確定無礙后,正理藥箱準備離開。抬眼忽見他往左手虎口的傷疤上正在倒一味藥。
藥味刺鼻,林群眉心跳了跳,趕往上去攔下,問是何藥。
“董真怎如此大意,把這等藥給司空?”林群看清那藥,臉都白了。
藺稷手中拿著的是一瓶消蝕骨,如此灑在傷口上,以后疤痕難消不說,若是撒多了直接腐蝕皮,破敗得更厲害。
“這傷口不是你說咬得太深,十有八九消不掉了嗎?”藺稷撒了薄薄一層,然后又輕輕吹掉,只余些微末在上頭,從書案來折扇來回扇著,“董真說過這藥的利弊,我有數。”
藺稷瞧著傷口上已經不見末,稍有微微疼痛,便是已經吸收了,遂合了合眼道,“你拿走,反正我用得差不多了。”
林群難得失了禮數,抓來藥氣鼓鼓走了。
“等等,把外間那人傳來。”
藺稷還在看傷口,上面清晰留有兩排牙印,一排在手背,一排在掌面。他撐了撐手掌,手上繃,五指抻直,一時間不由皺了下眉。
虎口依舊作痛。
“還真是下死口咬!”藺稷暗自嘀咕,放松手掌,目如水脈脈,全部凝在上頭。不自覺抬首至邊,啟口吻合,齒間纏。
敲門聲是這個時候響起的。
“進來!”他的聲音還帶著落吻牙印時的低沉輕,然抬起過來的眉眼,已經如朝局里戰場上、如世人口中相傳的那般冷冽威。
蘭心不住他一眼,“噗通”跪了下去。
“七日了,還沒跪夠?”藺稷也不看,只笑笑道,“還是我醫醫不,良藥不良,沒有治好蘭心姑姑?”
自隋棠從白馬寺回來,藺稷便讓蘭心每日跪在他政事堂門口,一日跪四個時辰,每晚有侍扶回房,醫親去治療上藥。第二日再跪,再醫治,如此往復。
蘭心本不怕被罰,但怕被罰得不明不白。
尤其是梅節死了,也死得不明不白。
明明是護主而死,但是沒有恩賞,只有一卷草席丟去了葬崗。
“司空的醫自然是好的。”蘭心撐著起,額頭上冒出冷汗。
每日被扶回房后,已經侯在一旁的醫總會讓在兩個一模一樣的藥瓶中擇一味藥用以服。一瓶是培元補氣的藥,一瓶是噬骨腐筋的毒。若選到培元補氣的藥,醫銀針,便是極好的活散瘀的良方,跪了一日的雙膝頓時松泛不;若是擇了噬骨腐筋的毒,銀針落下,則當真是噬骨腐筋,痛苦不堪。
若是直接以這樣的毒磋磨,不住便可直接求死。然而偏偏還有一味藥實實在在可以讓過活,不僅是活著,還可,如此勾著。
有兩日在劇痛中求死,然目所及另一瓶藥,便生出無限。恨自己明明有機會,卻沒有好好選擇。明明有一條坦途就在面前,為何要走布滿荊棘的小徑?如果再給選一次,一定一定會選正確的那一條……
“醫好壞,藥優劣,其實全在姑姑一念之間。”藺稷把玩手中折扇,“原本我譴走你們,是因為知道你們的來路與意圖,我不想開殺戒。你們為奴為婢已然不易,還要枉做棋子,實沒必要。然又被我喚回,乃是因為殿下。為了殿下,我愿意請你們回來。可惜,你們想錯了路子。重回之際,可是覺得本司空正中下懷?”
蘭心面如紙,當日崔芳來請
和梅節回司空府時,太后與陛下確實是這般認為的。
“阿姊不錯,竟這般快住了藺稷的心。如此蘭心梅節前往,可為我們往來傳遞消息。藺稷乃正中下懷。”天子歡愉道。
“你們首要任務是服侍好長公主,沒有指令不可妄。”太后再三叮囑。
“既然司空大人如此清楚,婢子也無甚可再瞞的。但是我們并沒有收到指令——”蘭心忽得抬起頭,腦海中想起梅節素日時不時口無遮攔的話,“不,確切地說,是婢子至今不曾收到指令。”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84 章
冷王盛寵魔眼毒妃
一朝醒來,她不僅成了需要坐輪椅的殘疾人,還被替代胞姐扔進了陵墓陪著一個躺在棺木裡的男人,沒錯,她就是那個活人陪葬. 在這不見天日的陵墓中度過漫漫黑夜,一朝突然被匆匆換走,因爲帝王有旨,欽點她這個殘廢嫁給戰功赫赫的九王,其實只爲羞辱! 九王帶領千軍萬馬守衛邊關,戰績輝煌天下皆知.但某一天,聖旨下來,要他娶一個雙腿殘廢坐在輪椅上的女人.這是個偌大的羞辱,他暫時接受;不就是個殘廢的女人麼?和一件擺在角落裡接灰塵的花瓶有什麼區別? **** 然而,當做了夫妻後,才發現對方居然如此與衆不同! 這個打小混在軍營裡的九王有三好,成熟,隱忍,易推倒! 這個實際上根本就不是殘廢的女人有三毒,嘴毒,眼毒,心更毒! 火熱的生活開始,其實夫妻之間也是要鬥智鬥勇的. **** 紅燭搖曳,洞房花燭. 男人一襲紅袍,俊美如鑄,於紅燭輝映間走來,恍若天神. 走至喜牀前,單手拂去那蓋在女人頭上的蓋頭,眸色無溫的掃視她一遍,他的眼神比之利劍還要鋒利.審視她,恍若審視一個物件. 女人任他審視,白紙一樣的臉上無任何表情,眸子清亮,卻獨有一抹高傲. 對視半晌,男人拂袖離去,女人收回視線閉上眼睛。
99.9萬字7.54 45971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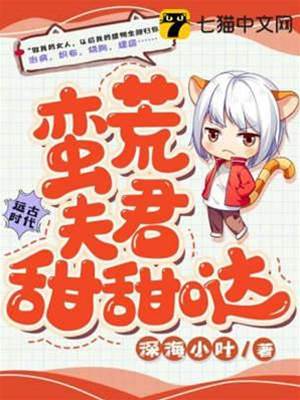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8714 -
完結347 章

穿越第一天,我逼婚了攝政王
整個京城都炸了鍋。 京城第一花癡草包沈驚鴻糾纏溫雅如玉的三皇子不成,竟然破罐子破摔,轉頭去逼婚了冷麵閻羅一般的攝政王! 更令人驚掉下巴的是,攝政王他、他居然還答應了! 面對或同情憐憫、或幸災樂禍的各種目光,攝政王蕭千決嗤之以鼻:「我家王妃的好,你...
62.9萬字8 29712 -
完結439 章
鸞鳳重華
重活一世,沈君兮只想做個坐擁萬畝良田的地主婆,安安穩穩地過一生,誰知她卻不小心惹到了一臉高傲卻內心戲十足的七皇子!“做我的皇妃吧!”“不要!人家還只是個孩子!”“沒關系,我可以等你……”這是一個關于青梅竹馬的故事……
81.2萬字8 15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