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險!太子爺他差點成為前夫哥》 第75章 小荔枝把三公子當鴨
棠荔睡飽後,舒舒服服地了個懶腰。
檀司煜應該一早上都在給按,現在腰也不酸,也不疼。
氣神十足,還能報複地一腳踹上男人的側腰。
檀司煜翻個側臥,抬眸睨:“又來勁了?”
“哼!”
盤坐在床上,雙手叉腰,氣勢洶洶地瞪了一眼男人,咬牙切齒:“檀司煜,這兩天發生的事我一輩子都不會忘的!”
男人趁機扣住的腳踝。
幹燥的掌心挲著凸起的踝骨,剮蹭得孩細膩的都泛起了點點紅痕。
男人下意識了。
他好迷,迷的一切,就連上的紅痕他都想。
檀司煜微微仰頭對上孩視線,角一勾:“一輩子都要記住我是怎麽你的嗎?”
男人起了點興趣,順著的踝骨一路往上,最後停在大側。
拇指稍微用力,白的便紅了一大片。
他整個上半都湊了過來,仰頭時銳利的結滾,得要命。
Advertisement
他半是玩笑半是認真地問棠荔:“那你要是忘了怎麽辦?”
棠荔咬,冷著小臉。
可不想再讓狗男人在跟前耀武揚威。
這一回,一定要扳回一局!
棠荔是忍住要落荒而逃的衝,雙手撐在床上,毫無預兆地前傾。
兩人的距離無限拉近。
再靠近一點點,鼻尖就會親昵地靠在一起。
可棠荔偏不。
這種似有若無的距離,偶爾一不小心上的鼻尖,又迅速分開,把檀司煜釣得死死的。
語氣矜,“當然不會忘了,到現在我都記得清清楚楚,你在我下的時候,哭得連眼尾都是紅的。”
棠荔嘲笑他:“哭鼻子小狗。”
檀司煜:“……”
“我們還是要有點分居的樣子的,我先回去了。這兩天謝謝你的招待,不過畢竟我們倆要離婚了,這種事算清楚比較好。”
棠荔語氣不慌不忙,可在理服的時候張得手都在抖,生怕這過程中檀司煜發瘋把拉住,摁在床上。
索檀狗很正常。
穿戴完畢,筆地站在床邊,拎著自己的小包包。
檀狗坐在床上,他上沒穿服,被子都掛不住,隻遮住了腰腹。
在外麵的肩膀與膛上,還殘留著的齒痕。
舊印未去,又添新痕。
曖昧惹眼。
棠荔匆匆垂落視線,在包裏翻找。
檀司煜開眼皮覷,“算清什麽,怎麽個算清?”
棠荔沒吱聲,默默往他被子裏塞了一張黑金的卡。
看喬檸和一個男人劃清界限的時候,就是直接甩錢的。
拿了錢,以後可就不許再說兩人有關係了嗷。
“沒有額度,隨便你刷,你覺得你值多錢,就刷多。”
低著頭,時不時瞄兩眼男人的神,見他沒什麽太大的表變化,才敢繼續往下說,“但是、你刷完要記得還我……”
不限額的卡就這一張。
要不是對方是檀家太子爺,才舍不得呢。
“嗬。”
檀司煜生生被給氣笑了。
他和他老婆睡,指人不提離婚呢。
合著他老婆當嫖他呢。
男人指間夾著那張薄薄黑卡,“大方啊,棠荔枝。”
棠荔無辜地衝男人眨眼,“就這樣,我走了,拜拜。”
趿拉上拖鞋,跑得飛快。
**
一樓玄關,檀小魚轉著圓溜溜的小狗眼看向棠荔。
一聲比一聲難過的嗚咽,像是在挽留不要走。
“小魚,對不起,媽咪沒能把你帶走,但媽咪也沒有不要你,你要是想媽咪的話,就用daddy的手機給我打電話,啊,媽咪會來看你的哦,就算和你daddy離婚也會來看你的。”
“嗷嗚-”檀小魚要哭了,牠跳起來,腦袋一個勁兒地往棠荔懷裏鑽。
棠荔丟開包,一把抱住檀小魚。
一人一狗,傷心難過得像是要麵臨死別。
後的二樓走廊,檀司煜穿著睡,雙手撐在欄桿上,眸垂落。
跟他老婆睡的人是他。
現在依依惜別的反而了那隻狗。
還有沒有天理了。
“棠荔枝。”
男人喊了一聲。
棠荔應聲回頭看去。
隻見男人趴在欄桿上,姿態懶散,隨意套上的睡,扣子都沒係,腹和曖昧的吻痕若若現。
裏還叼著那張黑卡。
活的浪勾人樣。
現在,棠荔真信了這男人在majesty學過勾引人的法子。
故作平淡地移開視線,嘟囔著:“也就一般。”
男人眉梢一挑,“都這麽晚了,要不留下吃個晚飯再走?”
一張,黑卡垂直落在一樓地上。
檀小魚耳朵了,飛撲過去,想接住黑卡——
牠嗅到了棠荔的味道。
檀小魚費力地咬起黑卡,叼給棠荔,邀功似的朝瘋搖尾。
“這是給你daddy的哦,還回去,小魚。”
檀小魚逐漸冷靜下來,尾都不搖了。
“然後,再幫我給你daddy捎句話,就說我不留下吃晚飯了,拜拜~”
得。
樓上的男人嗤了聲。
這會兒連話都不跟他講了,直接讓狗轉告他。
合著真把他當鴨了唄。
也不是。
他老婆對鴨好著呢,還會平白無故心疼沒業績的鴨呢。
怎麽就不知道心疼心疼他呢。
他連鴨都不如唄。
——————
北:疑似某人破防。
煜:誰?
猜你喜歡
-
完結1221 章

報告爹地:媽咪要逃婚
夏心妍嫁了一個躺在床上昏迷三年的男人,她的人生終極目標就是成為一個超級有錢的寡婦,然後陪著她的小不點慢慢長大成人。 「霍總,你已經醒了,可以放我走了麼?」 「誰說的,你沒聽大師說麼,你就是我這輩子的命定愛人」 一旁躥出一個小身影,「媽咪,你是不是生爸比氣了?放心,他所有的家當都在我的背包里,媽咪快帶上我去浪跡天涯吧」 男人深吸一口氣,「天賜,你的背包有多大,還能裝下爸比麼......」
193.5萬字8 13052 -
連載1504 章

夫人她A爆全世界
【甜寵,重生,虐渣,馬甲,團寵】“還逃嗎?”秦初使勁搖頭:“不逃了。”放著這麼好看的男人,她再逃可能眼睛真有病,前世,因錯信渣男賤女,身中劇毒鋃鐺入獄,自己最討厭的男人為替自己頂罪而死,秦初悔不當初,重回新婚夜,秦初緊抱前世被自己傷害的丈夫大腿,改變前世悲慘人生,成為眾人口中的滿級大佬。人前,秦初是眾人口中秦家蠢鈍如豬的丑女千金,人后,秦初是身披各種馬甲的大佬,某天,秦初馬甲被爆,全
135.4萬字8 16222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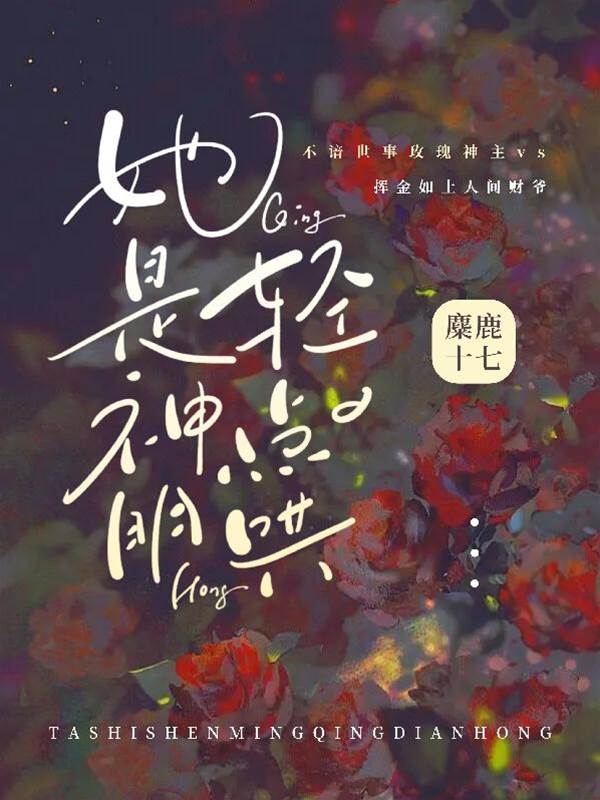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