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陰戾太子聽到心聲后》 第96頁
太子沉片刻,輕笑道:“自然是你的妻子告訴孤的。”
馮遇霍然起,死死攥著牢門,被火燒傷的半邊臉微微地搐著,“在你手里?你把怎麼樣了?”
連一旁的盛豫都面愕然。
據他所知,馮遇的妻子本就弱多病,二十年前聽聞他死在狼山,人悲痛絕,很快就病逝了,難道竟是沒有死?
也對,馮遇既然以盧槭的份活著,必然也要把妻子藏起來,否則豈不是輕易暴了份?
太子順著他的話道:“在孤宮中做客,若想讓命無憂,還需馮將軍配合。”
馮遇登時吼道:“你想知道的不是都已經查出來了嗎?當年一切都是我一人所為,與無關,你放了!”
太子似笑非笑:“所以,也是你給孤下了蠱毒?”
馮遇瞪大雙目,沒想到他連這個都知道。
他腦海中混地思索著道:“是……當年的蠱醫早已不在人世,天下唯有我一人能解,你若殺了我,蠱蟲會伴隨你一生一世,讓你這輩子都深折磨而死!你不能殺我……”
太子嗤笑一聲,“此蠱若對孤有用,今日孤在般若寺就該當眾癲狂失控才是,你想過是何原因麼?”
馮遇臉大變,“你解蠱了?不可能!今日我分明見你頭疾發作,那蠱蟲定然還在你上!”
太子道:“是還在,只不過孤邊有一子能為孤制蠱蟲的活,在孤邊不過半年,孤的頭疾從未發作過一次,便是你今日用了足量的香毒,對孤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
他的話,馮遇不得不信,否則今日在般若寺,太子如何能夠保持理智?
馮遇攥住牢門,手背青筋暴起。
盛豫聞言也多看了太子一眼,他口中的子,便是兒?
Advertisement
馮遇口中喃喃:“不,不會……蠱蟲只要不死,總有死灰復燃的時候,除非它死得徹徹底底……”
太子好笑地看著他:“難道你不知道,蠱蟲長久被制,失去活力,經年累月之下也會在自行消融。”
馮遇雙目圓睜:“不可能!”
他渾濁的眼球焦灼地轉著,損傷的面容極度扭曲。
「不會……那蠱醫說過,此蠱無藥可解,不死不滅,除非人在蠱蟲最為活躍之時將其滅殺于,否則將困其一生,直至人死亡……」
「如今他有那子在側,蠱蟲活躍不起來,便將永遠留在他顱,將來一旦到刺激,依舊能讓他發狂失控,痛苦而死!」
太子將他的心聲聽得一清二楚,方才不過是拿話誆他,果然套出了蠱蟲的解法。
他輕笑一聲,對牢人道:“孤還有事與尊夫人一敘,馮將軍好自為之。”
說罷轉離開,徒留馮遇在后拼命拍打著牢門:“什麼都不知道!你的蠱毒也只有我能解,只要你放了,我愿為殿下解毒!”
出了刑房,太子召來秦戈:“馮遇的妻子還活在世上,立刻去查。”
秦戈當即拱手領命。
太子又將方才所聽到的蠱毒解法告知何百齡。
又看了眼旁的云葵,道:“這段時日,你不能留在孤邊。”
云葵大致聽明白了,留在東宮,雖然能夠短暫制蠱蟲,卻不能徹底除,殿下需要在一定的刺激下,將蠱蟲激發出來,從而徹底滅殺。
可這種辦法也會讓他承極大的痛苦,并且要在失控的邊緣留一分理智,快準狠地將蠱蟲滅殺,否則極有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癲狂失控,而亡……
云葵心里擔憂不已,抖著嗓音道:“我……我還是得陪著殿下,我不進承殿可好?”
一旁的盛豫卻在這時突然開口:“不如,隨我回府住幾日,待殿下解除蠱毒,到時再……視況而定?”
殿眾人齊齊朝他看來。
第80章
云葵沒想到他突然開這個口, 下意識地攥了手指,“我……”
何百齡也有些不放心,“殿下從何得知這種解法?”
盛豫其實也疑, 方才太子不過是幾句試探,分明沒有提到蠱蟲的解法。
且那馮遇聲稱可以為殿下解蠱,大概率是將死之人拖延時間,想要以此威脅殿下,放了他的夫人,并未提到解法, 殿下又是如何得知?
太子面平靜道:“馮遇與淳明帝想要對付孤,不可能將那蠱醫留下活口, 此蠱無藥可解, 為今之計只有將蠱蟲引出來滅殺, 孤的頭疾才有可能徹底痊愈,否則終都是患。”
何百齡嘆道:“毒經中的確有這樣的記載, 只是風險太大, 殿下當真要嘗試?”
云葵也忙道:“我可以一直陪著殿下,不會讓殿下有事的……”
盛豫看著姑娘擔憂的表,心中暗暗琢磨這句話的深意。
說, 要一直陪著太子?
難不姑娘不想跟他回家,想一輩子在宮中當差?還是等殿下登基為帝,要留在后宮當娘娘?
太子凝視片刻,“我意已決, 不必再勸。”
只要蠱蟲還在,他永遠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哪怕只是一味最普通的香料,都有可能讓他發狂失態。
他肩負江山社稷, 要為萬民敬仰信賴的君主,也要給所之人一顆定心丸,賴以依靠的夫君至是個健康的人,無病無災,緒穩定,而不是隨時都在失控的邊緣。
云葵眼眶酸泛紅,強忍著落淚的沖。
曹元祿瞧瞧,又瞧盛豫,“那姑娘這段時日……”
云葵不想離開東宮,想隨時知道殿下的安危,更是從未有過跟盛豫回府的打算……
太子沉默片刻,道:“你留下,我有話同你說。”
這句話是對云葵說的。
殿眾人相視一眼,盛豫斂下詫異之,隨眾人拱手退了出去。
太子坐在榻上,朝招手,云葵這才乖乖地走到他面前,隨即就被他緩緩手,攬在懷中。
男人溫熱的氣息落在耳畔,就這麼抱著,沒有說話。
云葵低聲開口:“殿下,一定要解蠱嗎?我一直陪著殿下,也是可以控制的,殿下決意解蠱,萬一出了意外……”
太子道:“從前是不知道,如今知曉我有蠱蟲的存在,你不害怕嗎?”
云葵搖搖頭,“我早就不害怕殿下了,我只怕殿下有危險,怕你會疼,我留在東宮,隨時可以幫到殿下。”
“是,你可以幫我,”太子笑道,“可我怕蠱蟲才被引出來,又讓你嚇回去,如此反反復復,我還治不治了?”
云葵咬咬瓣,“那我回偏殿住,我可以忍住不來見殿下,就在偏殿等你的消息。”
太子了的鬢發,“可我忍不住想見你,怎麼辦?”
云葵心口仿佛塌陷下去一塊,泛起綿綿麻的痛意。
太子沉默片刻,問道:“你不愿意認他,不想跟他回府嗎?”
云葵低聲道:“我也不知道。”
盡管知道他也有苦衷,這些年過得不容易,可與阿娘的苦又算什麼?
就算他想彌補,阿娘的命也救不回來了。
而這些年跌跌撞撞地長大,從來沒有依靠過他這個父親,他對來說就是陌生人。
要隨他回去,與這個有名無實的父親同住一個屋檐下嗎?
太子道:“這段時日,東宮會很危險。”
今日浴佛法會上,他與淳明帝已經徹底撕破臉面,如今馮遇在他手中,淳明帝必然害怕他會供出當年狼山之戰的真相,要麼對馮遇先下手為強,要麼除去他這個太子,永絕后患。
至于盛豫,對淳明帝來說并非頭等要之人,盛府暫時還是安全的。
他笑了下,“今日你也見到了,他武功高強,對付一個錦衛指揮使都不在話下,自是能護得住你的。”
云葵想起在街上他從天而降的場面,的確是英姿卓然,俊逸非常。
這還是他四十往上的年紀,倒退二十年,不知是何等的神俊朗,難怪阿娘為了這個男人,不顧一切也要生下。
太子道:“你也是想見他的,是不是?”
云葵眼睫輕輕了,“可我不知道如何面對他,應該恨嗎?還是應該原諒,就這樣心安理得地接他給我的補償。”
太子道:“他只有你一個兒,不論是彌補過失,還是真真切切想要疼你,給你的一切,你照單全收便是,不管認不認親,這些原本就該是屬于你的東西。”
見沉默不語,太子又道:“你若不愿意,我也不勉強,這段時日,我會妥善安排你的住,派人保護你的安危。”
云葵攥手里的帕子,猶豫許久,終于小聲道:“他既然都那麼說了,還特意安排別作甚。”
太子“嗯”了聲,指腹的眼尾,“若是住得不習慣,或者不想認他,隨時可以回來,我說過,東宮便是你的家。”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9018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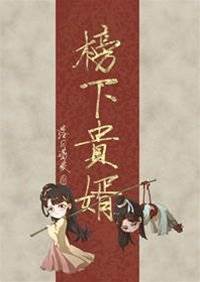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765 -
完結899 章
權寵天下:紈絝惡妃要虐渣
她不學無術,輕佻無狀,他背負國讎家恨,滿身血腥的國師,所有人都說他暴戾無情,身患斷袖,為擺脫進宮成為玩物的命運,她跳上他的馬車,從此以後人生簡直是開了掛,虐渣父,打白蓮,帝王寶庫也敢翻一翻,越發囂張跋扈,惹了禍,她只管窩在他懷裏,「要抱抱」 只是抱著抱著,怎麼就有了崽子?「國師大人,你不是斷袖嗎......」 他眉頭皺的能夾死蒼蠅,等崽子落了地,他一定要讓她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斷袖!
76.9萬字8 202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