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新婚》 第143頁
...
陸潯之在紀荷家這層的樓梯上坐了一夜,旁邊的垃圾桶里扔了一堆的煙。
他整晚清醒,泛紅的眼睛里帶著濃濃的疲憊。
從起初聽到那件事時的震驚、憤怒,與想去牢里把趙嘯給千刀萬剮的心在一晚上靜默的沉淀中化為了心疼,十五歲被孤立,十七歲被猥,紀荷出現在他面前時,卻是永遠都帶著溫的笑意,老天待如此不公,卻對所有事都充滿著善意。
這些年,究竟是如何熬過來的。
自般,一遍遍去地想象那幾年里紀荷的痛苦與絕,越去想,他的心就痛得無法呼吸。
攥著空煙盒的指尖漸漸泛白,陸潯之腦海里此刻只有一個念頭,趙嘯必須死,折磨至死,無論付出什麼代價,即使是把他自己的一生都賠進去也無所謂。
-
紀荷在清晨五點多的時候就醒了,嘗試再次睡無果后,起床洗漱,整理完今天外出購的清單抬頭一看才六點半,換了運裝,戴好帽子,準備出去晨跑。
站在玄關穿好鞋,吃著罐頭拌糧的大橘忽然跑過來蹭了的一下,并且朝著門的方向了聲。
Advertisement
心里奇怪大橘的舉,但保險起見,還是往貓眼里看了看。
外邊沒人。
彎下腰安地了大橘的腦袋,然后開門出去。
大橘看著關上的門,又喵了幾聲。
它從昨晚就聞到了門外有悉的氣味,是它和大白日思夜想的“凍干”!
紀荷去按電梯時發現安全通道那邊的窗是開著,冷風吹進來,裹挾著淡淡的煙草味,驚了下,大橘不會無緣無故就,難道剛才真的是有人在這里嗎?
壯著膽子慢慢往安全通道的門口走,在探頭往樓梯間看的一瞬間,整張臉都生了起來。
“你怎麼在這里,很嚇人。”
陸潯之也沒料到紀荷會突然出現,他先是愣了下,眉眼里的鷙迅速消散,有些意外地看著紀荷臉部的表,隨即想起了什麼,馬上拿起臺階上的帽子戴上,用力往下,嘶啞著嗓音說:“我早上路過,順便上來看看。”
“你傷了嗎?”紀荷走進去,瞥了眼垃圾桶上那一堆煙,怕是昨天晚上就來了。
停在陸潯之面前,呼吸間都是他上清寒的氣息。
雖然他極力想掩飾,紀荷還是看見了他額頭上的繃帶和蒼白的臉。
陸潯之抬眸看,一的運裝束,氣看起來倒是比昨天好了很多,“撞門上了,你出去跑步?”
“嗯,”紀荷把鑰匙給他,也不問阿蒙那晚講得出差是怎麼回事,“你進去洗澡休息會兒,關于離婚的事,我覺得我們還需要通。”
陸潯之上一秒還在高興紀荷的前半句話,一聽后半句頓時就不想接那串鑰匙了,“我陪你一起跑。”
紀荷不由分說地把鑰匙塞往陸潯之手里塞。
手卻被他順勢握住。
直覺告訴紀荷,要不是因為他了整晚的煙,他一定會抱住。
看了看他瘦削的下頜,再迎上那雙漆黑深邃浮著紅的眼睛,心口猛地了下,輕輕地嘆了口氣,“你的手很冷,進去吧。”
陸潯之握那只纖細的手片刻,最終,還是慢慢松開,紀荷轉,他立即起,坐著太久,猛地一下站起來不太適應,往前趔趄了下,緩過來后大步走出去。
進電梯,他努力克制著自己想進去的沖,眼睜睜看著電梯門緩緩關上,直到看不見紀荷的臉。
-
紀荷沒看時間也沒在意跑了多遠,著氣跑跑停停,這個時間點,路上的早餐鋪子都營業了,蒸包籠一打開,白煙霧裊裊升起,在被涼意籠罩著的秋日清晨滲出一暖意。
原地平復好呼吸后往人多的那家去排隊,最后是要了兩杯豆漿,兩個叉燒和兩個蔬菜包。
付完款,想把手機放回挎包里時,震了下,進來了條短信,點開,看完容后愣了許久。
陌生號碼:[好像我的出現又給你的生活造了麻煩,很抱歉,欠你的,也許我這輩子也還不清了。陸潯之做事果然雷厲風行,我今天要離開北京了,并且不會再回來。他那天狠狠打了我一頓,我心甘愿著,就當是償還你因為我而承的痛苦的千分之一了。紀荷,對不起。也祝你幸福。]
紀荷從電梯出來,手剛放在門鈴上想按,門就從里面打開了,看著陸潯之上略微有點的黑和牛仔,疑他這是從哪里找來的。
陸潯之微揚,“在書房柜子里,尺寸像是紀述的。”
這樣一講倒是記起來了,紀述去年有次和隨士吵架,離家出走在的書房里睡了一個星期。
紀荷走進去,把早餐放在客廳桌上,然后回臥室洗澡換了服。
出來一看——
......陸潯之又在喂貓吃凍干了。
有些無奈,但看著大白大橘那的眼神又不好再去阻止,坐到沙發上開始吃早餐時,看見了臺那盆郁郁蔥蔥的發財樹。
昨晚送紀述回去后去花店買了好幾盆綠植,但搬到臺后就沒力氣管了,連樹罩都沒取走。
視線還落在臺,咽了口豆漿后了陸潯之過來吃早餐。
兩個人安靜地吃著。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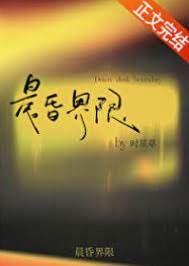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