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笑一下唄》 第1卷 第17章 等我病好,任君收拾
飯后,季云白開車給時銳三人送回學校。
杜若陪著徐京墨去醫院掛水。
到了醫院,門診護士先給徐京墨測了溫。
40度,屬于高熱。
又拍了CT、做了常規等檢查,排除肺炎染和病毒染,只是簡單的流,才開始對癥下藥。
醫生開了些退燒藥,又囑咐了一些注意事項,建議他回家休養。
自從新冠病毒出現以來,醫院發熱門診的病患每天都數量眾多。
復的、甲流乙流的…,床位張,空氣流通還不好,普通的流病患,一般都不收,留下來也容易叉傳染。
徐京墨和杜若便又回了家。
到家后,杜若拆開藥盒,仔細閱讀了說明書后,將藥片逐一挑出,遞給徐京墨:“把這些吃了之后,去睡覺捂汗吧。”
說完又突然踮腳了下他的額頭,覺比剛剛又燙了幾分,盯著他滿眼驚奇,“你應該把溫度計的度數發個朋友圈,燒到40度還能像你這麼鎮定自若的,也是罕見。”
徐京墨接過藥片,笑道:“夸我還是損我?”
杜若:“佩服你。”
護士說,免疫系統差一點的,高燒到40度一般都乏力,頭暈目眩、渾發冷了。一問徐京墨的癥狀,就是---有一點點難。
也是6。
徐京墨吃完藥,便走進次臥,準備換睡睡覺。
杜若整理好藥盒,發現袋子底下還有一盒退熱,便拿著退熱跟著走向次臥說:“退熱你也上吧,雙重效果,能好得快…”
剛剛推開臥室門,就頓了一下,“一點兒…”
只見徐京墨剛剛完上,此時正背對著,寬肩窄腰,背部線條流暢分明,豎脊的背如壑一般深邃,自上往下長長地蜿蜒至腰邊緣,引人遐思。
Advertisement
徐京墨聽見的聲音,轉回頭。
杜若又清晰地看見他結實致的和廓分明充滿力量的腹,甚至暗嘆的思維反應過于敏捷,竟然一眼就看出來是六塊腹。
這還是杜若第一次這麼直觀的看見男的軀,難免好奇,目不由自主地多瞧了幾眼。
徐京墨被這直白又毫不掩飾的打量視線看得心里一熱,手將剛剛下來的T恤扔到頭上,蓋住了的視線,迅速地穿上睡,低聲問道:“好看麼?”
杜若扯下頭頂的T恤,上面似乎還殘留著屬于徐京墨的炙熱溫和淡淡的松木香,應該是洗的味道,還好聞的。
杜若如實評價:“你材好的。”
線條流暢、飽滿又不夸張,符合的審。
“謝謝夸獎。”徐京墨系好睡紐扣,被氣得開始怪氣。
杜若若無其事的走進來,將退熱遞給他,向他復述看過的醫囑,“退熱可以在額頭、頸部、腋下、腹…”
念到此,杜若停頓了一下,腹是哪兒來著…
剛要往徐京墨上掃,徐京墨突然作迅速地用手遮住了的眼睛。
這個突如其來的作嚇了杜若一跳,不設防地想向后仰頭躲開,卻踉蹌了一步,差點跌倒,被徐京墨眼疾手快地用另一只手抓住的胳膊扯回來,杜若又因慣,撞上他的膛。
鼻尖猛得一酸,還失去了視線,杜若本能地保護自己,抬手想要推他。
隔著薄薄的布料,的右手掌心下是徐京墨急促紊的心跳,左手則到了他那堅而有力的線條,十分特殊的,杜若推人的作一頓,愣在原地。
兩人得很近,徐京墨上的滾燙包圍著,杜若覺得自己好像被火爐炙烤著,臉上熱得慌,心里好像也熱得慌,奇奇怪怪的覺卷土重來。
只是短暫的一兩秒鐘,兩人誰也沒說話,誰也沒撒手。
徐京墨很猶豫,既害怕自己不控的心跳暴自己的心思,又舍不得眼前如此親的距離,沒推開他。
徐京墨結輕輕滾,垂眸看了眼杜若白皙的脖頸,忍住想低頭親下去的沖,啞聲問:“好麼?”
杜若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明明徐京墨上穿著睡,的眼睛也被蒙住了,但是此時,手下的莫名跟剛剛看見的曲線重合在一起,自浮現在腦海里久久不散。
都怪記憶力太好。
徐京墨話音一落,杜若就迅速回神,本往后退一退,又覺得他說的話好有歧義,這是不小心到了,又不是故意他,剛這麼想著,左手就不由自主地沿著線條廓了下。
杜若:……
死手!你聽話啊!手!
霎時間,徐京墨形都變得僵一般,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把的手臂抓的更了幾分。
杜若強裝淡定地抬手攥住他的手腕,移開他的左手,又輕輕甩開他的右手,往后退了兩步,給出評價:“好的。”
徐京墨目沉沉地盯著,薄抿一條直線,無形中讓人覺得有些威,就像是一匹伺機而的狼,隨時會撲上來咬人一口。
杜若卻泰然自若地就那麼迎著他的視線,毫無反應,實在心里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只要我足夠淡定,你就奈何不了我。
兩人目匯了幾秒,徐京墨率先別開了視線,往上提了提睡領口,轉輕哼道:“好也不給你。”
杜若:“……”
切,誰稀罕。
徐京墨坐到床上,打開一個退熱在自己的額頭上,見杜若還站在門口沒走,在那靜靜地看著他。
徐京墨心里莫名躥出一火,他真的要被那單純又充滿好奇的眼神氣死了。
氣無形中的瞎撥他,氣自己本無法淡定自如地面對。
隨便的一個眼神、一個作,都能輕易地牽起他的心緒,勾的他無法自拔。
心里明知道不是故意的,卻仍讓他忍不住想非非。
或許他有機會呢?
要不要一下?
本不知道他腦袋里想的都是什麼齷齪的心思。
他也不敢試。
這種事,對他來說,承擔不起試錯的后果。
或許是氣急攻心,徐京墨燒的腦袋也不清醒了,口無遮擋地說:“還站在那干嘛,想看我怎麼腹?”
“……”
杜若視線下移掃了一眼,后知后覺地察覺到了那個位置的尷尬。
杜若突然覺得自己在耍流氓,好像在調戲良家婦男,什麼時候還有這種齷齪的好了?
有些心虛,可一想到面前的人是徐京墨,沒理也變得有理了幾分。
跟誰倆呢,還敢板了。
幾年不見,忘了自己的江湖地位了。
杜若作十分自然地倚在門框上說:“想看啊,讓看麼?”
徐京墨面一黑,起扳住的肩膀,將轉個面,推出門外,氣道:“不、讓!”
他就是這麼完蛋,敢看,他不敢讓看,生怕自己會當著的面起反應。
杜若心里輕笑,面上不顯。無所謂地聳下肩,上不饒人地說:“小氣鬼。”抬腳就朝客廳走去。
剛踏出次臥一步,又突然被徐京墨攥住手腕猛得扯回去,兩人的再次狠狠撞到了一起。
只不過,這一次,杜若沒來得及用手隔開,兩人的膛在一起,心臟一上一下劇烈地跳著,寂靜中,分不清誰的更加急促、更加震耳聾。
杜若抬眸看著他,心里沒來由地有些張。
已經好幾次了,那種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的緒,自從回國后,出現了好幾次,不知道是為什麼。
“拉我干嘛?”杜若盯著徐京墨深不見底的黑眸問他。
徐京墨目幽深地注視著,盡量保持語調輕松,半開玩笑地說:“杜若,你知不知道生直勾勾地打量男人材,對男人來說,算是調。”
杜若眼眸微微睜大,是慌,他該不會以為想故意調戲他吧??
雖然是故意的,但不是那種故意的!!!
靠!冤枉啊!
杜若連忙甩開徐京墨的手,跟他拉開距離,一副你別瞎說的表。
徐京墨姿慵懶地倚在門口,老神在在地看著,笑著說:“你想跟我‘調’也就算了,我又不能怎麼著你,換個人都得欺負死你。”
杜若不屑道:“誰能欺負得了我?”
徐京墨輕揚眉梢,點頭附和,“也是,誰也欺負不了你。”
說著,他又突然向前,微微彎腰,直視的眼眸,放語氣說:“那你能別欺負我這個病號麼?”
杜若沒來由地慌了一瞬,一掌推開他的腦門,“我怎麼欺負你了?”
徐京墨不破,看著破防松的表,已經很滿意了,輕笑一聲,轉進屋,臨關門前,還故意說了句:“我要退熱,你別看哦…別欺負我這個良家男…”
“徐京墨,你是不是欠收拾了!”杜若氣的咬牙。
“等我病好,任君收拾。”徐京墨朝眨了下眼,在杜若揍他之前,連忙關上了門。
猜你喜歡
-
完結114 章

豪門老公破產后
阮顏從二十一歲大學畢業之后就嫁入豪門成功產子,過的是無憂無慮的闊太生活,誰也沒想到二十七歲這年,風云變幻。 她那位被稱為商業金童的總裁老公居然賠的連條褲子都不剩了。 一家三口身無分文被趕出來好不容易租到了房子,阮顏才發現了最大的問題,她看了一眼手里牽著即將入學一年級的小豆丁,懊惱道:“完蛋了,幼小銜接班還沒報!孩子讀一年級怎麼辦?” 尤其是小豆丁連拼音都認不全…… 看文提示:1、女主前期就是靠著美貌生子上位,介意請莫點。 2、本文多會描寫幼小銜接教育課文的事情,比較細水長流,旨在讓大家了解孩子多麼需要家長陪伴。 3、適當狗血,增加戲劇性,大家莫介意。
26.1萬字8 9241 -
完結1747 章
千億總裁寵妻成癮
出現部分章節有空白問題,請大家在搜索框內搜索《千億總裁寵妻上癮》進行觀看~ —————————————————————————————————————————————————————————————————————————————————————————————————————— “老公,快來看,電視上這個男人長得和你一樣帥!”在電視上看見和自己老公一模一樣帥的男人莫宛溪非常驚訝。賀煜城扶額,“你確定他隻是和我像?”“不對,他怎麼和你一個名字?”被惡毒閨蜜算計以為睡了個鴨王,誰知道鴨王卻是江城最大的金主爸爸。天上掉餡餅砸暈了莫宛溪,本來是爹不疼,四處受欺負的小可憐,現在有了靠山,整個江城橫著走。
318萬字8.33 462778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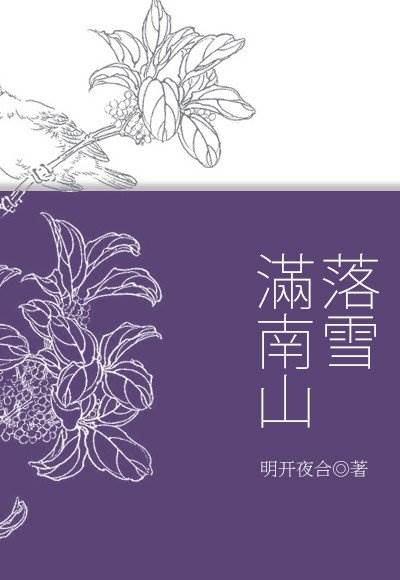
落雪滿南山
[小說圖](非必要) 作品簡介(文案): 清酒映燈火,落雪滿南山。 他用閱歷和時間,寬容她的幼稚和魯莽。 高校副教授。 十歲年齡差。溫暖,無虐。 其他作品:
18.5萬字8 2384 -
完結296 章

心尖蘇美人
當一個女人獲得經濟獨立,事業成就。 男人就只是調劑品,周啟萬萬沒想到,他會栽在她手里,一栽幾年,食髓知味欲罷不能。 蘇簡拉開抽屜,看著里面的九塊九以及一張紙做的結婚證書&”&” 周啟扯著領口,低笑:“這什麼東西?誰放這里的?” 蘇簡默默地把它們拿出來,道:“扔了吧
42萬字8 98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