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婚后我高嫁小叔,太子爺你哭什麼?/刺激!未婚夫成了前任小叔》 第1卷 第192章 在你眼里,我連呼吸都是錯的?
保镖也不傻,要是今天帮了苏以柠拿了这小钱,来日司北琛然大怒,可不是他们小小一个保镖就能顶罪的。
什么契约神?大难临头夫妻都各自飞自己的,他们哪里还管得了别人。
苏婉禾直接从包里拿出支票,分别写了两百万给两个人。
“你们不伤害我对我来说有恩,放心,我一定不会报复你们的。”
“谢谢苏小姐。”
苏以柠也没想到苏婉禾现在出手这么大方,就算是也舍不得拿四百万给两个什么都没做的陌生人。
“所以麻烦你们帮我请苏小姐跪在我母亲的墓碑前,好好地将这些排泄给干净。”
两人听到这个请求,也害怕得罪了苏家,便立马拒绝,“苏小姐很抱歉,我们还是有职业道德的,不可能为了钱就背叛旧主。”
苏婉禾又低头写了两张支票,“每人再加一百万。”
放到以前也不会这么大方,最近司北琛给的太多。
区区几百万就能让出一口恶气,提供很好的绪价值,何乐不为呢?
Advertisement
两人立马改口:“既然苏小姐你这么有诚意,那我们就勉为其难同意。”
每人三百万呢!
这比抠抠搜搜的苏以柠不知道好了多倍!
眼看着他们朝着自己走来,苏以柠也没想到到的鸟不仅飞了,而且还变了这样的后果。
“住手,我给你们钱,你们别……”
“钱?听说苏家最近资金链断了,你能拿得出六百万雇人?苏小姐,别怪我们了,这是你自作自。”
另外一个保镖道:“多行不义必自毙。”
“你们两个吃里外的畜生,你们敢动我,苏家不会放过你们的。”
两人见钱眼开,那可是三百万啊!
他们得干多年才能挣到?
别说是让苏以柠去屎,就算是给喂屎两人也义不容辞。
两人拿了支票干起活来也是干净利落,将苏以柠的双膝狠狠往地上一按,苏以柠跪在了脏兮兮的墓碑前。
苏婉禾看着那没有一完好的墓碑,冷着一张脸道:“苏以柠,今天你要是不给我干净,休想离开这里一步!”
只要目落在墓碑上,就会气不打一来。
两人按着苏以柠的头,眼看着的脸就要贴上去,耳边传来苏逸山的声音:“你们在干什么!”
苏婉禾一转,就看到一脸错愕,怀里抱着鲜花的男人。
苏婉禾看到他手里的香槟玫瑰,角勾起一抹冷笑。
为枕边人,他竟然不知道妈妈喜欢的是什么花,这也太可笑了。
一见到苏逸山出现,苏以柠就像是找到了靠山,脸上一片委屈之:“爸……救命!”
“发生什么事了?”苏逸山还没走近就看到被保镖押着跪在墓碑前面的人。
不分青红皂白朝着苏婉禾开口道:“苏婉禾,你妹妹好心过来祭奠你母亲,你怎么能这么对?上次在苏家你还没有玩够吗?”
提到苏家的事,苏逸山然大怒,“你妹妹的膝盖已落下了病,今天你又将按在这里,你简直太过分了!”
“过分?”不屑轻笑。
这表落在苏逸山眼里,另他更加愤怒无比。
“苏婉禾,为了报复你妹妹你不惜连自己的终生大事都能豁出去,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你非要如此恶毒!你想要报复就冲着我来!不要对们下手。”
哪怕那天在医院苏婉禾就和他们断绝了往来和关系,此刻听到他的声音,仍旧觉得而有些刺疼。
抬眼看着苏逸山轻声问道:“是不是在你眼里,我连呼吸都是错的?”
苏逸山当即就懵了,“你说什么?”
苏婉禾指着墓碑,“你那双眼睛长着是装饰吗?难道你没看到苏以柠做了什么?”
在苏婉禾发火下,苏逸山这才将目从苏以柠上转移到墓碑上。
刚刚他太过着急,也都没有注意,如今才发现上面的秽,顿时拧着眉头。
他再怎么不信任苏婉禾,也不会怀疑是泼的。
“这是怎么弄的?”
“你为什么不问问你的好儿都做了些什么呢?天底下有人用这样的污秽来祭拜别人?如果这是苏家的习惯,等你们祭祖的时候,我就泼向苏家祖先每一个墓碑!”
“混账东西!你听听自己说的是什么话?”苏逸山拔高了声音。
苏婉禾冷笑:“你也觉得很可笑吗?就是你这个猪狗不如的儿,对一个死者做了这样的事!你觉得应该怎么理?”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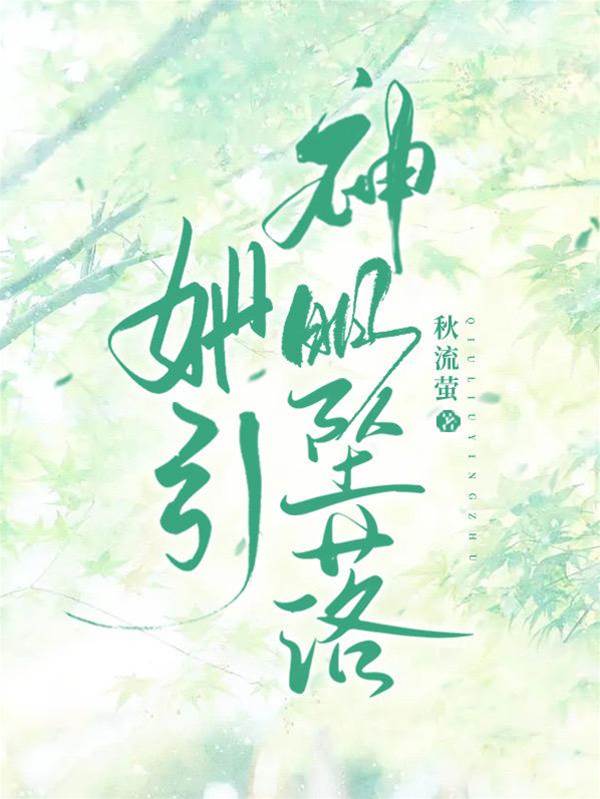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