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活活燒死后,全家后悔了》 第28章 舊事
等到蘇錦棠陪著虞歸晚用完午飯后離開后,虞歸晚的臉才難看起來。
不傻,看得出來蘇錦棠心中的天平已經往著虞疏晚那邊偏去了。
自己要是再沒有作,只怕是虞疏晚就要將給吃了!
想到這些,虞歸晚開始焦灼起來。
畢竟自己的金手指只有一個:知道劇,通過劇打原主可獲得主氣運最后取代主。
可現在劇……
跟印象之中的本不一樣啊!
……
一連幾日,虞疏晚也難得老實了下來,主要是背上的傷一直崩開也不是個事兒,好在虞歸晚也用養病的借口躲著。
實在是樂得清閑。
不過最得意的丫鬟流可慘了。
府上暗自都是議論紛紛,說流不知道是怎麼惹惱了夫人,被幾個婆子按在倒座房那兒狠狠地打了頓板子。
“今日已經是第三天了,昨兒晚上才醒呢。”
可心跟虞疏晚說著從旁聽到的消息,小聲的問道:
“小姐,您也沒說什麼,夫人罰的也忒狠了些吧……”
“這是夫人的拳拳之心,全在板子上顯示了。”
虞疏晚心不在焉的回答著,可心卻不忍,“可流也就才十三歲呢。”
“哦。”
十三歲咋了。
三歲的時候路都還走不穩當的時候就給劉春蘭當牛做馬了。
十三歲還在想著當別人的狗,流這頓打一點兒也不冤枉。
Advertisement
可心想起給虞疏晚沐浴時候,的上都還有一道猙獰的傷疤。
即便虞疏晚沒提這道疤痕的來歷,可心心里也知道虞疏晚從前過得肯定很不好。
但二小姐是真厲害啊。
不僅僅是的手能力,就是眼前抄寫出來的佛經都能夠知道是怎樣堅毅的人。
一個最開始筆都拿不穩的人,如今也能夠寫出一片工整的字來。
“小姐這兩日沒日沒夜地練字,好看許多。”
可心幫著將一張才寫完的給拿過去晾干。
虞疏晚只是低著頭,腦袋里面回想著上一世虞歸晚們握筆的姿勢一點點地抄寫著手上的佛經。
從窗欞落進來在虞疏晚的上。
本就容貌不俗,如今好生養著,也逐漸展開了幾分的艷麗。
臉上宛如白瓷一般蒼白,的長睫,神分外專注。
子雖然瘦弱,可無端地讓人覺得有種傲氣,怎麼也讓人挪不開目。
可心想,跟著這樣的主子,算是賺大發了。
歲月靜好間,門忽地被推開,發出一聲巨響,將可心給嚇了一跳。
“誰……侯爺?”
可心慌忙行禮,心中一下子張起來。
前幾日虞方屹在認親宴的當晚就進了宮,這幾日都不曾回來。
如今這樣大干戈,難不也是來找小姐麻煩的?
“父親,我的字被你毀了。”
虞疏晚方才手上一抖,墨滴落在宣紙上,暈開了一片。
帶著嘆息將筆放下,“有什麼就盡快罵吧,我還要趕場。”
估計著時間,虞景洲也要回來了。
既然是扮豬吃老虎,那至也得裝得像一些吧。
虞方屹難以理解地看向,“你說什麼?”
“父親,我說,哥哥也快回來了吧?”
虞疏晚掰著手指,“應該跟你將什麼事兒都說了,所以你回來連服都沒換就急著過來了。
落水的事你應該知道,哥哥進祠堂、我跟母親爭執……還有嗎?”
的眼中還帶著一種懵懂和純真,把虞方屹給看愣住了。
“父親?”
虞疏晚好笑,“再不罵等下哥哥來了你倆就得罵重聲了,不會笑出來嗎?”
“虞疏晚!”
自己這個名字的確好聽,但也不能這樣天天啊,怪害的。
虞方屹深吸了口氣,“你才回來多久,就惹出這些是非,是不是非要整個虞家都要圍著你轉才高興?”
那倒也不必。
虞疏晚還是更希自己能夠親手為上一世畫個句號。
“父親你太晚了。”
虞疏晚嘆了口氣,“這些話我已經被祖母訓斥過了。”
虞方屹被噎住,可一時間又不知道該說出什麼來。
他本就是擅長帶兵,這些是他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應,想要跟虞疏晚好好算算賬。
可自己對上這個兒到現在,似乎都沒有一次贏過。
“既然是訓斥過,你可知錯了?”
虞方屹冷著臉,“我知你從前不容易,但你也別太過!”
“自然是知錯了。”
虞疏晚眨了眨眼睛,“父親這幾日在宮中忙些什麼?”
被虞疏晚一點,虞方屹眼中的神一怔,像是想起了什麼,神也變得復雜了幾分,
“你當日回去的時候可曾見到……劉春蘭?”
見話題突轉,虞疏晚的面半點不曾變化,
“不曾見到,當時我不是說了嗎,收拾了細,將我一個人丟下了。”
可這一回虞方屹的眼中卻帶著些許的懷疑,
“你當真是不知道?”
忠義侯府是有兵權的朝臣,忠義侯府的兒也自然會嫁東宮。
這是整個大梁心照不宣的事。
可從前忠義侯府只有一個兒,如今,忠義侯府卻出現了這樣的真假千金橋段。
倘若只偏心一個兒也就罷了,可忠義侯和夫人疼大小姐,掌管虞家的老夫人卻偏二兒。
這一次也正是因為消息傳到了宮里的貴人耳朵中,至是要驗明虞疏晚正的。
從前種種,祈景帝自然也是要一一過眼。
自然而然地,劉春蘭的份也被查得清清楚楚,換了他兒人生的拐子,在這十四年中對虞疏晚做的事連他一個男人都忍不住的垂淚。
可劉春蘭如今實在是消失得莫名其妙,也不見文書流通。
想到虞疏晚那一日的所作所為,如今想想,實在是有些不對。
“我若是知道,早就告訴虞歸晚了。”
虞疏晚一臉坦然,“雖然說要好好相,可你們不是說生父母恩大于天麼,該恩劉春蘭的。”
說完,一臉驚訝,“逃的那樣徹底?”
虞方屹不做聲,只是盯著。
虞疏晚好笑道:“父親是覺得不見了是跟我有關系?”
“沒有關系?”
虞疏晚想了想,道:“那父親就當做是我恨死了,所以把殺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232 章
腹黑郡王妃
一覺睡醒,狡詐,腹黑的沈璃雪莫名其妙魂穿成相府千金.嫡女?不受寵?無妨,她向來隨遇而安.可週圍的親人居然個個心狠手辣,時時暗算她. 她向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別人自動送上門來討打,休怪她手下不留人:姨娘狠毒刁難,送她去逛黃泉.繼母心狠手辣,讓她腦袋開花.庶妹設計陷害,讓她沒臉見人.嫡妹要搶未婚夫,妙計讓她成怨婦.這廂處理著敵人,那廂又冒出事情煩心.昔日的花花公子對天許諾,願捨棄大片森林,溺水三千,只取她這一瓢飲.往日的敵人表白,他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心,她纔是他最愛的人…
155.2萬字5 59507 -
完結752 章

盛世凰歌
擁有精神力異能的末世神醫鳳青梧,一朝穿越亂葬崗。 開局一根針,存活全靠拼。 欺她癡傻要她命,孩子喂狗薄席裹屍?鳳青梧雙眸微瞇,左手金針右手異能,勢要將這天踏破! 風華絕代、步步生蓮,曾經的傻子一朝翻身,天下都要為她而傾倒。 從棺材里鑽出來的男人懷抱乖巧奶娃,倚牆邪魅一笑:「王妃救人我遞針,王妃坑人我挖坑,王妃殺人我埋屍」 「你要什麼?」 「我要你」
132.9萬字8 10928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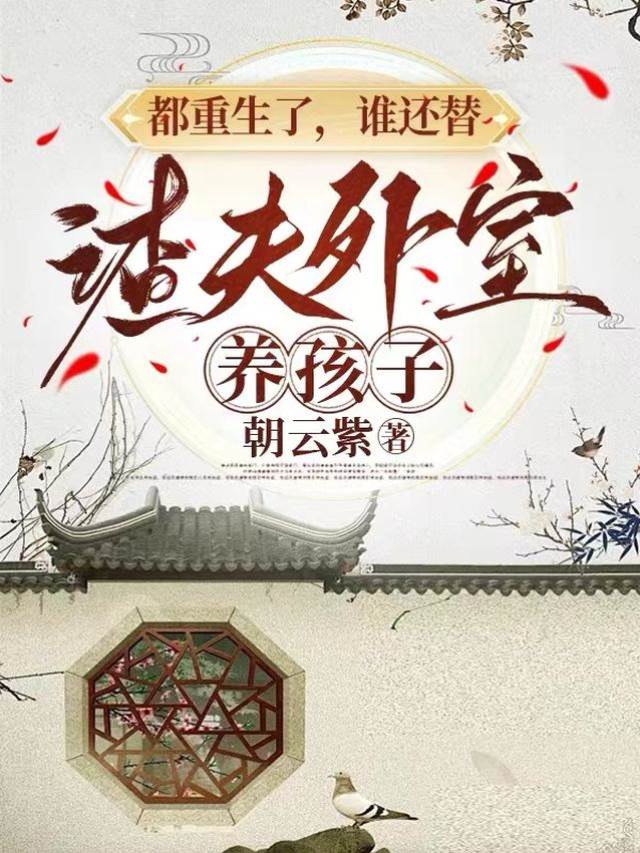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