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我說渴膚的第三天》 第126頁
「臥槽臥槽, 」吳文宇一進來就是一連串的
我草,然後幾步撲過去, 探薄彥的鼻息, 「薄......」
薄彥睜眼,滿臉都是被擾了清夢的不耐。
「喊什麼?」他人還燒著,說這句時沒看到房間門口站的幾個工作人員。
吳文宇看到他睜眼,也顧不上他對自己的態度,大氣似的轉向不遠穿酒店工作服的幾個人:「活了活了。」
「沒事了, 謝謝啊!」
薄彥終於反應過來屋子裡還有人, 皺眉往那看了眼,著毯子眉心, 沙啞著聲線:「你有病?」
吳文宇站起來, 謝完那幾個工作人員,又委婉把人謝走,等門關上,再折回:「我草,什麼我有病?我看是你有病吧,你嚇死我了, 我給你打電話你怎麼不接??」
薄彥眼看了眼不遠的手機, 眼睛又闔上:「靜音了,沒聽見。」
他態度太冷漠, 人又病殃殃的,一看就不太正常,吳文宇環視了一圈房間:「帛夕呢?走了是什麼意思......」
Advertisement
薄彥閉著眼,眼角耳朵都是燙的,單臂在側臉下,腦子非常混沌。
須臾:「走了就是分了,不要我了,很難理解?」
吳文宇正打算打趣,被他一句話噎得調侃卡在了嚨里。
「什麼?」他往沙發邊走,出笑,試圖緩和氣氛,「不是還過來陪你比賽......」
「來說分手的。」他打斷他。
薄彥聲音非常低,臉上沒什麼表,睫微微,因為發燒,側臉有不明顯的紅。
片刻後,像是終於忍不了吳文宇的聒噪,毯子掀了一半,撐著坐起來。
吳文宇手扶他,手剛到他的手臂,被溫度燙到:「你發燒了?」
薄彥手臂從他手里出來,眉骨往下垂著,說話有些費力:「有點。」
「有點?什麼有點?都燙這樣了有點??」吳文宇說著轉往周圍看,「你這地方有藥沒,要不我陪你去醫院?」
不行的貓包就被放在不遠,他兩隻爪子趴著包的邊沿,沖這「喵」了一聲。
薄彥目落在那,看到不行脖頸戴的銀貓牌,那是過年前帛夕買給它的。
他看了片刻,吳文宇還在到找藥,勸他去醫院:「你這樣不行,萬一燒出肺炎……」
「不要我了。」他忽然說。
「也不要不行了。」
「去年給不行掛貓牌還說要一輩子給它當姐姐。」
結果轉頭人就走了。
騙子。
不行看到他看自己,前爪從貓包里出來,張著了個懶腰,才慢騰騰地邁著貓步走向薄彥。
剛邁了兩步,薄彥起,燒得太狠,他走路都有些晃。
吳文宇正跪在電視櫃前找藥箱,還沒等拉兩下,轉頭看到薄彥跟喝多了一樣往不行的方向走。
「你要干什麼你給我說,你自己起來幹嘛,再摔了我靠。」
話音落他看到薄彥在不行前蹲下。
男生兩手搭膝蓋,像是看了一會兒才意識到周圍的環境和不行。
隔著好幾米,吳文宇都能覺到他上冒的熱氣似的,剛那溫度,跟烙鐵一樣,他特別怕薄彥燒傻。
那人跟不行一人一貓對了會兒視線,右手抬起了把發頂,之後把不行脖子裡的貓牌摘下來。
「喵——」
薄彥長指繞了下貓牌的鏈子纏在手里,之後起,拉著衛的帽子罩在頭頂。
吳文宇半跪的姿勢看他。
「我下午去趟西南。」他說。
「什麼東西?」吳文宇炸開,「我剛過來你說你要走,你有病吧。」
薄彥沒理他,徑直往臥室走。
纏在右手手心的金屬牌,因為染了他的溫度,微微發燙。
這東西是好早之前就給不行的,都是不行上的味道,現在對他來講完全沒用。
他眼眶發燙,燒得有點半死不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喜歡,現在連貓和以前常用的東西都沒用了,只能是。
好難,離開一分一秒都像被筋剝皮一樣難。
走到臥室關上房門,吳文宇和不行的聲音都被關在門外。
他頹敗的後背抵著房門,站了良久,低頭拿手機打給劉明,讓他幫忙訂張機票。
就這一次,他得拿點藥回來,才能捱得過這一年。
晚上八點,帛夕正在房間收拾東西。
還沒來得及重新聯繫租房,只能先搬回宿舍住,床單被罩剛買了兩套新的,昨天洗淨曬乾,現在正在鋪床。
薄彥電話來的時候,剛把被子套好。
聽到床頭手機振,把套好的被子折了一下扔在床上,俯過去撿起看。
是個不認識的號碼。
和薄彥說好了分開,就沒有再刪他,但不知道為什麼屏幕跳的這個號碼總覺得是他的。
猶豫兩秒,在床邊坐下,劃了接聽鍵接起來:「餵?」
第一聲對面沒說話,奇怪地又問了一聲。
「不說話我要掛了。」
外面下雨了,細細的雨刮的人臉涼。
薄彥站在們學校門口,靠著電線桿,他繃了一下線,像是糾結了一番,終於吐聲:「你前男友。」
哦豁,小夥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 (>.
: | |
猜你喜歡
-
完結43 章

春色難馴
江城時家弄丟的小女兒終于回來了。 整個時家,她要星星還強塞月亮。 —————— 二中開學,時年攬著好不容易找回來的妹妹招搖過市。 眾人看著那個被時年夾在咯吱窩里,眉眼如春的小姑娘,紛紛誤會,“小嫂子絕了,絕了啊。” “想什麼呢?!”時年忿忿,“這是我妹!” 時·暴躁大佬·年,轉頭笑成智障,“歲歲,叫哥。” 此時,一位時年的死對頭,江·清貧(?)學神·頂級神顏·骨頭拳頭一起硬·馴,恰巧路過—— 椿歲哥字喊了一半,就對著江馴甜甜一聲,“哥哥!” 江馴看著這對兄妹,鳳眼微掀,漠然一瞥,走了。 時·萬年老二·考試總被壓一頭·年:“???”啊啊啊啊你他媽什麼態度?!所以為什麼你連哥都比我多一個字?! —————— 時年曾經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江馴踩在腳下,讓那個硬骨頭心甘情愿叫他一聲“哥”。 直到看見死對頭把他親妹子摁在墻角邊(沒親,絕對沒親)。 時年真的怒了,“你他媽壓.我就算了,還想壓.我妹??!!” 江馴護著身前的椿歲,偏頭懶聲,“哥。” 椿歲:“…………” 時年:“???”啊啊啊啊別他媽叫我哥我沒你這種妹夫!! —————— 小劇場: 椿歲:“為什麼裝不認識?” 江馴:“怕你喜歡我啊。” 椿歲嘁笑,“那為什麼又不裝了啊?” 春夜的風,吹來輕碎花香。 江馴仰頭,看著枝椏上晃腿輕笑的少女,低聲笑喃:“因為……我喜歡你啊。” #你是春色無邊,是難馴的執念# 冷漠美強慘X白甜小太陽 一句話簡介:我成了真千金你就不認識我了? 1V1,HE,雙初戀。不太正經的治愈小甜文。
16.3萬字8.18 6106 -
完結1181 章
余生悲歡皆為你
婚前,她當他是盲人;婚后,方知他是“狼人”。 * “你娶我吧,婚后我會對你忠誠,你要保我不死。”走投無路,喬玖笙找上了傳聞中患有眼疾、不近美|色的方俞生。 他空洞雙眸毫無波瀾,卻道:“好。” 一夜之間,喬玖笙榮升方家大少奶奶,風光無限。 * 婚前他對她說:“不要因為我是盲人看不見,你就敢明目張膽的偷看我。” 婚禮當晚,他對她說:“你大可不必穿得像只熊,我這人不近美|色。” 婚后半年,只因她多看了一眼某男性,此后,她電腦手機床頭柜辦公桌錢包夾里,全都是方先生的自拍照。 且看男主如何在打臉大道上,越奔越遠。
216.9萬字8 12334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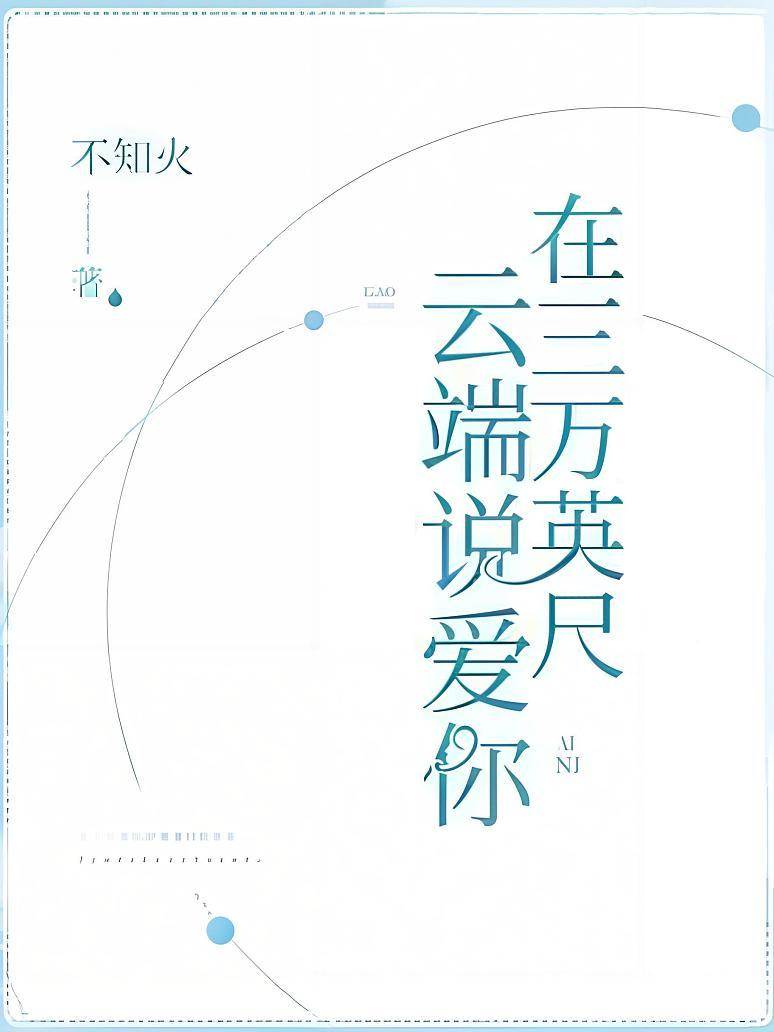
在三萬英尺云端說愛你
高考過后,楊斯堯表白周月年,兩人在一起,但后來因為性格不合,和楊母從中阻撓,周月年和楊斯堯憤而分手。分手之后,兩人還惦記著對方,幾番尋覓,終于重新在一起。周月年飛機故障,卻因為楊斯堯研制的新型起落架得以保全生命,兩人一同站在表彰臺上,共同迎接新的生活,新的考驗。
18.2萬字8 3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