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孕後,渣老闆每天都想拿掉我的崽》 第546章 滾落
山風烈烈,匕首的尖端往下墜著。
江稚的手在抖,跑得很快很急,嚨里灌進來的風就像刺,好似割傷了的管,吞咽進來的都是沫,一子生銹的味。
興許是跑得太急,腳下不穩,摔在地上,膝蓋和雙手都被糙的石頭磨破了。
江稚顧不得別的,爬起來只能往前跑。
夕的余暉,瑰麗昏黃。
風越來越大,吹了的頭發,看起來有些許的狼狽,快要耗盡力之前,總算看見了江歲寧今天開過來的車。
很舊,很老,不知道從哪兒借來的。
江稚氣吁吁走過去,聽見嬰兒的哭聲。
的眼淚幾乎一下子就掉了下來,連日來輾轉反側,深夜難眠的時刻都在擔驚怕。
用力拉開車門,將被隨意放在副駕駛上的孩子抱了起來。
可能是心有所,小朋友窩在媽媽的懷里,就漸漸止住了哭聲。
乖巧的待在懷中,不哭也不鬧了。
江稚滾燙的眼淚倉促落在他臉上,又著急忙慌的幫他了臉,檢查了他上沒有傷口才勉強放下心來。
江歲寧已經追了上來,并不是一個人過來的,帶了幾個花錢雇傭的保鏢,當然也不是什麼正經人。
江稚后就是山的盡頭,只有一條靠著斷崖的道路。
摟著孩子。
江歲寧看著孤立無援站在車的旁邊,“你以為你還能跑得掉嗎?”
江稚現在的確不占優勢,除了剛才那把匕首,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和江歲寧后的黑保鏢比起來也什麼勝算都沒有。
Advertisement
“你這樣是犯法的。”
“你剛才拿刀傷我也是犯法。”江歲寧當然不會怕這句恐嚇,事已經做到這一步,早已退無可退,放江稚離開,安全之后立刻就會報警。
當然,江歲寧一開始把江稚騙到這邊來就沒有想過要放離開。
孩子不過是的魚餌,起初要的就是江稚的命。
江稚就該當一個早死的前妻。
江歲寧這會兒不用演戲,索把所有的事都說給聽,不介意讓知道真相之后再死,“當年那個綁匪犯糊涂,心慈手沒有舍得撕票,是他糊涂,他鬼迷心竅、壑難填,拿了我媽媽的錢還不夠,還想要沈家的錢,所以你才好命活到現在。”
江稚以為自己當初不過是倒霉,才為了被綁匪隨機挑選的那個人,原來并不是這樣。
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預謀的。
“是你媽媽找的人?”
“當然,那個時候江家也沒什麼錢,你以為綁匪憑什麼能看得上這點贖金?”
不過是自導自演的一場戲。
母親給錢。
綁匪撕票。
誰知道那人貪心不足。
“你要死了,我不介意多和你說一些。”江歲寧一步步往前,卻又怕像剛才那樣忽然發瘋,拿刀朝自己捅過來,因而也只敢停在離不近不遠的地方,“你以為沈律言現在也是真的你嗎?你知道他當初為什麼選了你結婚?”
江歲寧盯著的臉,“你不會覺得只是睡了一次,他就因為要負責和你結婚吧?”
;江稚一直都知道,和沈律言曾經那段婚姻,是各取所需。
沒有什麼基礎可言。
不用江歲寧再次提醒。
“他就算需要一個結婚的對象,哪怕只是娶回家當一個擺設,也多的是人愿意,憑什麼是你呢?你真的仔細想過嗎?”江歲寧看著逐漸擰起來的眉心,扯起角笑了笑,接著往下說,“因為你和我有幾分相似啊。”
是的替而已。
是一個用來消遣、可以隨意打發的替代品而已。
江歲寧不放過任何打擊的機會,看著漸次白下去的臉,和愈發脆弱破碎的表,語速不慌不,慢吞吞的確保能夠聽得清楚,“他以前看著你的眼神難道不像是在看別人嗎?你真的一點兒都沒有察覺到嗎?
江稚忽然想起來曾經被自己忽略的很多細節。
其實也沒有忽略,只是自欺欺人,故意當做自己忘記了。
剛結婚的那段時間,沈律言每次看著的目都有種看不的深意,他偶爾會看著的眼睛走神,好像就是著在懷念別的什麼人。
和江歲寧,盡管是同父異母有緣關系的人,也只有這雙眼睛有幾分相似。
難怪、難怪。
原來就連一開始的各取所需,竟然也是另有圖謀。
從一開始在沈律言的眼里就是個不值錢的、不被在意的替代品。
江稚心麻木的連笑都笑不太出來,還能說什麼呢?失了太多回,已經不會失了。
江歲寧似乎終于說夠了,給后的保鏢使了眼神,人高馬大的男人就朝江稚的方向近。
“你生了這個孩子又怎麼樣?現在只能讓你兒子陪你一起去死,黃泉路上也不孤單。”
江稚的后背著車門,,已經沒有再退的空間。
當機立斷,拉開車門,爬進駕駛座,將孩子旁邊的座椅。
啟汽車的手都在發抖,現在頭腦格外的冷靜,啟了車輛,踩下了油門。
幾乎是汽車發的瞬間,就聞到了汽油的味道,空前的刺鼻。
江歲寧并不慌張,這輛車本來就不打算留下來,連著車里的孩子都沒打算讓他活,之前就人剪斷了剎車線,捅了油箱。
再往前都是絕路。
江歲寧給保鏢使了個眼神,接著保鏢便開著來時的車,追了上去。
江稚已經快要將油門踩到了底,后面的車追不舍,已經快要開到山崖的盡頭,哆哆嗦嗦的出手機,打電話求救的瞬間,后車的保險杠毫不猶豫的朝撞了過來。
砰的一聲,撞上了山崖前的石頭。
安全氣囊彈出來的瞬間,江稚也不知自己的手到了哪個號碼,腦袋被撞得發暈,顧不得其他,解開安全帶,將孩子抱了起來。
車里的汽油味越來越濃郁。
已經燒起來了火苗。
怕是很快就要炸了。
江稚渾都疼,用力推開車門,連滾帶爬下了車,下一秒鐘后車就又撞了過來。
火勢迅速猛烈了起來。
江稚的腦袋已經很暈,護著懷里的孩子,倒在地上,模模糊糊間看見那輛車偏離了方向,車頭似乎是要朝這邊碾而來。
左邊是燒得快要炸的汽車。
右邊是看不見底的陡崖。
江稚在黑車朝碾過來的那個瞬間,毫不猶豫選擇摟了孩子,從崖邊滾落了下去。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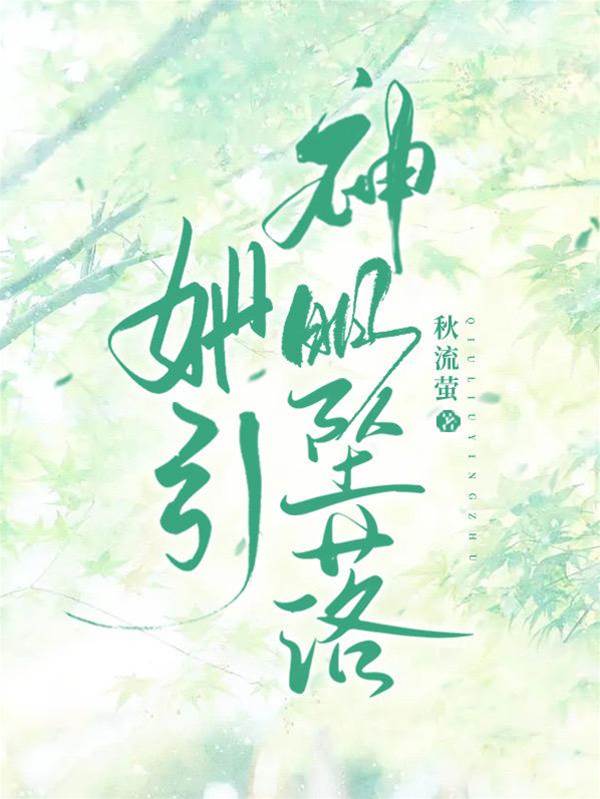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