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王追妻:這個小妞有點甜》 第一千二百一十八章 失敗
最後也沒有功,一直到村民都撤了,剩下一個的,更像是村頭潑婦,還是罵街不很兇,又不得窩囊氣的那種。
舌頭上像是沾了火星一樣,燒的干疼,但停不下來,一停下來,就好像被空了元氣,就輸了。
不能輸。
一直罵,罵到連自己生疏的辭彙和胡言語都再找不出,找不出合理的排列組合的時候。
沒有人發聲,甚至連搭理的人都沒有,就好像此時此刻的田迭香,已經勝利了。
只有趙冷了,田迭香早已經敏銳得近乎神經質,一見到趙冷的抖,甚至這抖只是那麼微不可聞,也立刻、迅速平靜了下來。
就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那樣,面帶微笑,臉沉寂地,吐出一口氣。
等。
等待趙冷。
趙冷只問了一句話。
「說完了嗎?」
半睜眼,氣吁吁。等到的只一句而已。
看到趙冷穿著一潔白的服,長而立,手裡的銬子不知道開過還是怎麼的,鋥亮。
趙冷很快就到了邊,冷冰冰的像是北風一樣吹過來冷抓起田迭香的一雙手臂,竹篙子那樣,一隻手就給並了起來,拿銀白的銬子往上一套一扣,作很乾脆。
完了?迭香心想。
「完了——」
翻翻皮,再扭頭看看不怕死的老馬。
那一黑的皮大亮著白的褶子,像是從地獄里跑出來的使者,如果看了他眼的一雙細長眼睛,就更覺得像了。
就是這個男人,拿槍著自己,像是賭命。
抬起頭,乾的嚨滴,聲音還不如村頭忘添油的磨機細緻,幾乎是聽著就讓人眉頭鎖,眼眶沾。
「我還有一件事。」上一沾下瓣,就被粘粘的唾粘得撕裂開來,沒了傲氣和智謀,只剩下一肚子哀怨。
Advertisement
但偏把哀怨了下來,把滾著膿腥味兒水的唾沫往肚子里咽,只是央求,可那口氣並沒有半點鬆。
這話當然是對趙冷說的,但又像是自怨自艾。
看了趙冷一眼。
「這件事,我想讓你知道。」田迭香看著趙冷,又像是看著以前的自己:「別被他騙了。」
趙冷攤開手,把玩手裡銀的手槍,的神很安然,自然不可能被田迭香的一句話說,甚至眉微微那麼一挑,甚至頗有些嘲弄。
「田小姐。」趙冷笑了笑:「用我再提醒你一次,這是我的師父麼?」
指了指老馬,連多看一眼都顯得多餘,更不必去看老馬的神,趙冷也知道那會是怎樣的嘲弄和戲謔,就像現在的自己一樣。
「就怕只有你自己是這麼想。」田迭香不咸不淡地說了這麼一句,左邊半張臉的頭髮更一些,瀑布樣落下來,顯得接近瘋狂的一張臉上更加詭異。
「你這話裡有話啊。」趙冷問。
田迭香看了看老馬,趙冷也回頭看他。
但老馬的模樣讓趙冷有點兒詫異。他若無其事地收起手裡的槍,整了整風的立領,臉沉在風的領子下看不真切,但有一點讓趙冷心裡「咯噔」地響了一聲。
老馬沒有敢跟趙冷視線対。
或者說。
他躲過了趙冷的視線。
這有點奇怪,但還在理之中。趙冷放下槍,往後退一步,整個人就與老馬並肩站立,拉下臉瞪著田迭香,「你還想說什麼。」
「沒有。」田迭香搖搖頭,臉上的神變得恍惚,兩邊的發梢微微晃。輕輕移步上來,來到趙冷的手槍前,不顧趙冷的喝止,雙手攥住趙冷的槍,一張臉煞白,兩瓣薄薄地切到一,角一張開,嘶啞的聲音和艷紅的跡就印眼裡。
儘管趙冷提醒了不下三次,「再輕舉妄,就開槍」。
但也不知道是不怕死,還是確信趙冷不敢這麼做,單薄的軀頂在趙冷的槍口,那麼真實的存在,卻讓怎麼也扭不手裡的扳機。
「你,開槍啊。」田迭香嘲弄一樣歪了歪頭,拿得很有分寸,順道了兩鬢的髮,似乎不用怎麼思考,就能從趙冷的臉上讀出想要讀出來的一切。
就很簡單。
「你知道,我是很重要的嫌疑人,就算我當著你的面殺人,你也不敢輕易拿走我的命,對麼?」田迭香問。
不知道為什麼還笑得出來。趙冷想不明白,只是的沾著,臉又像紙一樣難看,笑出來絕算不上好看,這樣一副臉孔,偏偏還讓拿不準,到底該怎麼辦。
「告訴你一件好事。」田迭香湊到趙冷的耳朵邊,張開,嘶啞的聲音和就好像流淌在趙冷的里一邊一樣:「你,很仰慕這位老馬?」
趙冷耳朵一紅。
老馬是什麼人?師父?長輩?還是什麼?趙冷想了想,搖搖頭。
老馬就是老馬,五年前,把從基層挖出來的恩人,五年後,又讓自己回到警隊里,如同再造父母一樣的恩人。
但他從沒有向自己索要任何回報。
只是希,自己能為一名好警察。
一定是這樣,趙冷似乎有這樣的覺,說不準,但老馬一定是憑著信念活著的那種人。
所以,當田迭香告訴,老馬是個「叛徒」的時候,除了冷笑,什麼反應也沒有。
「你不相信我?」田迭香神兮兮地說,的眼睛里像是有無數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閃著,否則不會這麼亮。
趙冷當然不信,但連搖頭都覺得多餘。
田迭香又說,「你如果真的不信,不該是這樣的反應。你知道你剛才下意識地把耳朵往我前湊了兩公分麼?」
趙冷實在忍無可忍:「要你的人立刻撤開,等老柴回來,我們就要收網了,你不反抗的話,我可以考慮替你在聽證法庭上說兩句。」
田迭香側目看了老馬一眼,出了一張很神奇的臉孔,這種表趙冷從沒見過。
很難去形容這樣的表。
拿不準,到底是找死,還是已經沒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氣。
也許兩者都有。
把手鬆開,順著趙冷的手到槍的扳機,手指倒扣在扳機上,兩隻眼睛木木地,瞪得有茶杯大小,忽然勒了手指。
這一下要不得!
趙冷趕懟了指頭,稍不留神,扳機就扣,那眼前的田迭香肚子上就要開一個大。這孩兒已經連死都不怕了嗎?趙冷盯著看了一分鐘,確認不是。
因為笑了。
據趙冷所知,死之前的人可不會笑。
田迭香笑的有點兒甜,甚至讓趙冷有點兒恍惚,接著就起了,起的時候,飄飄若仙。
面無的田迭香說,「你以為的老馬,和我以為的老馬,也許本不一樣。你知道,他能在組織里有這麼高的信譽,能讓這麼信任他,用了什麼花樣麼?」
趙冷搖頭。
田迭香捂著,眼很是鋒利。
「我早覺得,這件事告訴你最有意思,小姑娘,你聽我說。五年前,老馬還有一個兒子,但是,但是那個兒子讓他很難堪。」
「我不明白你想說什麼。」
趙冷有意回頭看了一眼。
老馬的臉果然很奇怪,兒子這個話題是他最忌諱,也最不想提及的,是黑歷史,也是他的噩夢。有這樣的反應不奇怪。
可是……
田迭香現在的境用「絕」來說也不為過,為什麼偏偏要選在這麼一個機會,說這麼久遠的故事呢?
田迭香卻就不管這些,很有意地看著老馬的臉,從平靜,轉變為憤怒和惱火,樂在其中的了手,修長的指頭摁在趙冷的槍管上,面如常。
「但不管怎麼說,兒子也是自己的兒子,不可能因此就不待見。」田迭香就像是沒見到老馬那紅的臉一般,繼續進行著自己的話題,也本沒打算就此打住。
儘管老馬已經命令了好幾次。
但就當做耳旁風,繼續往下說。
「但後來,兒子如果闖出禍來怎麼辦?趙警,如果是你,你的好朋友,親人,甚至父母,該怎麼辦?」
趙冷愣住。
「不用陪玩這種無聊的問題。」老馬拉下臉來:「小趙,按計劃進行,等柴警回來,我們立刻行。」
趙冷沒多想就點了頭。
田迭香卻笑得更開心了,彷彿沒什麼比今天遇到的事更讓雀躍。
「真有意思,狐貍,你還裝著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樣,簡直就和五年前那些對你兒子視而不見,害死他的那幫畜生沒有兩樣,不是麼?」
趙冷明知道這句話是挑釁,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老馬中計了。
他的表藏在面底下,「狐貍」的眼睛卻藏不住,通紅。
趙冷從沒見過一個人的神能如此割裂,桀驁不馴的「狐貍面」彷彿就像是對老馬的嘲弄,而此時他的緒也直接反映在他的軀上。
全的發出悶響聲,發出了油鍋炙烤的聲音。
田迭香看了一眼,揚了揚下。
就像在說,你瞧,跟我說的一樣,他有反應了。
「五年前的案子,讓老馬從此一蹶不振,他對這個系統,這個世界,甚至自己失了——狐貍,你是不是忘了,當初把你從深淵拉起來的人是什麼人?為什麼你回到了自己的象牙塔,就覺得,以前的棋子,就可以拋棄不用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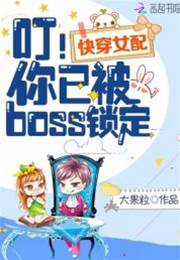
快穿女配之你已被boss鎖定
阮綿綿隻想安安分分地做個女配。 她不想逆襲,也不想搶戲,她甘願做一片綠葉,襯托男女主之間的純純愛情! 可是為什麼,總有個男人來攪局?! 阮綿綿瑟瑟發抖:求求你,彆再纏著我了,我隻想做個普通的女配。 男人步步逼近:你在彆人的世界裡是女配,可在我的世界裡,卻是唯一的女主角。 …… (輕鬆可愛的小甜文,1v1,男主都是同一個人)
103萬字7.83 14294 -
完結231 章

離婚夜,植物人老公扒光我馬甲
成為植物人之前,陸時韞覺得桑眠不僅一無是處,還是個逼走他白月光的惡女人。 成為植物人之後,他發現桑眠不僅樣樣全能,桃花更是一朵更比一朵紅。 替嫁兩年,桑眠好不容易拿到離婚協議,老公卻在這個時候出事變成植物人,坐實她掃把星傳言。 卻不知,從此之後,她的身後多了一隻植物人的靈魂,走哪跟哪。 對此她頗為無奈,丟下一句話: “我幫你甦醒,你醒後立馬和我離婚。” 陸時韞二話不說答應。 誰知,當他甦醒之後,他卻揪著她的衣角,委屈巴巴道: “老婆,我們不離婚好不好?”
56.4萬字8 19064 -
完結81 章

仲夏呢喃
霖城一中的年級第一兼校草,裴忱,膚白眸冷,內斂寡言,家境貧困,除了學習再無事物能入他的眼。和他家世天差地別的梁梔意,是來自名門望族的天之驕女,烏發紅唇,明豔嬌縱,剛到學校就對他展開熱烈追求。然而男生不為所動,冷淡如冰,大家私底下都說裴忱有骨氣,任憑她如何倒追都沒轍。梁梔意聞言,手掌托著下巴,眉眼彎彎:“他隻會喜歡我。”-梁梔意身邊突然出現一個富家男生,學校裏有許多傳聞,說他倆是天作之合。某晚,梁梔意和裴忱走在無人的巷,少女勾住男生衣角,笑意狡黠:“今天賀鳴和我告白了,你要是不喜歡我,我就和他在一起咯。” 男生下顎緊繃,眉眼低垂,不發一言。女孩以為他如往常般沒反應,剛要轉身,手腕就被握住,唇角落下極輕一吻。裴忱看著她,黑眸熾烈,聲音隱忍而克製:“你能不能別答應他?”-後來,裴忱成為身價過億的金融新貴,他給了梁梔意一場極其浪漫隆重的婚禮。婚後她偶然翻到他高中時寫的日記,上麵字跡模糊:“如果我家境優渥,吻她的時候一定會肆無忌憚,撬開齒關,深陷其中。”·曾經表現的冷漠不是因為不心動,而是因為你高高在上,我卑劣低微。 【恃美而驕的千金大小姐】×【清冷寡言的內斂窮學生】
40.2萬字8.18 48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