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你悅人》 第68頁
今天就是因為梅惠和駱文謙不在家,隔壁噪音頗大,在打墻柜,駱悅人才找了自習室,打算消磨一天。
進了店,他們選了二樓靠窗的位置,梁空坐在駱悅人對面,悠哉剝殼,兩口把那顆茶葉蛋吃了。
之后駱悅人看書寫題,梁空趴在對面睡覺。
十點多的時候,外面出了太,厚重的云層邊緣,忽然溢出一抹耀眼日,直直打在大片玻璃上。
淡金的線折進室,強烈又灼目地落在梁空閉合的眼皮上。
他皮白,上眼瞼出淡且細的藍紫管,睫烏濃纖長,睡著的樣子沒有平日里鋒芒畢的攻擊。
枕一只手臂,另一只手臂半環著自己,是很沒有安全,自我防衛的姿態。
駱悅人看了一會兒,見他有皺眉的預兆,立馬回了神,還有些心虛。
好在梁空并沒有醒。
從書包里出一本書脊較的資料,從中間打開,豎在靠窗邊的桌角,替他擋著玻璃外的刺眼的線。
他睡在和的翳里,發梢廓染著淡金,駱悅人沒有學過,但那畫面里的影對比,燦爛又融合,著冬日獨有的凜冽與纖薄,和他周的氣質,講不出的一種自洽。
Advertisement
總歸是很好看的。
這一覺梁空睡得非常長,因為他高長,趴在這種小桌上,不管換什麼姿勢都不會睡得太舒服,骨頭蜷久了,會發酸。
醒來第一時間,他抻了一下肩骨,眼睛里的睡意剛散去一些,就見對面的駱悅人言又止地盯著他。
“干什麼?”
駱悅人停了兩秒,拿筆頭往旁邊指了指。
梁空莫名其妙地看過去。
臨桌有三個跟他們差不多同齡的生,正枯苗雨般的看著這邊,梁空不設防地轉頭,跟們草草對了個眼神。
目收回來,他又看著駱悅人:“什麼意思?”
那三個生沒有說話,因為梁空睡著那會兒,已經跟駱悅人通過了,這會兒只出期待的表,等著幫忙轉達。
駱悅人也不負厚,對梁空說:“們想要你的聯系方式,但你剛剛在睡覺,不好意思打擾你,就一直在等。”
說完,又略小聲地補一句。
“等了久的了。”
駱悅人的聲音在還未醒的腦子里過一圈,隨著睡意散去,聚攏起來的是梁空的眉頭。
他匪夷所思,目在那三個生和駱悅人之間又遞了一個來回。
怎麼出現這種況的?
明明只要說一句“不好意思,這是我男朋友”就能打發了的事,為什麼會發展那三個生等他睡醒?
駱悅人這大善人還在幫人傳話。
到底拿他當什麼?
梁空輕輕冷冷一聲笑,嚨淤了火氣,聲音反而更加輕飄飄的:“你不是有麼?你直接給啊。”
駱悅人放低聲音:“那樣會不會太不尊重你了,萬一你不想給呢?”
梁空眼底滯著寒氣,卻笑得更歡,點著頭夸:“你真的會尊重人的。”
最后聯系方式給了,字字清晰報的數。
其中有一個生說他名字很特別,很見名字里有空這個字,問有什麼講究。
他耐心無幾。
“沒講究,隨便起的。”
駱悅人這才發現他好像是不太對勁,等那三個生走了,握著筆,掌心有點微微發汗。
“你是不是不喜歡給生聯系方式?”
梁空靠在椅背上,兩臂疊輕環,單姿態上就一沖天戾氣,偏把話說得和:“怎麼會,我聯系人里多得是生,多這三個不多,這三個不。”
指間用力,磨著筆上防墊的凹,好像室暖氣開的太足了,心口有點悶。
“哦。”
說出這個單音,視線依然和梁空對著。
他眸慢慢有變化,在數秒鐘的安靜后問:“們沒問我們是什麼關系嗎?”
“問了。”
“你怎麼回的。”
“我說我們是同學。”
不知道怎麼回事,明明當時在心里想的時候覺得很順理章的事,化作聲音說出,卻覺得心虛,每個字都落不到實一樣。
之前裴思禹說過,梁空從來沒有對外說過是他的朋友,學校里都沒人知道,梁空怕麻煩,自攬份也有些不恰當吧。
反正他們之間也從來不像談,就不想給梁空添麻煩,好像攔他的桃花,也不太合適。
邏輯上是講得通的。
但總覺得哪里不對勁。
那天之后,很快就迎來十校聯考,學校放了半天假布置考場。
駱悅人抱著書跟江瑤一起往校門走,正聽在苦惱十三班張泉那朵爛桃花。
“你說他是不是在拿我當備胎?”
駱悅人接著話問:“什麼備胎呢?”
江瑤嘆了一聲說:“就是明明不,還一直拖著不放。”
出了高三的教學樓,駱悅人正思考這句話,就聽邊的江瑤忽然咋呼起來,指著某個方向激道:“就是!快看啊悅人!”
駱悅人看過去,一個束著高馬尾的生被幾個小姐妹簇擁著,走去網球場那邊,
生長長的發尾自然微卷,鮮紅的緞頭花格外醒目,昂首像只小天鵝。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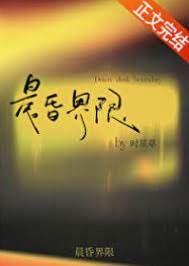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