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甜妻在上︰墨少別亂來》 第91章 偷了個吻
教授聞言有些驚訝,不過最終也沒問什麼,隨和的點點頭,「可以,這都是小事,那你按照這張單子上的要求,把該準備的都準備好,遞上來。」
就此,霍雨辰上學的事有了著落,一家人這才放下心來。
一切好像都發生的剛剛好,或許就連上天都期盼著這樣的結局吧。
離開北城的前一天晚上,霍雨眠始終提不起心,心不在焉的,儘管總是帶著笑,可誰都能看出來,的笑容里是那麼的苦。
飯後,回到房間,什麼都干不下去,看著角落裡已經收拾好的行李,雙臂抱膝坐在床頭,獃獃的著虛空,雙眸沒有焦點,眼睛里也沒有亮。
房門突然被敲響,霍雨眠沒有看過去,只是淡淡的說了句,「進來吧。」
秦詩寧推開門,就看到一落寞的姐姐,彷彿也看到了心抑著的痛苦,心下意識的跟著痛了一下。
緩緩走到邊坐下,親詩寧的臉上滿是擔憂,聲問道,「你是不是還在想墨封訣?」
這個名字,家裡這兩天一直不敢提及,都害怕到霍雨眠敏的緒,可秦詩寧卻知道,越是不提,霍雨眠心裡的空就越大,有的時候,需要找個人訴說一下,有關,有關墨封訣,有關他們的點點滴滴。
果然,聽到墨封訣的名字后,一直面無表的霍雨眠終於有了反應,眼簾微微的下垂,烏黑的睫羽如蟬翅般輕輕了。
Advertisement
半晌,才聽到極輕的聲音響起,堵在嗓子里的苦冒了出來,「我不想去想他的,可是腦子裡總是控制不住,浮現起關於他的畫面,他現在在哪裡?他現在過得好不好?有沒有吃飯?有沒有好好睡覺?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說著,眉宇間縈繞著揮之不去的痛苦,酸鑽進了鼻腔,衝上的眼底,驀地讓的眼眶一熱,水就泛了上來,連忙仰起頭,不讓眼淚落下來。
秦詩寧看著這幅樣子,心也是一痛,心疼的手牽住的,溫的勸著。
「哭吧,也許哭出來,你才會覺得好一些,我知道,這種事別人勸是沒有用的,總需要自己扛過這一道坎,沒有什麼別的辦法,只有堅持,慢慢的,一切都會變淡,即使還是放不下,但也不會這麼痛了。」
手心的溫度通過皮傳霍雨眠的心底,讓稍稍平復了下緒,深吸一口氣后,重新低下頭,溫和的看向秦詩寧。
「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經結束了,新的生活也要開始,我總不能一直活在回憶里,人總是要朝前看,放心,我都明白。」
短暫的沉默,兩個人面對面坐著,曾經的恩怨並沒有讓們現在的親昵變得尷尬,霍雨眠突然想起秦詩寧的況,斟酌著問出口。
「你就這樣走了,秦家那邊沒關係麼?真的可以就這麼離開?連招呼都不用打一聲了麼?」
提到秦家,如果說真的一點都不在意了,那是假的,可秦詩寧已經看得很淡了,應該說是在被一次次利用和拋棄之後,徹底死了心,對那個家失去了所有的希和熱。
「沒關係的,其實對他們來說,我本就是可有可無的,不過就是個利用工,現在徹底撕破臉,沒有用了就可以把我一腳踢開,而我也是一樣,他們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家人了,我現在的家人,是你們。」
霍雨眠看著這樣孤單又倔強的孩,想到那家人的臉,心裡不由有些心疼,反手握住的手,對輕輕一笑,聲音堅定而有力。
「我們是一家人,以後都不會再改變。」
……
第二天一早,墨靖珊的人就等不及的上門來催了,他們一家四口,終於在墨靖珊的督促下,離開了這座從出生起就生活在這裡的城市。
登上離開北城的飛機,霍雨眠看著屬於北城的天空,在自己的視線里漸漸消失不見,心裡竟然一片寧靜,比想象中的還要平和。
那一刻,的心裡就只有一個念頭,只期盼著墨封訣能夠一切安好。
今後一生都能頂天立地、彩奪目的活著。
……
英國,EIN醫院。
深夜,墨封訣他們所在的病房,突然有人從外面破窗而,墨封訣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聞聲立即起,並且迅速的站到墨傾雪前,擋著。
段狂和後手下落地后,第一時間解開纏在腰間的繩索,並在房門被外面的黑人打開前,迅速的先發制人。
在黑人沒反應過來之前,他們率先掌控優勢,再加上段狂手下帶的人個個都是頂級的高手,很快就將門外的那些黑人一一制服,一個個拿繩子捆起來,丟進房間里。
墨傾雪眼看著這場驚心魄,心有餘悸的站在墨封訣的後。
驀地,看著他的背影,的腦海中突然浮現起小時候,還很是疼這個弟弟,看他長得白白的,生怕別人欺負了他,經常在他上學的時候送他到班裡去,然後裝出一副霸氣的樣子,對其他人耀武揚威的說,這是的弟弟,是罩著的。
那時候的墨封訣,對此頗為不滿,可雖然他總是冷漠如冰,但每次送他去班裡時,卻從未說過什麼。
現在一轉眼,他已經長的比還要高出一頭,曾經白如酒釀丸子似的人,如今也了頂天立地的男人,可以站在的前保護了。
可他們之間,卻越來越疏遠。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起,他們姐弟兩人要站在對立面,看到對方,眼裡就只要厭惡和麻煩了呢?
「說,你們的頭是誰?說不出幕後黑手來,廢了你的胳膊,不過是小事一樁。」
段狂冷凝的聲音拉回了墨傾雪飄遠的思緒,往旁邊錯了兩步,和墨封訣肩並肩站著,面也冷下來,沉沉的看著跪了一地的黑人。
黑人本想守口如瓶,可就在段狂一隻手住了他的肩膀后,劇烈到難以忍的痛頓時襲遍全,他疼的齜牙咧的說不出話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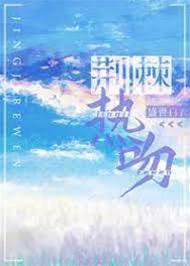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