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追了!厭世大佬攔腰纏吻!》 第11章 薑絨真難哄
因為隔著聽筒,他沒聽清對方的聲音,但能清楚知曉,的確是個男人。
薑絨眉頭皺的越發厲害,他和薛雅總是晚上出去玩,從來沒告知過,現在又為什麽要來管?
薑絨溫淡聲線冷靜道:“祁盛,你管我。”
祁盛猛然一噎。
反應過來時,薑絨早就掛了電話。
他心裏驟然生出一無名火,胳膊揚起,手機被砸在了地板上,四分五裂。
……
聚餐是每年的慣例,薑絨想不出推的理由。
出發祁家之前,薑建平緩和了臉同講:“飯桌上,多和阿盛講講話。”
往常薑絨回來,總能看見和祁盛視頻或者語音通話,但這幾次,一回也沒看見過。
薑建平不得不多留個心眼。
薑絨已經和他說過,祁盛不可能娶自己的事,但他顯然不願意相信,既然這樣,也沒必要多費口舌去解釋了。
“知道了。”
語氣平平的應聲。
抵達祁家時,祁家人都在,除了祁煜。
有關祁家的家庭活,他一向參加的,甚至是從不參加,祁家人也不會主提他。
不知道為什麽,明明以往不會覺得有什麽,但現在,看著祁家人其樂融融的樣子,薑絨心裏有點不舒服。
“絨絨來啦,這可是我們今天的小主角呢,快進來。”
Advertisement
祁母雖年過半百,但保養得當,瞧著也就三十五六的年紀,一瞧見薑絨,臉上頓時洋溢出了笑容,很是和藹可親。
薑絨也衝出乖巧笑臉:“伯母好。”
祁母拍拍的手,又看向正坐在沙發上打遊戲的祁盛,提醒道:“阿盛,趕過來給你薑伯父他們拎東西。”
薑家人自然不可能空手過來。
祁盛頭也沒抬說:“再等兩分鍾。”
祁母皺眉道:“這孩子,就是玩心太重了!一點事也不懂。”
這種事以前也不是沒發生過,那時薑絨不覺得有什麽,但現在隻覺得,祁盛他真的連最基本的禮數也沒有。
或許是有的,但隻是對而言沒有。
因為不重要,所以這些也就不在乎了。
薑建平倒是不在意道:“這些東西也沒多重,那需要這麽多人來拎呢,更何況家裏還有傭人呢。”
話說完,一旁的傭人有眼力見的將他手裏的禮品提走了。
薑絨來過祁家很多次了,對而言,這裏並不陌生。
“絨絨,你和阿盛坐在一塊兒。”
祁母指了指祁盛邊的空位,薑建平的眼神也虎視眈眈的看向。
薑絨心裏歎了口氣,到底是沒違背兩位家長的意思,纖細影走過去,悄無聲息的坐了下來,沒像過往那般同祁盛打招呼。
祁盛手中的遊戲突然打得沒意思了。
他直接掛了機,看向薑絨,問:“早上那個男人是誰?”
他還在想這事。
薑絨懶得搭理他,隻當作沒聽見。
這般冷漠姿態,祁盛以前從未驗過,他心裏似乎被什麽東西撓了下,刺痛著的悶。
他有點想煙了。
“薑絨,我們談談。”
他說的大聲,薑建平以及祁母他們都聽見了,薑絨抿了。
“行。”
點了頭。
兩人走向了後院。
祁母若有所思的看向兩人的背影,薑絨不像從前那樣,跟在祁盛後,反而主拉開了一段距離。
薑建平笑嗬嗬道:“年輕人嘛,有時候總會吵點架,我們年輕那會兒不也這樣?吵一吵,反而更好。”
祁母也笑:“吵一架才好呢,絨絨這孩子就是脾氣太了,這樣倒還能管住點阿盛。”
祁煜的企業越做越強,祁盛卻還是一心撲在其他事上,真擔心未來有一天,祁父會突然反悔,決定把祁氏給祁煜。
那樣祁盛可就真的什麽都沒了。
祁家的後院是心打理過的,如今正當夏天,鮮花盛開的好時節。
五六的花朵姹紫嫣紅的簇擁著腦袋綻放,淡淡花香盈鼻腔,薑絨慢條斯理的深呼吸了一口。
心暢快了不。
“你的生日禮。”
祁盛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黑絨盒子。
薑絨看了看,手上沒作。
祁盛忽然苦笑了聲,“我現在就這麽令你討厭嗎?連禮都不準備接了?”
“薑絨,我們到底是一起長大的。”
布滿顆粒的下,孩細的長睫很輕的眨了眨。
“不要了。”
靜默幾許,朝祁盛搖了搖頭。
他送禮給,被薛雅知道了,又要來計較,懶得陷這樣的三角關係。
沒想到還是選擇拒絕,祁盛臉一僵,他沉了臉,不管不顧的抓住薑絨的手腕,打開絨盒子,是一條的鑽石手鏈。
“你幹嘛?”
薑絨想躲,祁盛力氣比大多了,掙不開,鑽石手鏈被強製戴上了腕骨。
“不許摘。”祁盛說:“你摘了的話,我現在就去告訴薑伯父,你拒絕我送的生日禮。”
手鏈在的折下更添幾分。
薑絨去摘手鏈的作頓住,嘲諷的扯開角笑了笑:“隨你。”
手鏈被放到了一旁的小圓桌上。
背對著祁盛,心平氣和的同他講:“祁盛,這些禮你以後送給薛雅會更好。”
比起而言,薛雅應該會更喜歡。
祁盛死死盯著孩離開的背影,他煩躁的了頭發,不明白為什麽現在的薑絨這麽難哄了?
以前明明不過是幾句話的事。
重新回到祁家,晚餐已經準備開始了。
薑絨坐在了許茵旁邊,祁老爺子和祁父也紛紛來了。
“祁爺爺,祁伯父晚上好。”
薑絨挨個乖巧的打了招呼。
祁老爺子年過古稀,兩鬢早就斑白一片,平時總是笑容居多,讓人覺得親近。
“有段時間沒見,絨絨又長漂亮了許多。”
說完,銳利眼神又看向沒出聲的祁盛,眉宇皺了不:“你這臭小子,今天絨絨生日,禮都沒準備一個?”
其實最開始,祁盛記不住生日的。
是祁家人一遍遍的在他耳邊念叨,他嫌煩,這才每年應付般的給準備了生日禮。
一晃過去,也有二十二年了。
祁盛譏諷的起眼梢,滿不在乎的答:“沒準備。”
他沒說手鏈的事。
祁老爺子眼睛一瞪:“臭小子!”
祁父也道:“也就絨絨格好,不和你計較這些事。最遲明天晚上,你得把生日禮給絨絨送去。”
薑絨盯著祁父的臉,忽然走了點神。
想,祁盛其實長得更像祁父一點,祁煜不怎麽像。
小時候便聽大人們講,祁煜長得更像他母親,他母親是京宜著名的“小神”,當年在戲臺上的票稱得上一句萬人難求。
可惜自古紅薄命。
祁煜從一出生就沒了母親。
“想什麽呢?”
這時,許茵推了推胳膊,薑絨回過神來,正好聽到祁老爺子問:“絨絨,你同不同意?”
同意什麽?
薑絨剛才沒聽他們大人之間說了些什麽。
薑建平見這沉默的木頭模樣,心中更不喜,搶先回答了:“能有什麽同意不同意?肯定是願意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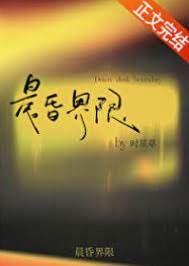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