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詩重提》 第99頁
向繁洲怔愣著,回頭,眼神中的變得復雜,仿佛在說:那你在這繞半天彎子,到底什麼意思?
門外,有腳步聲,很輕。
向啟淞明白定然是孟玉臻在外面,只是向繁洲本無心注意這些細節。
“坐,”向啟淞耐著子說,“別整得我們跟仇人似的,說兩句話就要走,你年紀不小了,沉穩點行不行?”
見對方語氣緩和,向繁洲才勉強賣個面,坐回來,向啟淞也離開了書桌,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
向繁洲這人和長輩關系理得都不錯,就是從小和他爸這關系跟風似的,總有堵不完的,明明也說不出有個什麼矛盾,卻總是一言不合就嗆起來,不歡而散。孟玉臻在其中斡旋了一次又一次,這關系裂了又補,補了又裂,循環往復,跟沒盡頭似的。
這次顯然向啟淞在著氣,控制局面,倒引得向繁洲生出些歉疚。他默默回想了一下剛才爭端發生的過程,似乎都是他自己在扔緒炸彈,老向倒始終沒說什麼重話,連開場也是在關心他的近況,想自己確實有點莽撞了。
Advertisement
他略微頷首了一下,卻沒道歉,他說不出任何。這樣的對白本不會出現他和向啟淞之間,心照不宣似的,他們向來都是用行和好,從未有言語上的過渡,仿佛總覺得這話黏黏糊糊的,不夠颯爽。
“我是想說,你也老大不小了,喜歡哪家的姑娘,就領家里看看,”向啟淞語重心長地說,“不要拖泥帶水的,跟誰都糾纏不清,做男人得有點擔當。”
向繁洲一轉頭,恍然看到了向啟淞眉宇的滄桑,卻又在下一秒捕捉到了他眼中的清明,開悟般心頭松,意識到自己從不曾真正認識向啟淞。
他的父親也不曾是他所主觀臆斷的那般獨斷專行。
作為大院子弟,向啟淞似乎總是特立獨行的。退伍后,沒有和邊的人一樣走上仕途,而是去學了醫。協和醫學院博士畢業,進國一等一的頂尖醫院工作,卻又因為去偏遠地區醫療支援時深深到國醫療水平的落后,果斷投到了醫療械開發與制造領域。
在最難的階段,著石頭過河,填補了國醫療械領域的空白。深耕數十載,甚至這個年紀仍一線,致力于推醫療事業的進步發展。
這樣的毅力和決心非常人所能及。
向繁洲也是創過業的人,怎麼能不懂向啟淞,只是他好像一直都在陷自己的迷障,好似溫室里長慣了,覺得一切都是應得的,所以潛意識一直都未原諒向啟淞于兒時缺席的陪伴。
這一刻,向繁洲如夢初醒般深刻悟到向啟淞好像真的老了,向啟淞已然不是那個肩膀寬厚,永遠英姿發的中年人,是他常常把自己當個孩子,無止境地在親近的人邊喧鬧,不愿長大,不愿胎。
大抵也是他自己太清楚,他就算鬧著脾氣,這些人也不會因此而離開。很多東西對他來說,生來就是易得的,所以他似乎也不曾懷自己的幸運。
離開向家別墅的時候,向繁洲都是懷著歉意的,出門前,著目送他離開的向啟淞和孟玉臻凝良久,分別朝兩位深深鞠了一躬,才走。
向繁洲回到漫云的住,一眼就看到了客廳擺著的那一大束花,難以名狀的特別與難忘,卻很像何慕,世獨立。
客廳的燈是關著的,他卻覺到臥房有亮溢出,輕輕推開門,床頭的燈果然是開著的,昏黃卻溫暖和。
那打在何慕裹著的被子上,還有頭發上,只有數映在臉上,卻始終令人覺得心安。
他忽然想起,幾次到何慕睡著,邊都是有亮的,后知后覺自己馬虎心。他京市和今浦的房子,都用的遮極好的窗簾,燈滅時漆黑一片,那麼怕黑,一個人一定睡得不安穩。
向繁洲被催著,俯吻。
何慕睡得糊涂,半明半昧中覺有寒的氣息鉆過來,又似有人從后抱,作溫,下意識翻,鉆過去攬他的脖子。
結果,向繁洲反倒被何慕親了,甚至沒事人似的,抱著他不松手,一個勁往他懷里鉆,嚶嚀出聲,甚是依賴。
他的心得一塌糊涂,就這般任抱著,卻又忍不住吻。
何慕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夢,總覺得向繁洲回來了,這味道悉得很,跟真的似的,條件反般張著小口回應他。
雪松氣息帶著約的酒氣,與清冷的花果香纏在一起,溫熱的呼吸愈發滾燙,兩個人的也開始升溫。
直到覺舌開始酸疼,何慕才驀地睜開眼,仍未分辨出現實還是夢境,手臂僵住,睜大了眼睛看正與接吻的人。
向繁洲覺到的停頓和遲疑,安般額頂的頭發。
何慕目中帶了點木然,仿佛認不出他似的凝了好一會兒,最后眼睛帶著水氣地再次將他抱。
他挲著的腰肢竊笑。
而何慕卻覺得自己在重疊的夢中。
第一重夢,鵝大雪紛紛揚揚下了三天三夜,京市碧瓦朱檐的古建筑和星羅棋布的現代高樓都落了白。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43 章

春色難馴
江城時家弄丟的小女兒終于回來了。 整個時家,她要星星還強塞月亮。 —————— 二中開學,時年攬著好不容易找回來的妹妹招搖過市。 眾人看著那個被時年夾在咯吱窩里,眉眼如春的小姑娘,紛紛誤會,“小嫂子絕了,絕了啊。” “想什麼呢?!”時年忿忿,“這是我妹!” 時·暴躁大佬·年,轉頭笑成智障,“歲歲,叫哥。” 此時,一位時年的死對頭,江·清貧(?)學神·頂級神顏·骨頭拳頭一起硬·馴,恰巧路過—— 椿歲哥字喊了一半,就對著江馴甜甜一聲,“哥哥!” 江馴看著這對兄妹,鳳眼微掀,漠然一瞥,走了。 時·萬年老二·考試總被壓一頭·年:“???”啊啊啊啊你他媽什麼態度?!所以為什麼你連哥都比我多一個字?! —————— 時年曾經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江馴踩在腳下,讓那個硬骨頭心甘情愿叫他一聲“哥”。 直到看見死對頭把他親妹子摁在墻角邊(沒親,絕對沒親)。 時年真的怒了,“你他媽壓.我就算了,還想壓.我妹??!!” 江馴護著身前的椿歲,偏頭懶聲,“哥。” 椿歲:“…………” 時年:“???”啊啊啊啊別他媽叫我哥我沒你這種妹夫!! —————— 小劇場: 椿歲:“為什麼裝不認識?” 江馴:“怕你喜歡我啊。” 椿歲嘁笑,“那為什麼又不裝了啊?” 春夜的風,吹來輕碎花香。 江馴仰頭,看著枝椏上晃腿輕笑的少女,低聲笑喃:“因為……我喜歡你啊。” #你是春色無邊,是難馴的執念# 冷漠美強慘X白甜小太陽 一句話簡介:我成了真千金你就不認識我了? 1V1,HE,雙初戀。不太正經的治愈小甜文。
16.3萬字8.18 6106 -
完結1181 章
余生悲歡皆為你
婚前,她當他是盲人;婚后,方知他是“狼人”。 * “你娶我吧,婚后我會對你忠誠,你要保我不死。”走投無路,喬玖笙找上了傳聞中患有眼疾、不近美|色的方俞生。 他空洞雙眸毫無波瀾,卻道:“好。” 一夜之間,喬玖笙榮升方家大少奶奶,風光無限。 * 婚前他對她說:“不要因為我是盲人看不見,你就敢明目張膽的偷看我。” 婚禮當晚,他對她說:“你大可不必穿得像只熊,我這人不近美|色。” 婚后半年,只因她多看了一眼某男性,此后,她電腦手機床頭柜辦公桌錢包夾里,全都是方先生的自拍照。 且看男主如何在打臉大道上,越奔越遠。
216.9萬字8 12334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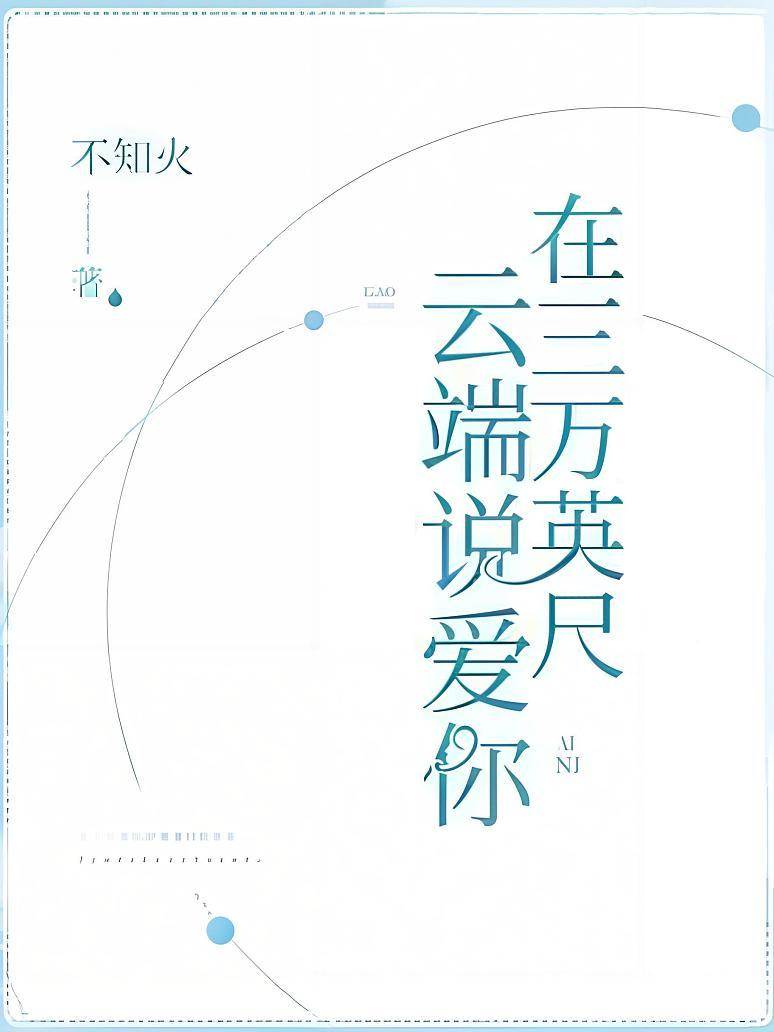
在三萬英尺云端說愛你
高考過后,楊斯堯表白周月年,兩人在一起,但后來因為性格不合,和楊母從中阻撓,周月年和楊斯堯憤而分手。分手之后,兩人還惦記著對方,幾番尋覓,終于重新在一起。周月年飛機故障,卻因為楊斯堯研制的新型起落架得以保全生命,兩人一同站在表彰臺上,共同迎接新的生活,新的考驗。
18.2萬字8 3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