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小叔》 第721章 糖霜
近水樓臺先得月,沈驍九的后院清凈不清凈,可沒幾個人比沈南意還清楚了。
林煌環顧四周,確定這地方藏不住十八個人之后,開始苦思起索圖等人的藏之地來,照沈驍九所說,書房里滿是珍寶字畫以及朝廷文,多著呢,那十多個外邦人,又都是五大山的武夫,沈驍九定不會讓他們住在書房。
不在書房,不在練武場,也不在武庫,就只可能在客房了。
但客房能有多大,才能裝下十九個大男人呢?
但再想想,他們都是一群大老,說不準一個房間便能睡上五六個人,這樣算來也能裝下,一時有些拿不準主意了。
旁敲側擊沒用,看來只能直接問了,同沈驍九等人也算是一起出生死過的,隨口一問,應當不要吧?
“劉懷恩與趙大德一死,金州的事總算是落下帷幕了,想起一路來京也極為不易,”嘆了兩句,林煌話鋒一轉:“說起來,怎的不見索圖大哥一行人,他們是外邦人,許久未見,也不知在京城能否待得慣?”
Advertisement
沈驍九笑著用瓷蓋將杯中漂浮著的茶葉撇到一邊,頭也未抬,“羅風同我提起過,前幾日他去尋索圖時,你恰好也在香珍居,實在算不上是許久未見吧。”
林煌眼可見的慌起來,臉也被臊的通紅,拿起塊兒紅棗糕在手里,卻不知道吃,慌忙解釋:
“正是如此,那日見他們在香珍居用飯,我本上前閑話幾句,可惜自己不勝酒力,被同桌幾位好友勸酒幾杯就醉倒在桌上,等醒來人已在客棧。之后想來頗為憾,這才有此一問。”
“才來京城十日不到就結了能把酒言歡的至好友,林公子果然厲害。”
沈南意抿笑,論起諷刺揶揄人,大概世間有人是他的對手。
“索圖等人野難馴,又不知輕重在香珍居大放厥詞,批判指點朝廷之事,險些鬧出事來,故而我將他們放到玄狐山罰去了,沒個十天半個月是回不來的。”
并未意識到沈驍九在提點自己不要在外人面前議論皇帝和朝廷之事,林煌將目放在了玄狐山三個字上。
玄狐山,玄狐山,得到了地址,林煌這才放心咬了一口手中的紅棗糕,在心里默念了兩遍這個名字后,再度端起茶杯,思緒也跟著飄遠,“如此是該罰,該罰。”
等羅風將人送走,一碟子花生糖也被沈南意吃了個。
沈驍九練的拿出手帕為沈南意拭手上沾的糖霜,的纖纖玉指白如削蔥,指甲圓潤晶瑩,比花生糖上裹著的糖更加人。
沒注意到沈驍九眼底的癡迷,沈南意盯著他又長又濃的睫看的出神,“你這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
沈驍九裝傻,“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沈飛茹出嫁那日,祝飛花帶著一樽青玉羊頭前來賀喜,可擺明了是送給你的,當時我就覺得有鬼了!此事過后沒多久你就趕往金州,潛去了西玥,還帶回來索圖和一群西玥人,眼下祝閣老又派人來打探索圖等人的下落……”
沈南意分出一縷青拿在手里把玩,沖他俏皮的眨了眨眼睛,“你可別想騙我!說吧,到底那樽羊頭究竟和西玥有什麼關聯?”
“能將這些事都串聯起來,看來你比我想象的要聰明。”
沈驍九從來不吝嗇對的夸獎,略微思索了一番,他調整了坐姿,神嚴肅的看向,“此事要從很早之前開始說給你聽,不過在這之前,我有個問題想要問你。”
見他如此煞有其事,沈南意趕忙將手里的頭發放下,端正好坐姿,“什麼問題,竟值得你這般嚴肅?”
“此事與我的世有關。”
猜你喜歡
-
完結1250 章

法醫王妃:我給王爺養包子
坊間傳聞,攝政王他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蘇七不過是從亂葬崗“詐屍”後,誤惹了他,從此他兒子天天喊著她做孃親。 她憑藉一把柳葉刀,查案驗屍,混得風聲水起,惹來爛桃花不斷。 他打翻醋罈子,當街把她堵住,霸道開口:“不準對彆的男人笑,兒子也不行!”
216.9萬字8.18 52483 -
完結2007 章

神醫狂妃:娘親你馬甲又掉了!
大齊國的人都以為瑾王妃只是個寡婦,瑾王府也任人可欺。可有一天,他們發現——神醫門的門主喊她老祖宗。天下第一的醫館是她開的。遍布全世界的酒樓也是她的。讓各國皇帝都畏懼的勢力是她的外祖家。就連傳說中身亡的夜瑾居然都回來了,更是將她疼之入骨,寵入…
181.2萬字8 94733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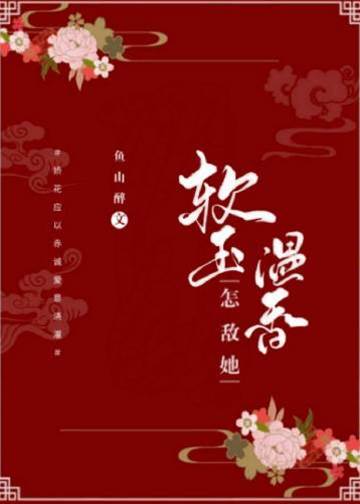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1801 -
連載2178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4.1萬字8.33 4778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