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宮殺,公子他日日嬌寵》 第530章 番外一:公子許瞻(六)
刺殺不過是個開始,薊城從來都是危機四伏,暗流涌。
魏使的國書敕封為嘉福郡主,呵,寓意雖好,虛名罷了。
不過是將與魏國牢牢拴在一起,這不是好事。
孤這三年都在與的陣營較勁,是什麼人,該站哪一隊。
是魏人,但不該做魏國的刀。
他日若仍有黨派紛爭,仍有奪權暗刺,都得站在孤的一旁,唯孤能護周全。
不該卷進列國的爭斗,亦不參進薊城的黨派。
總會是孤的人。
總有一日。
罷了,不提壞事。
這一年,孤最好的消息也都是關于。
一塊完璧。
干干凈凈,清清白白。
純粹得像個傻子。
孤不知有多歡喜。
孤笑,孤俯上前,命看孤,一次次挲的頸烏鬢,孤不釋手。
仍如從前一樣乖順,但目躲閃,不知在想什麼。
孤聽見的心跳得厲害,見的臉紅得似要燒起來,孤就看著一分分、一寸寸地把自己折了進來。
這樣的傻姑娘,躲著,避著,總顧而言他,垂頭要往后退。
但孤再不許回避。
孤的指腹在的瓣上細細挲,每挲一寸,的臉便紅上一寸。
孤聽見的心如敲鑼打鼓。
孤想,不急。
小七,不急。
許瞻,你也不要急。
總會看清自己的心,也總會為你留下來。
莊王十六年四月二十六,孤的生辰。
孤第一次與母親提起迎娶小七的事,便是在這一日。
Advertisement
母親不肯,在心里,能做蘭臺夫人的必是大國公主抑或簪纓之。說小七是魏俘,這樣的份是輕賤了孤,更是輕賤了燕國。
母親曾掌控孤的一切,然關于小七,孤意已決,執意要娶,半分也不肯退讓。
孤在宮宴上飲了酒,因急著見,早早就回了蘭臺。
那時蘭臺天青青,降著小雨。
在碎花亭閑坐,白木蘭映著那寒玉簪水般的臉,不自知,那一顰一蹙,皆落在了孤的心坎。
孤記得將最的木蘭于的髻上,記得將攬進懷中,記得將從雨里抱起。
就在傘下,就在孤懷里,似小一般乖乖蜷著,地瞧孤,孤都知道。
孤想,你瞧,許瞻,慢慢來,你不必急。
孤尤與對酌,看那張不施黛的臉漸漸被酒染人面桃花的模樣。
孤尤的采桑舞,翹袖折腰,長服曳地,就在孤面前翻卷出好看的袖花來。
孤也尤與閑話,就坐在孤一旁,暖黃的燭將籠著,春人,孤怎麼都看不夠啊。
醉意朦朧,孤仿佛也跟著去了桃林,養一條狗,去當壚賣酒,為滌,去聽路過的客商說起那些天南海北的見聞。
可真是個了不起的姑娘。
竟懂那麼多。
孤問,“小七,高興嗎?”
笑得真啊,說,“高興。”
孤問,“你說要當壚賣酒,那誰為你滌呢?”
說,“自然會有旁人。”
孤問,“會嫁給大表哥嗎?”
微醺笑著,說,“也許會罷。”
孤心中一嘆。
的以后沒有“公子”。
但孤不急,孤取來早就備好的木犢,孤說,親一口,就給你。
為了木犢,第一回親了孤。
溫溫熱熱的淺淺覆來,不過須臾。
不過須臾就將孤的心
全都抓了起來。
孤抬手想去捧住滿頭的烏發,卻只抓到一片袍角,就連那袍角也很快離開了孤的指尖。
孤心神微,眸中恍然。
孤知道自己醉了。
孤起時子輕晃,忍不住環住了的腰。心里有千句萬句,出口時卻只凝一句輕嘆。
小七。
這低賤二字,竟不知何時起,已了孤最好的話。
孤借酒問,小七,留在蘭臺不好麼?
猶豫了一瞬,沒有說“不好”。
那便好,那孤便等。
也是這一夜,孤那好堂弟許牧星夜集兵,終于反了。
孤候他多時。
一招請君甕,就他的鐵甲騎兵大潰而散,死傷無數。
許牧率殘部往城門逃竄,孤早在城樓布下虎賁等候,殺一個喪家之犬易如反掌,原本毫不費力。
那喪家之犬說,要送孤一份大禮。
呵,大禮。
孤鋪謀定計,殺伐果決,沒有什麼能要挾得了孤,他該知道。
但孤不曾想到,許牧的大禮竟是小七。
晨熹微,東方既白,上的麻袋旦一扯下,便出了那張煞白的臉來。
孤沒有肋。
沒有。
許牧該知道,王叔該知道,這天下諸人都該知道。
孤拉滿了軒轅大弓,而連一聲哀求哭泣都沒有。
心堅,孤知道。
冰雪聰慧,也該知道孤的心思。
孤朝許牧張弓拉箭,那利箭穿風破曉,直直進了那反賊的腦門。
你瞧。
孤箭甚佳,從無一分差池。
是日的兵變收鑼罷鼓,此時已是天大亮。
孤踩著滿地尸去尋,見了孤便往后退去。
怕了孤。
但這便是權力場。
你死我活,十分尋常。
也許去四方館報過信,也許與叛賊有牽連,不該出現在城門,孤都知道。
但孤不曾怪罪。
不疑,亦不曾想過殺。
問過孤,公子不怕奴果真背棄公子嗎?
孤也不知。
孤能翻攪風云,宰割天下,但孤不知的心思。
孤當真怕將自己折進去。
孤唯有正勸告。
“小七,離他們遠遠的,永遠不要卷進來。”
但愿能記住。
要記得死死的,要烙進腦中,要刻在心里。
這一日,孤帶進宮,命去聽、去看。
孤有心去試,看到底是不是孤的人。
但口中沒有一句實話。
沒有,那便不是孤的人。
是,盯著孤腰間的璽紱,說著氣話,說,奴是魏人,做不了公子的人。
還說,奴總是要回魏國的,那里有奴的父親母親。
生辰那日短暫的親近,再也沒有了。
孤心里何嘗不氣,孤嗤笑一聲,告訴,什麼嘉福郡主,追封毫無意義。
雙眸通紅,但沒有哭出一點聲音。忽而卻又笑了起來,到底說出了心里的話。
說,公子嗜殺殘暴,不配做北地之主。
孤。
孤將
趕下馬車,命跣足行走。
孤命下車,便下車。
孤命跣足,便跣足。
一句也不肯求孤,一句錯也不肯認下。
但凡肯說句話。
罷了。
孤在蘭臺坐臥不寧,然竟去了扶風。
呵。
孤星夜尋去,挎劍立馬,徑廳堂。
蘭臺的東西,誰人敢搶。
人。
君位。
王叔覬覦燕宮由來已久,孤與王叔的恩怨亦早已理不清楚了。
孤五歲隨父伐楚,王叔曾設計將孤虜至燕營,孤險些死于楚人劍下。
若不是敵軍主帥將孤送回父親的中軍大帳,孤早就客死異地,燕國也必將一敗涂地。
孤猶記得那時敵軍主帥是楚國的七公子,那是個儒雅的文人,孤雖記不清他的眉眼,但記得他眸溫和。
孤是后來才知道,七公子就是的父親。
他的手曾輕孤的頭顱,孤至今尤記得父親的話。
他說,“稚子無辜啊。”
聽說楚國敗后,七公子回國刑,后來竟不知所蹤,再無人知道他的消息。
狼若不死死咬住狐貍的咽,狐貍終究要尋機給狼以致命一擊。
王叔啊,那只狐貍。
他又從孤這里討到了什麼便宜,孤的獵犬撕了他的,吞了那孩子半只腳。
他年長孤十歲,自此再不敢小看于孤。
呵。
真是個倔強的人吶,孤命上車,竟不肯。
只自顧自往前走,孤不遠不近地跟著。
孤想,不審,不叱,不辱。
再不棄于鬧市,亦再不鎖于危樓。
孤還想娶。
但抗拒孤,死死掐住了孤的手,指甲深陷,掐掉了孤一層皮。
說,君侯是好人。
信了那只狡詐的狐貍。
不信孤,卻信一個謀面不過半日的人。
孤的心寸寸滴。
在心里,孤暴戾嗜。
同室戈,誅自己的父輩兄弟。
輒征戰,屠列國的兵卒百姓。
可孤就只是這樣的人麼?
孤不知道。
但真真正正地是站在了孤的對面。
孤最怕的事,就是不做孤的人,最怕做孤的敵人。
孤第一次害了怕。
孤將拽來,按上短案,扣住的脖頸傾覆下,去啃噬的舌,去撕扯的袍。
孤要縛住的雙手。
孤要占有。
孤一心要娶的人,得是孤的人啊。
但厭孤至極。
拼了命去推、去躲、去掐,策目切齒,痛斥說,“這世間怎會有公子這樣的人!”
孤是怎樣的人啊。
大聲地告訴孤,公子是不得人心的人。
孤心如刀刺。
原來孤竟是這樣的人。
可有人便夠了,要心干什麼。
多余。
跳下了馬車。
孤沒能抓住的袍。
厭孤,惡孤,寧死也不肯全了孤。
說要干干凈凈地回去。
在眼里,沈晏初好,良原君好,只有孤是惡人。
孤不死心,孤問,小七,你的將來該是怎樣的?
說,奴的將來,該在魏國。
孤,痛心骨啊。
孤說,你不走,我娶你。
但。
背過了去。
雨打窗棱,聲聲切切,如萬箭穿心。
孤險些掉下淚來。
暮春的雨無盡頭地下,孤就在木蘭樹下守著,守了數日深夜。
聽說燒了木犢,也不要孤的小狼,但有一夜,推門出來,就在木紗門外痛哭出聲。
孤的心已是千瘡百孔。
孤跪坐一旁,將攬懷里。
孤問,“小七,你想要什麼呀,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可沒有說話。
只想走,因而什麼也不要。
孤不知如何取悅,因而帶進宮見母親。
母親應了孤要好好勸,母親說的話,大抵會聽一聽。
路上孤送木梳,朱紅的梳子,繪著一朵木蘭,孤做了兩個日夜,十分喜歡。
孤想為簪上,但卻本能地躲開。
說,奴以為公子要打。
是,孤在眼里是個暴戾嗜的人。
孤定定,木蘭梳子在掌心,再也送不出去。
孤告訴,孤亦能為濯足。
但并不領。
這日家宴,母親借口打發孤與阿蘩阿婭一同去看父親,單獨留一人說話。
們說了許久,孤回去時,見髻上簪著母親的釵。
孤想,不管從前母親怎樣,但若能留下小七,那便是世間最好的母親。
可要離開時,孤聽見了母親的嘆息。
母親只說,可惜。
孤便明白了。
孤曾問,孤愿意娶,你可愿嫁?
然不愿。
燕莊王十六年農歷五月二十一,扶風滿月。
就是這一日,王叔也手了。
許慎之引出去時,孤知道不會簡單。
但孤握住的手,選擇了信。
回廳堂時,扶風的形勢已然顛倒逆轉。
孤附耳問,眼里凝淚。
那些眼淚出賣了,可一句實話也沒有。
你看,即便孤要娶,也仍舊不是孤的人。
背棄了孤。
孤借故離席,而大門闔。
這青天白日,扶風已是天羅地網。
一個個黑死士,手中兵刃凜凜。刀刀致命,下得都是死手。
孤拔出青龍劍,依舊將護在后。
孤說過,信與不信,都會護。
孤想,許瞻,你何必怪。
才十六,何必怪。
孤沒有怪,亦不曾將當作敵人,因而依舊把脊背留給了,就似獵將后背留給了獵人。
但抱住了孤。
為孤擋了一刀。
那刀從的發髻中間砍了下去,削斷了的青,劈裂了的木梳,劃上了的脊背。
孤寧愿這一刀砍在自己上,孤在背水拼殺的間隙想著,許瞻,心里是有你的。
孤心疼,但也真心歡喜。
孤推開了,要去找王叔。
孤知道王叔喜,必不會殺。
可磕磕絆絆地沖進那片廝殺的戰場,孤不知要干什麼。
孤只知要護住,只知持劍跟在后,短兵相接,白刃見。
孤想,孤得護好啊。
信與不信,都要護。
即便遍鱗傷,皮破流。
猜你喜歡
-
完結232 章
腹黑郡王妃
一覺睡醒,狡詐,腹黑的沈璃雪莫名其妙魂穿成相府千金.嫡女?不受寵?無妨,她向來隨遇而安.可週圍的親人居然個個心狠手辣,時時暗算她. 她向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別人自動送上門來討打,休怪她手下不留人:姨娘狠毒刁難,送她去逛黃泉.繼母心狠手辣,讓她腦袋開花.庶妹設計陷害,讓她沒臉見人.嫡妹要搶未婚夫,妙計讓她成怨婦.這廂處理著敵人,那廂又冒出事情煩心.昔日的花花公子對天許諾,願捨棄大片森林,溺水三千,只取她這一瓢飲.往日的敵人表白,他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心,她纔是他最愛的人…
155.2萬字5 59507 -
完結752 章

盛世凰歌
擁有精神力異能的末世神醫鳳青梧,一朝穿越亂葬崗。 開局一根針,存活全靠拼。 欺她癡傻要她命,孩子喂狗薄席裹屍?鳳青梧雙眸微瞇,左手金針右手異能,勢要將這天踏破! 風華絕代、步步生蓮,曾經的傻子一朝翻身,天下都要為她而傾倒。 從棺材里鑽出來的男人懷抱乖巧奶娃,倚牆邪魅一笑:「王妃救人我遞針,王妃坑人我挖坑,王妃殺人我埋屍」 「你要什麼?」 「我要你」
132.9萬字8 10928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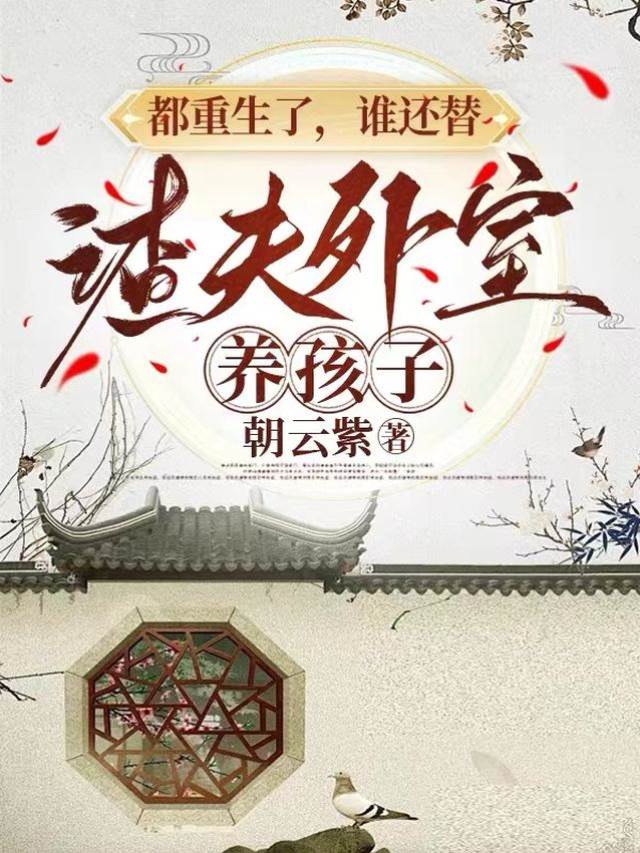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