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宮殺,公子他日日嬌寵》 第111章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小七不愿聽這種話,便揶揄,“姐姐喜歡便自己留著。”
槿娘臉一白,立即住了,手中的狼崽一時不知該往哪里放,就只是任由它好奇地東瞅西看。
片刻又將狼崽送了過來,“公子給的,你便留下,多好的事兒呀!”
小七想起從前許瞻的話來,那人說,“我給你的,你便得著。”
便也接過了狼崽,應道,“哦,好。”
槿娘眉開眼笑,“公子若知道了,必定高興!小七,你給它取個名字吧!”
小七莫名一嘆,哪里會取名字,連自己的名字都不出口。
見槿娘目炯炯地來,著狼頭,低聲開口,“那就小八。”
取了個與一樣低賤的名字。
槿娘一呆,片刻道,“姑娘還是再想一想罷。”
狼崽哼唧哼唧了兩聲,不知到底是贊同還是反對。
小七笑道,“就小八。”
槿娘也不再說什麼,安頓好了與小八,便又忙活去了。
半晌又端著湯藥湊了過來,“方才公子來了,公子問,姑娘給小狼取了個什麼名字。我便說,姑娘說‘小八’。公子好一會兒沒有說話,公子大抵以為姑娘會起一個像雪狼那樣的名字。”
小七垂著眸子,“我本來也不想要。”
Advertisement
槿娘便笑,“公子后來也覺得‘小八’這個名字很好,他說既是姑娘的狼,便小八。”
小八很粘人,因才出生沒多久,大抵果真以為自己是犬,倒是溫順,瞧不出一點狼,總窩在小七邊蹭來蹭去。
但小七并不怎麼抱它,抱得多了容易生出來,因而極去。
除了小八,那人還命鄭寺人送來許多錦緞履,不拒絕卻也不用,大多都由槿娘收了。
從前送到聽雪臺的,全都進了槿娘的柜子里,如今槿娘也什麼都不要了。
全都束之高閣。
除了母親留下的
桃花簪與沈宴初的云紋玉環,小七并不看重外之。
外之都是留不住的。
將來蘭臺與扶風一戰,輸的人連尸骨都不會剩下,要這外之干什麼。
蘭臺若輸,就連這府中的亭臺樓閣也都將化為灰燼。
還是以帛帶束發,穿婢子的袍,比從前還要乖順聽話。
那人又往聽雪臺送來木牘。
先前的一百二燒了灰燼,他又重寫了新的,將從前的補了,又額外多給了一百。
這便有了二百二十枚明刀。
小七拿在手中的時候,心里百味雜陳。
如今也不過是些竹片罷了,蓋了大印也并沒有什麼用。
皆是死。
哄玩而已。
他愿意哄,便也收下了,盈盈道了謝,也并不多說什麼。
從前還與他談禮法,談條件,如今什麼都不提。
隨手放在案上,不多看一眼。
槿娘嘮嘮叨叨地把木牘收了起來,“你從前恨不得日帶在上,怎的就堆在這里,仔細被小八叼走了,哭都沒地方哭去。”
清醒了,槿娘又憨傻了。
收到了什麼地方,小七也不去問,由著槿娘去收,沒什麼所謂。
了夜又下起了雨。
借著燭,能看見木蘭樹下依舊人影微晃。
先前只當是自己眼花,如今卻確定,樹下的一定是個人。
是個人。
沒有錯。
因為聽見有人在咳。
極力抑的咳聲,在雨里幾乎聽不分明。
但卻聽得清晰。
不是槿娘,不是小八。
不在室,是在雨里。
也許是裴孝廉,也許是鄭寺人,也許是府中帶刀侍衛。
但必是暗中監視的人。
不用想便知,青瓦樓那人雖明面上送東送西的,到底是疑神疑鬼慣了,約莫猜到與良原君的關系,這才暗中命人監視罷了。
那人還說什麼得人心是多此一舉,小七輕嗤,似他這般無恥行徑才真是多此一舉。
小七吹熄了燭臺,怏怏背過去,不再去看那個令人討厭的影。
迷迷糊糊睡了過去,再醒過來又不知是什麼時辰了。
驀地想起那個影來,抬眸朝窗外看去,檐下的防風燈籠自顧自燃著,在風里晃出巍巍的澤。
但樹下那人已經不在了。
大抵是被雨淋跑了。
槿娘早就睡了,聽得見此起彼伏的打鼾聲。這鼾聲并不令人煩心,卻使這冰涼涼的雨夜平添了幾分人氣。
小七起下了榻,夜里踢了一腳茸茸的小八,它哼了幾聲復又睡了過去。
推開木紗門,沒有月,沒有星子,夜雨涼風,吹得人瑟然打起了寒來。
自鴛鴦瓦當延展出來的屋檐寬大,將將好能遮住木廊。燕國的殿堂屋宇大多有此設計,先前小住的易水與高別館亦大多如此。
鋪滿青石板的庭院積滿了水,起一圈圈大大小小的漣漪。
窗邊的木蘭已謝了白花,傲然立著,枝干雖,那也藏不住人呀。
小七愁腸百轉,就靠在木紗門邊,沿著木廊緩緩地坐了下去。
往事暗沉,目不忍視。來路又山高水遠,步履艱難。
> 小七忽地痛哭出聲。
檐下的雨愈發下得急了起來,在木廊濺起高高的水霧,不久便打了的擺。
忽地耳邊雨聲乍遠,有人撐傘走近,就立在一旁。
小七抬眸,是公子許瞻。
那人的傘遮在了的腳邊,將雨水堪堪擋在外頭。
并沒有說什麼話,只是跪坐一旁,將攬了懷里。
那人掌心冰涼,袍泛著意,好似已在雨里待了許久了。
三更半夜的,他竟出現在聽雪臺。
并沒有逃跑,何苦他親自來監守。
當真是多此一舉。
他的懷抱依舊溫暖,可小七抗拒他的懷抱。
去推他,試著掙,但他抱得很,將將推開幾寸的距離,那人很快又將抱了。
這才看到他的額間竟也包扎著布帛。
記起離開扶風的那一夜,因不甘辱,將他狠狠地撞向了車楠木。
徑自跳下了馬車,沒有見過那人當時的模樣。
如今看來,那人亦是了傷。
記得他口有傷,臂上亦有傷,便用盡力氣去推他的傷口。
他吃了痛亦不松開半分。
他沒有說一句話,就那麼抱住,好像是一塊多麼難得玉,一塊多麼罕見的寶貝似的。
可小七知道自己不是。
是魏國一棵孤零零的蓬蒿野草。
那人咳了數聲,擋住了檐下的風雨。
小七心中一,那抑的咳聲,是夜便聽過的。
那樹下的影,竟是他嗎?
也不知過去有多久,那人才沙啞地開口,“小七,你想要什麼呀,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猜你喜歡
-
連載2084 章
王妃又逃跑了
天才醫學博士穿越成楚王棄妃,剛來就遇上重癥傷者,她秉持醫德去救治,卻差點被打下冤獄。太上皇病危,她設法救治,被那可恨的毒王誤會斥責,莫非真的是好人難做?這男人整日給她使絆子就算了,最不可忍的是他竟還要娶側妃來噁心她!毒王冷冽道:「你何德何能讓本王恨你?本王隻是憎惡你,見你一眼都覺得噁心。」元卿淩笑容可掬地道:「我又何嘗不嫌棄王爺呢?隻是大家都是斯文人,不想撕破臉罷了。」毒王嗤笑道:「你別以為懷了本王的孩子,本王就會認你這個王妃,喝下這碗葯,本王與你一刀兩斷,別妨礙本王娶褚家二小姐。」元卿淩眉眼彎彎繼續道:「王爺真愛說笑,您有您娶,我有我帶著孩子再嫁,誰都不妨礙誰,到時候擺下滿月酒,還請王爺過來喝杯水酒。」
352.4萬字8.17 497707 -
完結777 章
玄醫梟後
青南山玄術世家展家喜添千金,打破了千年無女兒誕生的魔咒。 滿月宴上言語金貴的太子殿下一句「喜歡,我要」,皇上欣然下旨敕封她為太子妃。 這位千金從出生開始就大睡不醒,一睡就是三年。都傳是因為她三魂七魄隻覺醒了命魂,是名副其實的修鍊廢物。 不但如此,這位千金還被展家給養歪了,是紈絝中的翹楚。沒有修為但各種法寶層出不窮,京城中金貴公子沒被她揍過的屈指可數,名門閨秀見到她都繞道走,唯恐避之不及。 所有人都不明白,生在金玉富貴堆、被展家捧在手心裡長大的千金小姐,怎麼就養成了這幅模樣,都很佩服展家「教女有方」。 展雲歌,玄術世家展家的寶貝,玉為骨、雪為膚、水為姿,名副其實的絕世美人。出生以來隻喜好兩件事,看書、睡覺,無聊時就去鞏固一下自己第一「梟」張紈絝的名頭。 南宮玄,華宇帝國太子,三魂七魄全部覺醒的天才。容貌冠蓋京華、手段翻雲覆雨、天賦登峰造極、性子喜怒不形於色,嗜好隻有一個,就是寵愛他從小就看入眼的人兒,從三歲開始就勵誌要在她的喜好上再添上一個南宮玄。 自從展雲歌知道自己滿月時就被某太子貼上屬於他的標籤後,就發誓,既然這麼完美的男人,主動投懷送抱了,而且怎麼甩也甩不掉,她自然是要把人緊緊的攥在手心裡。 世人皆知她廢材紈絝,隻是命好投胎在了金玉富貴頂級世家裡,唯獨他慧眼識珠,強勢霸道的佔為己有。 「梟」張是她前世帶來的秉性。 紈絝是她遮掩瀲灧風華的手段。 看書是在習醫修玄術,睡覺是在修鍊三魂七魄。 當有一天,她的真麵目在世人麵前展開,驚艷了誰的眼?淩遲了誰的心? 心有錦繡的世家貴女展雲歌和腹黑奸詐的聖宇太子南宮玄,在情愛中你追我逐,順便攪動了整片大陸風雲。 他以江山為賭,賭一個有他有她的繁華盛世。 --------------------- 新文開坑,玄幻寵文,一對一,坑品絕對有保證!陽光第一次這麼勤奮,昨天文完結,今天就開新文,希望親們一如既往的支援陽光,別忘記【收藏+留言】外加永不刪除。 推薦陽光的完結文: 絕品廢材:邪尊的逆天狂妃:玄幻 婿謀已久之閑王寵妻:古言、架空 浮世驚華之邪王謀妻:古言、架空 霸道梟少狂寵妻:現代、豪門 絕戀之至尊運道師:玄幻
213.4萬字8 68793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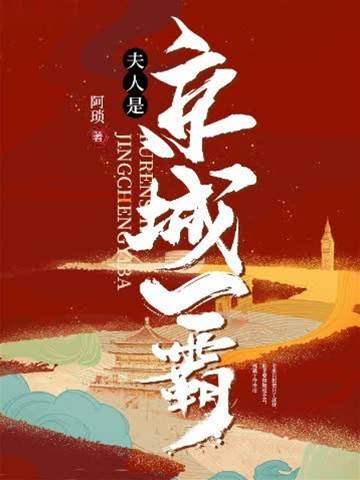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687 章

腹黑萌寶神醫娘親惹不起
【本書又名《我假死後,冷冰冰的王爺瘋了》假死追妻火葬場後期虐男主白蓮花女主又美又颯】一朝穿越,蘇馥竟成了臭名遠昭醜陋無鹽的玄王妃,還帶著一個四歲的拖油瓶。 玄王對她恨之入骨,要挖她的心頭血做藥引,還要讓她和小野種為白月光陪葬。 她絕處逢生,一手醫術扭轉乾坤,將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一心盼和離時,誰料玄王卻後悔莫及。 曾經冷冰冰的王爺卑微的站在她身後「阿馥,本王錯了,你和孩子不要離開本王,本王把命給你好不好?」 等蘇馥帶著兒子假死離開后,所有人以為她們葬身火海,王爺徹底瘋了!
67.5萬字8 1041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