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嬌嬌貴女一紅眼,禁欲王爺折了腰》 第172章 她是他的明月
沈定珠第一天回宮,乾元殿的宮人個個對畢恭畢敬,想問點什麼,這些宮人卻不敢多言。
蕭瑯炎理政務,一直到半夜三更才回來。
他有些疲憊地進了殿,當他看見床榻上那個窈窕睡的影時,蕭瑯炎才怔住腳步。
在南州,也跟沈定珠相多日了。
可是沒有一次,是這麼直觀地讓他到——
回來了。
就在他的邊,他的榻上。
沈定珠這個人很是奇怪,在的時候,他倒沒覺得多麼重要,但是走了的這四年,他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
從前還是王爺的時候,他就算再忙,也想著回府,看看這個人又有什麼作鬧的事。
可離開的四年,他的心里好像也跟著空了一塊。
更讓他自己也覺得驚奇的是,他登基那日,萬臣朝拜,可他總覺得邊缺了一個人。
所以,他才會在知道沈定珠的下落時,毫無理智地追了過去。
知道的消息時,是早上,晚上他就已經離京了。
趕去南州的這一路,他沒有停歇,原本需要耗費一個月的行程,他命車駕日夜兼程,僅用了十三日就抵達了南州。
然后,他終于見到了。
蕭瑯炎薄眸醞著復雜的緒,邁步走過去,在床榻邊,緩緩坐下來。
這四年來,他沒有停止過尋找沈定珠,蕭瑯炎知道,獨自在外,必定要靠什麼生活。
Advertisement
他曾想過,應該只會書法與刺繡,可是當他想到這兩樣以后,蕭瑯炎又有些慌張。
他竟害怕,沈定珠還有他不知道的才能,因為原本就是天上一皎皎明月。
如果不是沈家突然傾頹,作為沈相掌心中的一顆璀璨明珠,沈定珠必然是要嫁給最為寵的皇子。
何曾得到他,來撿拾起這一彎明月?
可現在,好似夢一樣,這個人就在這里,躺在他的龍榻上,且他們的孩子,就在皇宮之外不遠好好地生活著。
蕭瑯炎不自地
手,輕輕住的發梢。
沈定珠被驚醒了。
原本是想著靠一會,等著蕭瑯炎回來,畢竟他已經是皇帝了,若無召寢,睡在乾元殿也不合宮規。
沒想到,這麼一等,自己先睡著了。
方才到有人,才轉醒過來。
睜開朦朧的睡眼,就看見蕭瑯炎坐在榻邊,神晦暗復雜地看著。
“皇上?”沈定珠連忙坐起來,了眼睛,“您什麼時候回來的?”
“剛剛。”蕭瑯炎答。
沈定珠正要下榻,幫他更,但蕭瑯炎卻按住了“你繼續睡吧,一個時辰后,朕要去上朝了。”
沈定珠看了一眼殿里更,才知道竟是這麼晚的時間。
盈盈水眸看向蕭瑯炎,關心地詢問“那皇上要不要躺下來休息會?”
蕭瑯炎原本打算坐坐就走,因著還有一堆堆積的政務沒有理。
但聽到沈定珠這麼說,他便點點頭“好。”
沈定珠往里坐了坐,他就在外合躺下,沈定珠覺坐著也不合適,于是慢慢地躺在了他邊。
“剛剛進來的時候,看見外面的桌上還有涼了的晚膳,你晚上沒用麼?”蕭瑯炎問。
沈定珠沒了困意,聲音溫地回答“妾還以為皇上會回來,就等了一會,后來就忘記吃了,也不,明早再用吧。”
“等朕有什麼事?”蕭瑯炎原本閉眼假寐,這時,卻睜開了銳利的薄眸,轉而著。
他眉眼黑濃,劍眉凜冽,而下面的一雙薄眸,更是深幽。
沈定珠每每看進他眼底,都有一種被深淵扣留的覺。
無意識地了“妾是想問,什麼時候搬去自己的
宮里?”
這個舉,卻讓蕭瑯炎眼眸更加深了深。
他聲音喑啞,連他自己都沒察覺,蕭瑯炎手,把玩著沈定珠服上的一縷帶“為什麼急著要走?朕不是留人伺候你了嗎?難道是們不合你意?”
沈定珠忙說“不是,只是宮規規定,乾元殿是皇帝的寢宮,妾留在這里不合規矩。”
“之前就算在王府,妾也還有自己的屋子呢。”
蕭瑯炎薄抿出一聲嗤笑。
“明白了,是想要自己的住,不肯久居朕的屋檐下。”
沈定珠皎白的面頰頓時紅了紅。
蕭瑯炎倒是順著的意“過幾日,讓徐壽給你安排。”
沈定珠高興起來“多謝皇上。”
喊得生疏,全然不如那夜被撞急眼時,脆生生喊的一句“瑯炎”。
蕭瑯炎眼眸一沉,啞聲問“回來的這一路上,你跟朕生了十三天的氣。”
沈定珠怔了怔,眸狐疑地看著他。
有這麼久嗎?
道“沒有生氣,是妾不想耽誤皇上理政務。”
然而,這句話卻直接點燃了蕭瑯炎心底那把火。
他一個翻,將在下,薄眸中噙著熾熱的神“是嗎?真的不是想逃避,不愿服侍朕?”
沈定珠覺到他的變化,臉紅耳熱,手輕輕地抵擋在他的膛上。
“皇上,不是說只能休息一個時辰嗎?”可不能耽誤他早朝。
蕭瑯炎將的手拉下來,連帶著拽下床帳。
“一個時辰還不夠?”他在耳畔笑,帶著點戲謔的意味,“你要的太多了。”
沈定珠眸睜圓,頓委屈,分明是他食髓知味,不肯罷休。
然而,還不等控訴,蕭瑯炎就按著的下頜,咬著的吻了下來。
這細細的吻,原本帶著些
許憐惜,可后來不知怎麼,蕭瑯炎又橫沖直撞起來。
仿佛相比細弱的嗡,他更喜歡看求饒失神。
一場激烈的折騰過后,沈定珠勉強撐著困倦的雙眼,想送蕭瑯炎去上朝。
他沐浴完出來,發現沈定珠抱著被子,白皙的肩頭在外面,還遍布著點點紅的痕。
困的腦袋輕輕點,蕭瑯炎反而神清氣爽一般,嗤笑一聲“不用送了,你繼續睡吧。”
沈定珠閉著眼,里還堅持說“那怎麼能行呢,不合宮規呀。”
然而,蕭瑯炎走上前,將推了一下,人順勢倒在被褥里,呼呼地睡了過去。
蕭瑯炎笑得劍眉揚起。
他就知道,雖然沈定珠口口聲聲都在提醒宮規,可本是個蠻的姑娘,規矩在眼里,只有必要時候才遵從。
困得很了,他就由得睡。
次日。
沈定珠照舊喝了宮送來的避子湯。
隨后閑來無事,就幫忙澆乾元殿的花,那群宮嚇得魂飛魄散,本不敢讓手。
想勸,但是又不知道沈定珠是什麼位份,只能跟在后,一直喊“主子,您休息會吧。”
這可是皇上放在心尖上的人。
為了,殺前太子,連先皇都死的不明不白,還力朝議,要給封個不小的名分。
沈定珠對此一概不知,只是提著壺,笑著對們說“我只澆花罷了。”
這時,一個窈窕的影,卻帶著宮人,順著白玉臺階上來。
那人對門口的太監說“臣妾崔氏,來給皇上送湯。”
崔憐芙一轉眼,看見窗口笑盈盈跟宮說話的沈定珠,手里的食盒“咣”的一下掉在地上。
骨碌碌地順著白玉階滾了下去。
沈定珠聽見響,轉而看去。
崔憐芙看的神,像是見了鬼般,惶恐不安。
猜你喜歡
-
完結1250 章

法醫王妃:我給王爺養包子
坊間傳聞,攝政王他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蘇七不過是從亂葬崗“詐屍”後,誤惹了他,從此他兒子天天喊著她做孃親。 她憑藉一把柳葉刀,查案驗屍,混得風聲水起,惹來爛桃花不斷。 他打翻醋罈子,當街把她堵住,霸道開口:“不準對彆的男人笑,兒子也不行!”
216.9萬字8.18 52483 -
完結2007 章

神醫狂妃:娘親你馬甲又掉了!
大齊國的人都以為瑾王妃只是個寡婦,瑾王府也任人可欺。可有一天,他們發現——神醫門的門主喊她老祖宗。天下第一的醫館是她開的。遍布全世界的酒樓也是她的。讓各國皇帝都畏懼的勢力是她的外祖家。就連傳說中身亡的夜瑾居然都回來了,更是將她疼之入骨,寵入…
181.2萬字8 94733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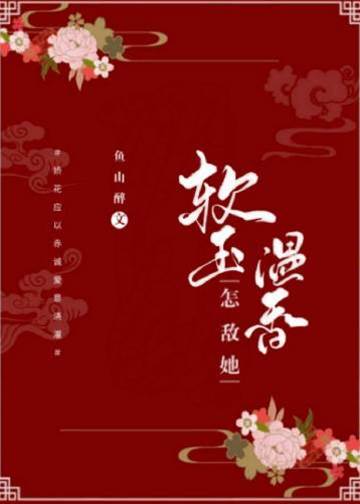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1801 -
連載2178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4.1萬字8.33 4778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