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辭歸》 第377章 朕看你是心眼小
圣上換了常服,在椅子上坐下來。
見李邵一副有話要說的樣子,圣上先晾了晾他,只與曹公公道:“朕有些了,小廚房里可有備著吃食?”
曹公公便道:“有清粥,還有些腌菜,是了,有。”
“就這些吧,”圣上道,“你讓人去取來,朕隨便墊一墊。”
說著,圣上又看向李邵,問:“邵兒呢?要不要陪朕用個粥?”
李邵急著和圣上告狀,可又不能直接忽略問題,便道:“兒臣陪您用粥。”
圣上微微頷首。
曹公公出去代小侍。
李邵見此,只能耐著子坐著。
再著急,也不能不挑時候。
粥很快會送來,這點時間說不上幾句話就會被打斷,得等一等。
圣上移步側間桌邊,李邵跟著過去,侍已經擺了桌。
李邵等圣上筷子之后,也端起了碗,哪怕不,還是著急喝完粥。
等放下碗筷,他正開口,卻被圣上淡淡掃了一眼。
眼神里的意思明明白白:食不言。
這不是父子兩人喝酒吃嘮幾句家常的時候,父皇現在并不想說話。
如此,李邵又只能把邊的話又咽了下去。
等圣上吃完了,兩人回到書房那側,圣上坐下來打量了李邵一會兒。
“邵兒,冷靜了嗎?”他問。
李邵一愣,上忙道:“兒臣沒有不冷靜。”
“是嗎?”圣上又問,“朕看你在金鑾殿時、憋了一肚子的火,朕且問你,一碗熱粥下肚,冷靜了嗎?”
李邵的頭滾了滾。
都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邵也是這樣。
從最初急著向父皇告狀,到一次次被打斷,那子火氣其實已經小了很多,可要說完全滅了,也斷然沒有,從大火轉為小火、溫著燉著,依舊在灼著五臟六腑。
Advertisement
“如您說的,兒臣早朝時的確不夠沉穩,若不是您攔著,兒臣大抵要失態了,”緒變化了,李邵開口時便沒有那般用詞激烈,反而迂回起來,“今日兩位史,以及顧大人說的話,實在讓兒臣心里不舒服。”
圣上靠著引枕坐著,只看神、完全看不穿他此時心。
“為何不舒服?”圣上問,“裕門關的事,他們說的也都是實。你的確扮作兵士悄悄出關,也的確是徐簡在兩軍戰時把你救回來,是朕讓徐簡瞞下了真相,這幾年也沒給個的代。”
“他娶了寧安還不夠?”李邵不由問,“若沒有那些事,他憑什麼娶寧安?皇太后會讓寧安嫁給一年到頭、守在裕門關不回京的人?”
“這是兩回事,一個國公,一個郡主,本就門當戶對,”圣上說著,手指關節在桌案上輕輕敲了兩下,“說到底,你有錯,朕也有錯,史們罵什麼都是應當的。”
李邵抿。
腦海里全是史的咄咄人,這讓他那竭了的火氣倏地又燃燒起來,冒了三丈高。
“父皇,兒臣想說的不是裕門關的對與錯,而是那些消息為何會在千步廊傳開?”李邵道,“來龍去脈知曉得那麼清楚,只可能是徐簡故意為之!”
圣上眼神沉沉:“邵兒,你想說什麼?”
“父皇,兒臣知道您很喜歡徐簡,甚至因為裕門關的事、格外包容他,您也說過,您想讓他做兒臣的左膀右臂,可是,”李邵深吸了一口氣,“兒臣以為,徐簡另有想法,他對兒臣可沒有那麼忠心。”
圣上冷聲道:“徐簡對你不忠心?那他對誰忠心?”
李邵想說什麼,又被圣上趕了先:“戰場上舍命救你、不算忠心?圍場上不顧舊傷救你,也不算忠心?邵兒,你該慶幸你沒有在金鑾殿里說這種話,否則有多人要寒心?!”
李邵臉上刷白,但他知道開弓沒有回頭箭,他若退了這一步,以后再想與父皇談論徐簡的狡詐用心就很難了。
他得替自己爭取!
“兒臣不是這個意思,”李邵急忙道,“兒臣想說的是,徐簡并非不希兒臣當穩穩當當做太子,他忠心的肯定是父皇您與兒臣,只是、只是徐簡很多事做得很奇怪,兒臣認為,他的野心不小,他想拿兒臣,他想攝政。”
見父皇眉宇皺,卻沒有阻攔他解釋的,李邵重新梳理了一下思緒。
“他一直在找兒臣的麻煩,”李邵道,“就說那批古月貢酒,當初的確是兒臣考慮不周,私下換了酒,徐簡卻讓寧安到慈寧宮、問皇太后討酒。
討酒是假,尋事是真!
還有虎骨,藥房里那麼多虎骨,寧安都看不上,非要問兒臣要。
圍城那天,寧安又故意在城門口下馬車……
徐簡不是有二心,他就是想拿兒臣,讓兒臣出丑,又給兒臣‘施恩’。
兒臣知道自己有很多做得不對的地方,父皇您怎麼教訓兒臣都是應該的,不止您,三孤是兒臣的老師,兒臣要聽他們的指點。
可這都不是徐簡該做的,徐簡不止自己做,他還教唆寧安,利用了皇太后。”
李邵一開口,就如倒豆子一般。
圣上沒有打斷他,直到李邵停下來,他才問:“說完了嗎?”
李邵道:“父皇,徐簡真不是您想的那樣……”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圣上的聲音一下子嚴肅了起來,著些許火氣,“原來你都是這麼揣度徐簡的,難怪!徐簡說你心思細,朕看你是心眼小!”
李邵慘白的臉瞬間染了紅,尷尬又難堪。
饒是他想過父皇許是不會信他,可被父皇說這樣的重話,李邵心里很難接。
“父皇,”李邵站起來,“徐簡與單慎關系好,耿保元的事分明也是他在背后搗鬼。
那個什麼外室的留書,早不拿出來、晚不拿出來,偏偏這時候出現了。
徐簡就是想讓兒臣下不來臺,還有那些傳言也是,一個個為徐簡鳴不平……”
“住口!”圣上一字一字道。
就兩個字,卻如兩把刀,扎得李邵神恍惚。
從小到大,這麼多年,他不是沒被父皇罵過,裕門關回來時、他被罵得狗淋頭,但那時候,罵來罵去都是圍繞著他。
這一次,是為了一個外人。
父皇更信徐簡不信他,父皇為了徐簡罵他。
李邵被這些緒裹挾著,以至于只看到圣上的皮子在,卻沒能聽清楚到底又罵了些什麼。
圣上罵得很兇。
聲音不大,可能中殿那兒都聽不見,卻很沉,聲音沉,語氣沉,用詞更沉。
失、難過、氣憤包裹著他,他甚至走到了李邵面前,真正的劈頭蓋腦一通罵。
“聽進去了沒有?!”訓斥到最后,圣上深吸了一口氣,一瞬不瞬盯著李邵,“朕說的,你都聽進去沒有?”
李邵一個激靈回過神來,了脖子。
圣上抬手,重重按在李邵的肩膀上:“人人都有緒,你有,朕也有,但一國之君不能借著緒去看人。
你如此揣度徐簡,朕當真十分失,你自己回去冷靜冷靜,想一想朕說的話,想明白了之后,去和徐簡賠禮。”
李邵愕然。
賠禮?
憑什麼?
徐簡坑他,躲得好、藏得深,算徐簡有能耐!
可他是被坑的那個,還要反過頭去賠禮,這口氣怎麼能順?
“父皇……”李邵張口。
圣上手上又加了些力氣:“你還有異議?”
李邵一時吃痛、皺了下眉頭,到底沒敢再說什麼。
說了也沒用。
“兒臣知道了,”李邵道,“兒臣告退。”
圣上沒有留他,示意他出去。
曹公公一直守在一旁,聽得心緒萬千,垂著頭送李邵出去后,又回到前。
見圣上靠著椅背閉目養神,眉宇間卻難掩疲憊之,曹公公的心也跟著揪了一下。
他伺候圣上這麼多年,最了解圣上對殿下的護之。
雖然說,“磨一磨殿下子”是圣上拿定的主意,為了達到效、圣上也布置了許多,但今時今日,殿下走進這張網里,當真說出那些話時,圣上依然會割心割肺的痛。
這種失在圣上心頭,這滋味……
曹公公輕手輕腳給圣上添茶,而后重新凈了手,站在大椅后頭,替圣上按額頭。
按了會兒,圣上低聲道:“是朕擰晚了,邵兒那子,朕早兩年就該好好擰一擰。”
曹公公便道:“晚是晚,卻不是遲……”
“你不用寬朕,”圣上嘆道,“朕確實沒料到,他竟然是那般揣度徐簡的,這兩年難為徐簡了。”
不止這兩年,近些時日,其實也在為難徐簡。
因著他想磨一磨邵兒的子,因著他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廢太子的理由,徐簡也是絞盡腦。
元月里耿保元那些事,想來與徐簡并無干系。
那塊腰牌是真的,耿保元早就不見了,徐簡弄不來真腰牌,應當就是借著順天府挖出東西來、順勢“添油加醋”。
畢竟,劉迅的外室是個什麼狀況,現如今也就徐家人清楚些,那封留書也只有可能是徐家人、或者說是徐夫人藏著,遇著事了拿出來。
至于外頭的風言風語……
平心而論,當年瞞下來的事,圣上并不想鬧得沸沸揚揚。
前幾天林玙來書房與他商量時,他也是這麼一個意思,可最后還是林玙說服了他。
裕門關的陳年舊事,京中只那麼些人知曉。
若非徐簡不方便進宮,需要他代為前請示,這事也不會告訴他。
可裕門關當時經歷了的將士們多心里都有數,他們守著邊關,將士會回京、兵士會返鄉,興許有一天就管不住了。
再者,此次的目的是廢太子,太子一旦被廢,多的是不想讓他復起的人。
過幾年,為了太子之位你爭我搶,鬧得厲害時,說不定就有人惦記著去裕門關把事弄清楚。
與其有朝一日忽然被翻出來,給予殿下沉重一擊,倒不如借著這次機會都展開了,罵也罵了、罰也罰了,往后再想翻舊賬,這舊賬也了霉了,沒什麼意思了。
斷絕將來不必要的麻煩,方便此次計劃,裕門關那事兒也差不多能“名正言順”廢太子了。
況且,傷口這東西,捂著會爛、難好,唯有掀開來、刮去潰爛,才能長出新來。
去除了患,這長得才好。
圣上當時沉默許久,還是都聽進去了,讓林玙告訴徐簡看著辦就是了。
這也才有了外頭漸漸傳開的流言。
圣上并不清楚徐簡是怎麼安排的,等來年徐簡進宮時倒是可以問兩句,但這個效,圣上已經看到了。https:/
千步廊那兒傳開了,史早朝時發難,顧恒也湊了一腳。
甭管都是什麼心思,總歸是達了他想要的局面,唯一讓圣上憋得慌的還是李邵的態度。
李邵直指徐簡。
誠然,徐簡的確在背后做了些事,但邵兒質疑他、卻是認為徐簡想拿他……
連貢酒、虎骨都一并搬了出來,可見緒之深。
邵兒與徐簡之間的心結必須得化解開,若能借著這一回刮骨療傷、徹底好起來,那是圣上最希看到的了。
“徐簡有能耐,”圣上嘆道,“可惜邵兒聽不進去。”
曹公公手上不停,心里也跟著嘆了一聲。
另一廂,李邵走出書房后,呼嘯的冷風沒有讓他冷靜下來,反而越來越煩躁。
汪狗子亦步亦趨跟著,垂著的那張臉,臉很難看。
他也算了解太子了。
早朝上被史們罵,書房里又挨了圣上的訓,殿下此刻緒可想而知。
這火氣憋著不發出來,悶到最后、炸得更響。
可要說讓太子殿下尋個地方把氣撒了……
眼下這狀況,還有哪里能悶聲不響?
圍場跑馬不行,吃酒撒酒瘋不行,尋個人更不行……
草木皆兵,被人發現了,完蛋!
李邵一直走到宮門,轉頭代道:“準備馬車。”
汪狗子心下一驚:“殿下,您要去哪兒?”
“去輔國公府。”李邵咬著牙道。
汪狗子一口寒氣,只道“不妙”!
李邵沒管他,又道:“父皇讓我去給徐簡賠罪,那我就去。”
汪狗子:……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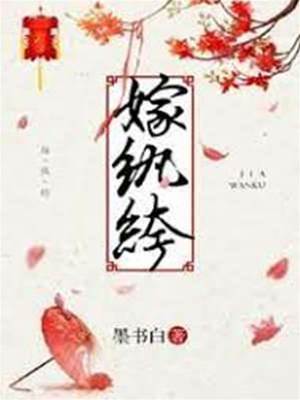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94 章

驚雀
虞錦乃靈州節度使虞家嫡女,身份尊貴,父兄疼愛,養成了個事事都要求精緻的嬌氣性子。 然而,家中一時生變,父兄征戰未歸生死未卜,繼母一改往日溫婉姿態,虞錦被逼上送往上京的聯姻花轎。 逃親途中,虞錦失足昏迷,清醒之後面對傳言中性情寡淡到女子都不敢輕易靠近的救命恩人南祁王,她思來想去,鼓起勇氣喊:「阿兄」 對上那雙寒眸,虞錦屏住呼吸,言辭懇切地胡諏道:「我頭好疼,記不得別的,只記得阿兄」 自此後,南祁王府多了個小小姐。 人在屋檐下,虞錦不得不收起往日的嬌貴做派,每日如履薄冰地單方面上演著兄妹情深。 只是演著演著,她發現沈卻好像演得比她還真。 久而久之,王府眾人驚覺,府中不像是多了個小小姐,倒像是多了個女主子。 後來,虞家父子凱旋。 虞錦聽到消息,收拾包袱欲悄聲離開。 就見候在牆側的男人淡淡道:「你想去哪兒」 虞錦嚇得崴了腳:「噢,看、看風景……」 沈卻將人抱進屋裡,俯身握住她的腳踝欲查看傷勢,虞錦連忙拒絕。 沈卻一本正經地輕飄飄說:「躲什麼,我不是你哥哥嗎」 虞錦:……TvT小劇場——節度使大人心痛不已,本以為自己那嬌滴滴的女兒必定過得凄慘無比,於是連夜快馬加鞭趕到南祁王府,卻見虞錦言行舉止間的那股子貴女做派,比之以往還要矯情。 面對節度使大人的滿臉驚疑,沈卻淡定道:「無妨,姑娘家,沒那麼多規矩」 虞父:?自幼被立了無數規矩的小外甥女:???人間不值得。 -前世今生-我一定很愛她,在那些我忘記的歲月里。 閱讀指南:*前世今生,非重生。 *人設不完美,介意慎入。 立意:初心不改,黎明總在黑夜后。
21.3萬字7.83 21942 -
完結866 章

神醫魔后
21世紀玄脈傳人,一朝穿越,成了北齊國一品將軍府四小姐夜溫言。 父親枉死,母親下堂,老夫人翻臉無情落井下石,二叔二嬸手段用盡殺人滅口。 三姐搶她夫君,辱她爲妾。堂堂夜家的魔女,北齊第一美人,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個笑話。 她穿越而來,重活一世,笑話也要變成神話。飛花爲引,美強慘颯呼風喚雨! 魔醫現世,白骨生肉起死回生!終於,人人皆知夜家四小姐踏骨歸來,容貌傾國,卻也心狠手辣,世人避之不及。 卻偏有一人毫無畏懼逆流而上!夜溫言:你到底是個什麼性格?爲何人人都怕我,你卻非要纏着我? 師離淵:本尊心性天下皆知,沒人招惹我,怎麼都行,即便殺人放火也與我無關。 可誰若招惹了我,那我必須刨他家祖墳!
228.2萬字8 394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